《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初版于1939年,是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随着本书的出版,最初由瓦尔堡学派创立的图像学已然脱离辅助地位成为美术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美术史之为人文学科,从此进入了图像学研究的时代,它与沃尔夫林的风格分析一起成为现代美术史教学的两大支柱。
除了作为方法论的导论之外,本书共有六章,每一章都是图像学方法运用的案例,从美术史、哲学史、宗教史、社会结构史、科学史等多学科多角度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作品的意义进行分析,正如译者引用的一位美国学者所说:“我们读他的《图像学研究》,‘皮耶罗’一章像读文明史,‘时间’和‘丘比特’二章像读文学史,最后二章像读哲学史;而且不是泛泛的文明史、文学史和哲学史,它们都是那些领域中的杰作;即使从比较文学而言,似乎也极少有一部书能与《图像学研究》比肩。”
本书是2011年中译本的全新修订本,文字做了大幅修订,替换了全新的图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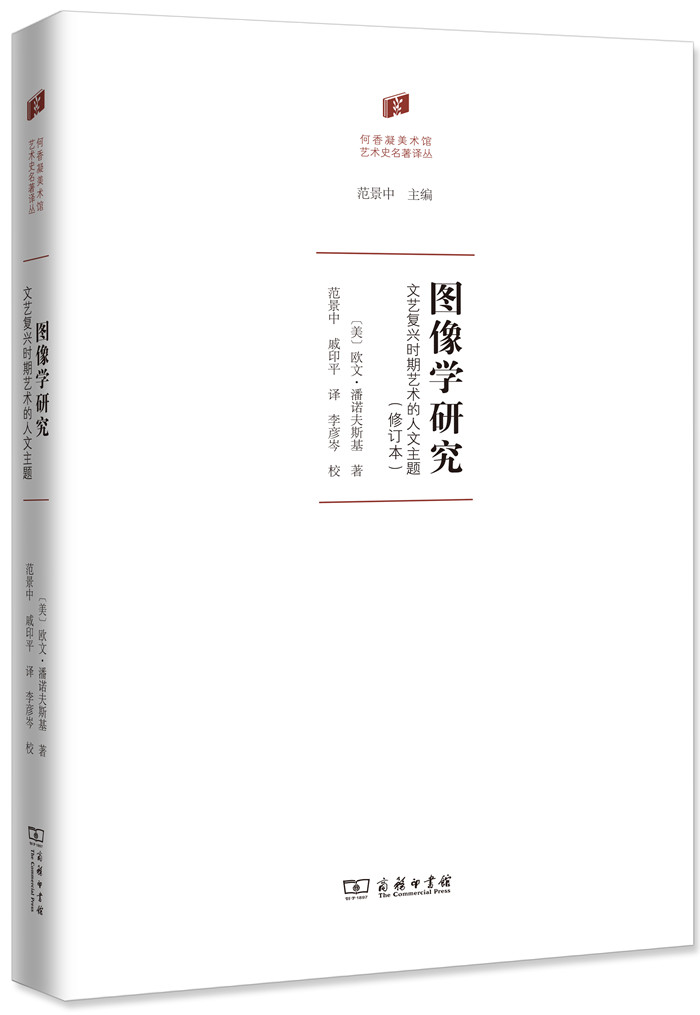
《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修订本)
[美]欧文·潘诺夫斯基 著
范景中 戚印平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内文选读:
在佛罗伦萨的阿拉齐美术馆,有一件佛兰德斯著名编织师乔瓦尼·罗斯特根据安吉洛·布龙齐诺素描底样编织的挂毯。一份1549年的收藏品目录称它为L’Innocentia del Bronzino[《布龙齐诺的纯洁图》]。在这幅作品中,“纯洁”受到由四种野兽象征的各种邪恶力量的威胁:它们是犬、狮子、狼和蛇,分别象征着“嫉妒”“狂怒”“贪婪”和“背信”。“纯洁”得到“正义”的拯救,后者手持剑和天平,有意模仿耶稣基督从地狱拯救灵魂的姿势。肩负一个沙漏的带翼“时间”搂抱着一个人,以前的一位作家叫她“年轻的姑娘”。但事实上,“时间”不仅搂抱着这个姑娘,而且还揭开了她的面纱,她因此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即“真理”的一个拟人像。由此可见,这幅作品混合了一个主题的三个相互关联的故事,即“被时间拯救的真理”“被时间揭开面纱的真理”和“受迫害后得到辩护的纯洁”。后者正是卢奇阿诺斯所记述的阿佩莱斯的名作《诽谤图》的主题。
这件挂毯还有一个“姊妹篇”,就是制作时间似乎稍迟,同样收藏于阿拉齐美术馆的《花神》。从纯技术的角度看,两件作品无疑是一对。它们的尺寸与缘饰完全相同。但《花神》挂毯的构图,一个被簇拥的主要人物占据中心位置,与另一件挂毯上人物的紧凑并不一致。从图像志的角度看,两件挂毯表达的概念也不尽相同,不仅光彩照人、动作轻盈的撒花女神与道德寓意像的严肃精神大相径庭,而且《花神》最初甚至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作品系列。这位不是骑着一只牡羊而是飞翔于其上的女性(顺便说一句,这位女性是以丢勒的蚀刻画《独角兽上的诱拐》,确切地说,是以《劫持普洛塞皮娜》为原型)不应当被称为“花神”,而应当称为“春”,区别在于,花神是独立的神话人物,春则属于“四季”的循环。此外,簇拥在这一人物周围的不仅有“牡羊”“牡牛”和“拥抱着的男女”,还有春季三月的黄道十二星座,即代表三月的白羊座,代表四月的金牛座和代表五月的双子座。这亦可佐证上述观点。当然,布龙齐诺的创作比起单纯地——用牛津词典的话说——“在一年中划分出气候的类型和植物的生长阶段”来说还有一层更丰富的意义;根据一个流传了近两千年的信仰,四季与人的四个年龄段、四个要素、四种气质之类的概念有联系,因此,布龙齐诺的“春”自然暗指青春、空气、多血质等概念及其衍生的其他含义,如愉悦与爱恋。显然,所谓的《花神》挂毯最初被构思为一组四联画中的一幅,将它与《纯洁图》挂毯扯到一起无疑是后人的想法,从图像志的角度看,并没有确凿可靠的依据。可以推断,将《花神》与《纯洁图》两件挂毯组合在一起,仅仅是因为编织师在着手编织时已经无法制作原本要与《纯洁图》配对的另一件挂毯,而这又是因为,他们已经无法获得最初为另一件挂毯绘制的素描底样。
实际上,如果要寻找与《纯洁图》挂毯在构图上略显拥挤、特殊的图像志两方面均完美匹配的某一幅布龙齐诺的作品,那可能是现藏伦敦国家美术馆的一幅著名的寓意图。这幅通常认为作于1546年前后的绘画,与《纯洁图》挂毯的素描底样颇为相似。瓦萨里是这样描述的:“他画了一幅非凡而美丽的画,送给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这幅画描绘了裸体的维纳斯和与她接吻的丘比特。两人的一侧有快乐、玩耍和其他丘比特;另一侧是欺骗、嫉妒和其他的爱恋情欲。
作者:[美]欧文·潘诺夫斯基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