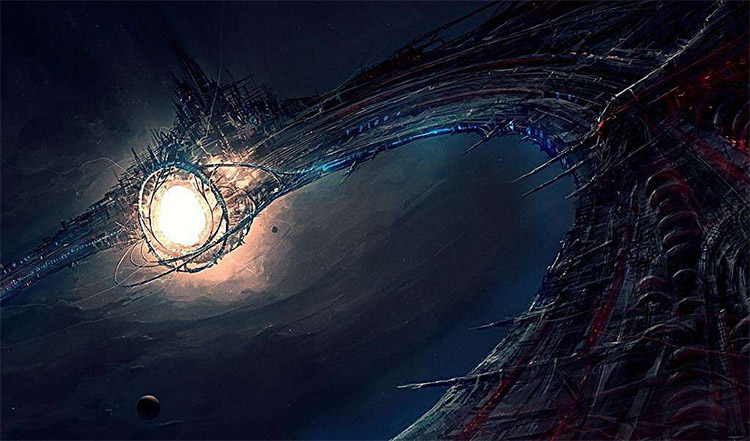
记得我在很幼小的时候,妈妈常常带我去值夜班。妈妈是医生,那时候医生办公室有炉子,我就着炉子读书。读的是什么呢?根据《星球大战》电影改编的小说。那也许是八十年代初,中国的电影院里还看不到《星球大战》。可是我已经读了小说,记得一开头描写的世界,两颗太阳照耀下的星球,天行者卢克,蕾雅公主求救的全息录影,神秘的绝地武士欧比万,我其实不记得那本小说里是怎样翻译这些名字的,但那样恢弘的印象,永远也不会忘。读完《星球大战》,立即读续集《帝国反击战》。天行者卢克遇到隐藏在密林中的绝地宗师约达长老。矮小动物一般的约达唠唠叨叨,卢克心猿意马,但终于在约达的指点下,开始理解何为原力,什么是心,什么是物。我读得如痴如醉。几年以后看到金庸《笑傲江湖》里写风清扬传剑一幕,不禁怦然心动。卢克和令狐冲,这两个英雄人物,在我心目中将科幻和武侠两个文类沟通起来,他们都是理想青年,而约达和风清扬那样的世外隐者,智慧的导师,沉着的高手,人生难得一见,在小说里看到,更是让人心旷神怡。

我描写的这个经验,为我同一代的许多人共享。了不起的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虽然年长我很多岁,也是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时期,读到西方科幻经典,凡尔纳,威尔斯,克拉克,阿西莫夫。几乎所有的科幻作家都差不多先经历过一个科幻迷的阶段。迷恋,才会热爱,热爱,才会创作,而创作,会令人更加持久的迷恋,热爱。没有半途而废的科幻迷,也没有半途而废的科幻作家。
记得韩松有一次讲话,一开头就把大家都逗笑了,他在几位青春小说家之后发言,说其余发言人都是青年,而科幻则是少儿文学。这是千真万确的。曾经有一个时期,中国科幻和科普读物是特别向少年儿童打开大门,通向知识大厦,通向世界想象。我记得小时候读过一些书,此后再也没有见过。一套书是当时从苏联翻译来的多卷本《人是怎样成为巨人的》,是整整一部科学发展历史,还有一套是中日建交之后日本为中国小读者印行的《少年博物馆文库》。这些书是广义的科普读物,适合孩子看。日本《少年博物馆文库》大约有十几本,图文并茂,纸张精美,从哲学到天文,从史前到当代,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真是让我和同学们大开眼界。记得当时大家没有人能买得起一整套,就你买一本,我买一本,互相交换着读。
儿童在一个年龄,对世界发生好奇,这样重要的事件,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如果这个时候,世界向你打开,你会看到世界无穷无尽的影像,此生此世都会继续好奇,保持理想。这是为什么我感谢科幻。在我六七岁到十几岁这个时期,中国经历了一次科幻的复兴。不用说各种中国科幻小说,而更让我着迷的是,各式各样从苏联、日本、美国、欧洲翻译到中文的科幻。法国人写的《猿猴行星》,重印的凡尔纳全集,日本星新一的作品,苏联的《飞人阿里埃》和《仙女座星云》,英国作家的《2001年太空漫游记》。我记得还在一本家里大人读的英文小说选中,吭哧吭哧地读过一篇小说,喜欢到不行,就自己翻译了出来,很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那是科幻大师布雷德伯里《火星编年史》中的一个章节。从另一位已经逝去的亲人那里,我得到一本《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1983年初版,我依然带在身边。我无法想象十岁的时候,我是怎样读《特隆,乌克巴尔,奥尔比斯,忒蒂乌斯》这篇无与伦比包罗万象的科幻小说。
我后来既没有成为物理学家,也没有继续发挥对古生物学和考古学的兴趣。不久之后,周围的同学都在读武侠小说。我也随着读了几本,只是喜欢金庸,对其余的武侠小说作家完全看不上眼。科幻文学渐渐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我看到录像带上的 《星球大战》。许多年过去,我在纽约最大的电影院里看《星球大战前传》。随着年龄增长,我似乎告别了科幻。我用新的眼光来读博尔赫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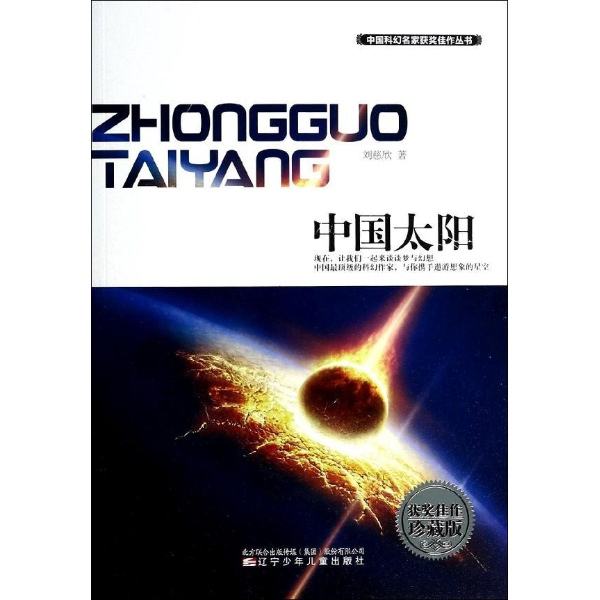
直到有一天,我得知《三体》的存在,我读到《中国太阳》《宇宙墓碑》。所有童年的记忆都打开了。那个无限美好的想象世界,在隐藏了许多许多年后,蓬勃而出。我为年轻的读者,为如同我幼小时代的年轻朋友们编选这本书,希望你们在好奇的时候,有一扇门打开,让你看到一个惊奇、美丽的世界。无论你将来成为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律师,创业者,或者普通上班族,这个世界永远跟着你,不会失去,你可以回到童年,回到未来,回到中国科幻的创世纪。(本文为东方出版中心《中国太阳———给孩子们的科幻小说》编者序)
文:宋明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