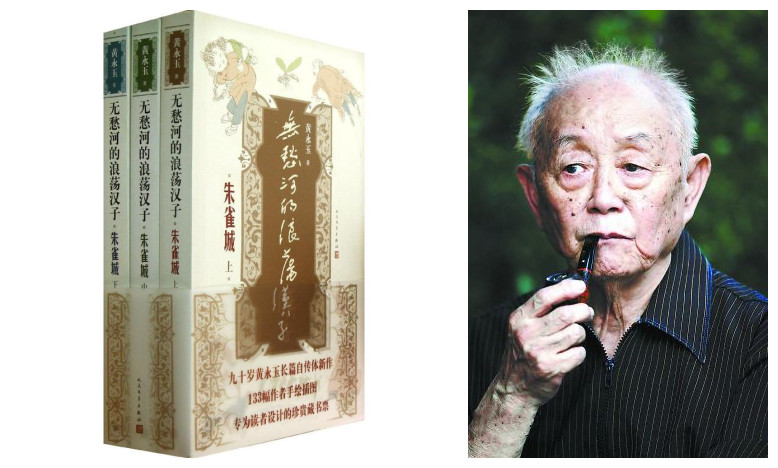
木刻展览会末一天,大家都没有走,帮着收拾画框子,十件十件垫着报纸捆在一起,帮着搬上卡车,又回头转来清理墙上和地面的杂物,把场面弄得干干净净。序子当时没注意是谁在打点拿主意的,觉得这种做法很好,很从容自然,像在家里过日子一样。
有人说,大家不要散,到法租界(那时还习惯这么叫)一家俄国西餐馆吃俄国大餐,AA制。有的人有事先走了,还剩下约莫三十多个。好像记得就那么走着去的,相当相当的远。到了一看,原来是间大弄堂房子,也没有想象中西餐馆讲究的排场,像一条深深的涵洞。桌子没铺桌布,应有的刀叉食具倒是齐全的。大概诃田跟老板熟,菜牌子和点菜手续都省了,一律“全餐”,每位八角。
计有:
开味小头盘,咸橄榄或甜酸黄瓜片,罗宋红菜汤,大面包两片(黄油一小碟)。
炖牛肉饭,或鸡腿饭,或猪脚饭,或猪肠饭,任选。
咖啡或茶。
口味、分量和仪式的单纯,价钱的公道,都让大家对饭馆产生敬仰。吃完之后由诃田弄来个纸盒子沿着桌子向大家收钱。说好秋季展览之后还上这儿来。李桦、烟桥和野夫三位头头也都说这样的饭馆真难得,好得有点违反常规。
序子遗憾这铺子离虹口实在太远了点。要不然一天一顿八毛的饭钱还是出得起的。解决了大问题。
到同济大学找李大宾。走好多路,幸好脚上这双皮鞋真经得住。听了马寅初老人家的演讲,座位坐满了,反倒在讲台右脚边上找到两个不是椅子的坐处。
马先生讲的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经济的必然沦落,产生恶性循环。现代化的耕作方式,现代化的饲养方式,丰收出现供销的不平衡,农产品过剩,牛奶倒进海里……
听完演讲,大宾介绍几个同学认识,一起去吃午饭,吃完午饭坐在树荫底下聊天。他们知道序子是木刻协会的,讲到过几天上海将有个“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序子问大宾:“我在江西画了一卷三十米长、四十厘米宽的土布反对美帝的漫画,用不用得上?”
“太好了,借给我们!”
序子又说:“这卷布漫画拉出来只是壮个声势,它远远看不清,实际不如传单好,直接送到老百姓手中。我回去向几位木刻前辈打听打听,这两天能不能找几个木刻家刻一些配合大游行的木刻,印成传单,到时候散发?”
几个人都说:“你们木刻协会这几天要是能刻出几张木刻来,我们几天工夫就把它变成十万张!到时候外滩、南京路就热闹了。”
序子说:“到时候,希望让我参加你们的游行队伍。”
“当然欢迎!”又说,“你看,今天是礼拜四,下礼拜四做不做得出来?”
序子说:“眼前我还不敢说,要真动手,可能要不了这么多时间。……那我就告辞了。”
“我下礼拜二到你家去听消息。”大宾说。
回到城里,序子马上到狄思威路九〇四弄五号向李桦报告。他和余所亚正在吃饭,见序子到来便叫女佣金凤添了碗筷。
余所亚对序子说:“你运气好,马上参加打仗了!”
李桦告诉序子:“你吃完饭就回去休息,明天上午不要来,我一早就去找野夫、烟桥商量。你中午吃过饭早一点来,不要忘记带木刻刀和板子,三十二开就行了。可能还会来不少人,办这事情越快越好,你说是不是?”
回到住处,几个人正剥花生瓜子,序子就介绍今天到同济去看了老同学李大宾,听了马寅初先生的报告。
阿湛是个万事通,世界上姓马的他几乎都认识,说得有头有尾:
“唉,唉!马寅初我在郑振铎先生家见过。大经济学家,美国留学,耶鲁、哥伦比亚都念过。研究人口学的大专家,我们隔壁嵊县人,他家是卖酒的。为了想外出读书,跟他爹狠狠干了一架,气得跳河,差点淹死。好玩的是他有七个子女,两个老婆,却是提倡节制生育的权威。是我们那位蒋委员长的死对头。吓不怕、关不死的大人物。”
韦芜说:“说起来也怪,同是肉身,有的胆大,有的胆小,有的高风亮节,有的奴颜婢膝。”
序子提壶灌满水,顺手炖在电炉上。
“水够了,两把热水壶,怕还喝不完。”阿湛说。
“洗脚。”脱下皮鞋和袜子,“你看,一边两个泡!”序子说。
“娇嫰!”韦芜说。
“嗳!嗳,老夫一辈子山南海北,同济跟虹口来回顶多三五十里,算得了什么?是我这对新鞋磨的。”序子说。
“新鞋和人有点像夫妻关系,要忍得住起泡,当然离婚的不幸是有的,都怪你原先弄错了鞋号,或者是试穿的时候大意粗心。”林景煌说。
“要是鞋铺有个试穿期就好了。”韦芜说。
“你实际上是想说人应该有个试婚期。”田青说。
“你才见鬼咧!看你那副样子就是你爹妈试婚期生出来的!”韦芜说。
序子烧热了水,端了个脚盆放在床边,调匀水温,泡起脚来,一边听众口纷纭。该笑的跟大家一齐笑,不该笑的不笑。渐渐地水凉了,抽起双脚擦干。林景煌过来:
“刚洗完,别凉了脚,这水我倒了罢!”
序子扯了被单角盖住脚,坐着坐着就躺下了……
第二天大清早,屋里剩下序子一个人。菜市场买了四个烧饼,两个吃了,两个留做午饭,坐在桌子边上构想传单稿子。一要意思直接,二要画面夺目,于是就在板子上动起手来。准备了两张,一张叫《消灭打手》,一张跟着一首骂国民党的歌谣的题目叫《你这个坏东西》。


心想,多少年来跟反动派打仗,画画、写文章隔好几层关口。这下子拿木刻面对面,像刺刀、像子弹、像投枪、像手榴弹,直接跟反动派见面,好昂扬,好威风!
到了中午,《消灭打手》已刻好半张。一点钟到狄思威路李桦家,两个人又在吃午饭,见序子进门,忙叫金凤添碗筷,序子说自己带了午饭,陪着把烧饼吃了。
饭后把稿子给两位看,都笑着说好,序子跟着开心。眼看大家没来,就着饭桌刻起剩下的那半张《消灭打手》。两点钟左右,麦杆第一个赶来,见序子快刻完第一张,拍拍肩膀说:“我快,没想到你比我还快!”
不久,赵延年、西厓、余白墅和刃锋都来了。
李桦讲:“昨天我找烟桥、野夫讲了,都很兴奋,说人不宜太多,以免张扬,也要快,要严格保密,注意安全。”
“我认为这是一个干通宵的工作,半夜三更还亮着灯会引起特务的注意,这扇大玻璃窗应该用军毯子钉起来。”刃锋说。
“有道理,李桦你一定有国民党灰军毯,拿出来用用。钉子垫了纸不会坏的。”麦杆说。
李桦果然有军毯,西厓、刃锋、麦杆三两下子就钉好了。除序子的稿子刚才大家看过之外,其余的人都亮出自己的稿子。大家都清楚西厓的东西细而慢,没想到他的题目也是那么明快——《拿饭来吃》。
李桦严肃地说:“这工作大家头脑要清楚,今晚上特务如果上门搜查,各人都要有个准备,要是审问起来,说什么好?大家仔细想想……”
“可以说我们想开个救济难民的展览义卖会。”麦杆说。
“开玩笑!上海这些日子到处讨饭的乞丐,其实都是苏北解放区逃亡过来的地主富农,怎么可以当他们是等待救济的难民?我们为他们开神圣的夜车?”刃锋不高兴。
“这不就对了嘛!我们一口咬定半夜辛辛苦苦帮助上海市长吴国桢解决困难,他们还有什么话说?还不多谢我们?”麦杆说。
刃锋开始微笑点头。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李桦问。
“那可是要坚决一点,绝对不能到时候变节。”赵延年说。
几个人曲起手臂碰在一起,连坐在床边的余所亚也曲起手臂:“坚决!”“坚决!”

(事隔七十二年,当时的情景好真诚,好幼稚!有没有共产党员在内我不太清楚。李桦不像,西厓不像,汪刃锋不像,赵延年不像,余所亚不像,我不是,就差个王麦杆,不大清楚是不是?我看当时的王麦杆也不太像是,虽然他参加过新四军。后来知道他也不是。
如果当年其中有共产党,他就会帮助我们把事情弄得正常些。
不过,我觉得这样也好,自自然然,天真无邪!
多少年后,有位党员同志开我们玩笑说,你们当年如果窗户不钉毯子,或许特务不会注意;钉了毯子,我若是特务,见了,非抓你们不可!)
天亮了,木刻刻完了,各自出钱买了豆浆油条回来,吃完再见。合计:
李桦一张,赵延年一张,汪刃锋一张,麦杆两张,张序子两张,西厓一张,一共八张,到中午阿杨又送来一张,一共是九张。
今天是礼拜二,李大宾带了两位同学来探消息,没想到木刻完工,介绍李桦和余所亚跟他认识,兴奋地抱着木刻板走了。
五月四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开始。序子一早搭公共汽车到外白渡桥外滩这头下车,沿路步行到汇丰银行左边大狮子石阶上坐着,人来得千千万万,还有骑马的巡逻队盾牌兵、黑色喷水的水龙头车、响的大小警车、囚车……
上海各大学,江苏和浙江各大学、专校……打着横幅长长的标志牌,横幅大标语,“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打倒美帝侵略者”等横批,大队伍隔不多远有个大喇叭,随时领导人群喊口号,唱歌。同济大学正举着那三十米长的反对美帝布漫画,序子便挤了过去,见到李大宾和其他几个熟人,他们正散发着木刻,一张一张交给拥挤的叫喊的市民们。好笑的是外国公司铁栅门上爬满看热闹的外国人,还有美国大兵,都跟着游行队伍高唱《团结就是力量》那首歌,以为是原来的《耶稣的圣歌》,不清楚其中部分内容是诅咒他们,为他们预备的。
序子还真没见过这么热闹的场合。
几万学生和看热闹的市民一下子都挤到这黄浦滩来,叫口号,贴标语,散传单,唱歌。
黄浦江上停着中外大小轮船,像闹新房一样地跟着起哄,大小粗细嗓门的汽笛乘兴拉响起来,哪个也制止不了。
队伍走得慷慨激昂,阵势雄壮,旌旗飘扬。口号和歌声响彻云霄。
“剥开四大家族画皮!”
“废除一党独裁!”
“党、团滚出学校!”
“取消特务政治!”
“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反对迫害!”
“拿饭来吃!”
……
这时候,马队冲过来了,只往人多处来回凶猛践踏,挥动马棒四处乱斫。高压水龙头直对学生队伍扫射,学生们手牵着手愤怒呼叫,倒下又站起来,扶起受伤的同伴,紧跟着大队伍的脚步。
序子运气好,只让水龙头末梢扫了一下,滑倒地上,差点让马蹄踩着,爬起来闪到华懋饭店花坛市民那边。
特务多次想冲散队伍抓人,学生们以拳头抵抗,遗憾的都是徒手,要不然完全有可能狠狠地还击一番。
序子回到住处,脱下变了形的衣服用电炉烘烤。林景煌带回三个浙大同学,都是外滩参加游行的,交流了些经历,感受差不多。得意的是给国民党点颜色看。学生游行,代表全国老百姓的政治成色,不是好惹的。
林景煌上市场买回好多生煎馒头,大家就着茶水吃了。原来都是闽南老乡,怪不得讲起北京话来疙里疙瘩。说着说着告辞走了,要赶当晚火车回杭州。
来源:收获微信公众号
编辑:李添奇
责任编辑:李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