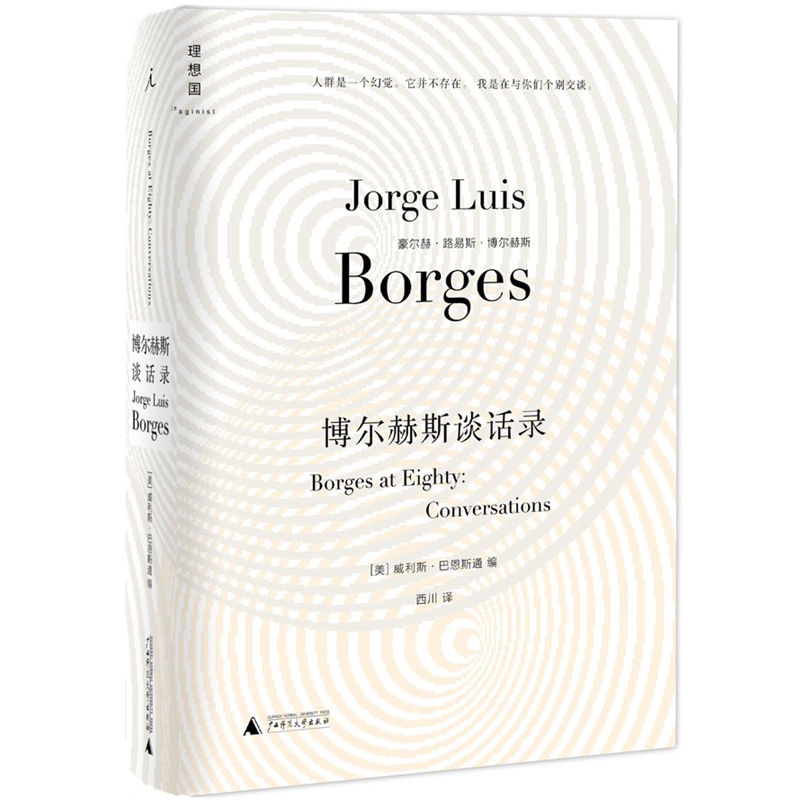
《博尔赫斯谈话录》[美]威利斯·巴恩斯通编 西川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博尔赫斯是享誉世界的阿根廷诗人、作家、翻译家,美洲西语文学的最重要开创者。创作风格深邃博学,独树一帜,尤以融现实于虚构而臻于神秘的迷宫式构思著称。而博尔赫斯的谈话,与他的作品一样深邃智慧,历久不衰。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他游走四方,口授诗歌、寓言和故事,在旅行和闲谈中,他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口头文学。《博尔赫斯谈话录》收录了他上世纪七十年代两次美国之行期间接受访谈的记录结集,展示了他“惊人的坦率、困惑和睿智”,其中,迷宫、死亡、梦境、诗歌、友谊等主题,交织闪耀在这十一篇谈话中,使人得以一窥这位文学巨擘的心灵堂奥。
巴恩斯通为什么你想去中国旅行?你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什么?
博尔赫斯我有一种感觉,我一直身在中国。在我捧读赫伯特·阿伦·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时我就这么觉得。我多次读过《道德经》的许多种译本。我认为阿瑟·韦利的译本最好,但我也读过卫礼贤的译本和法文译本,西班牙文的译本也有好多种。此外,我在日本呆过一个月。在日本,你始终能够感受到守护神一般的中国的阴影。这与政治无关,这与日本文化是它自己的文化这一事实无关。在日本,人们感受中国就像我们感受希腊。我当然知道我永远搞不懂中文,但是我要不断地阅读翻译作品。我读过《红楼梦》,我不知道你是否读过。我读的是英文和德文两种译本,但是我知道还有一种更加完备的,也许是最忠实于原文的法文译本。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红楼梦》这部书就像它的书名一样好。
巴恩斯通请把我们带回意识之岛,回到那词语、思想与感觉的源泉,告诉我们在语言之先,在博尔赫斯铸造词语之前,博尔赫斯的意识是怎样一种状况。
博尔赫斯我想我可以说写诗或写寓言——反正最终都一样——这个过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我从未尝试过什么主题,我从未寻找过什么主题。我让主题来寻找我,然后走上大街,或者在我家里,一个盲人的小小的家里,我从一个房间踱到另一个房间,我感到有什么东西要到来,也许是一行诗,也许是某种文学形式。我们可以用岛屿来打个比方。我看到岛屿的两端,这两端就是一首诗、一篇寓言的开头和结尾。仅此而已。而我不得不创造、制造两端之间的东西。这得由我来做。诗神缪斯——或者用一种更好、更幽暗的称呼,圣灵——所给予我的就是一篇故事或一首诗的结尾和开头。于是我只好把空填出来。我也许会走错了路而原路返回。我只好再创造些别的东西。但我总是知道开头和结尾。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依我看每个诗人都有他自己的方法。据说有些作家只要有开头就能写下去,在快要结束时他们发现或创造——两个词说的是一回事——一个结尾。但是我自己却必须在知道了开头和结尾之后才下笔。我尽量避免让我的观点打扰我的创作。我只考虑寓言本身而不考虑其寓意。观点、政治如过眼烟云,我个人的观点时时都在改变。但是在我写作时我努力忠实于梦。我只能说这些。在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的作品有一种相当浓厚的巴洛克风格,我尽量模仿托马斯·布朗爵士或贡戈拉或卢贡内斯或其他人写作。那时我总是想欺骗读者,总是使用古词、偏词或新词。但是现在我尽量使用很简单的词汇,我尽量避免使用英语中被认为古奥艰涩的词汇,我尽量避开它们。我认为我写得最好的短篇小说集是最近的一本《沙之书》。在这本书里,我想没有一个词会限制或妨碍读者。这些小说叙事简朴,尽管故事本身并不平直。既然宇宙间没有平直的事,既然每件事都是复杂的,我把它们装扮起来,写成朴实的小说。事实上那些小说我反复写了九到十遍,而我却想让它们看起来仿佛不事斟酌。我要它们越平凡越好。如果你们不曾读过我的书,那么我要斗胆推荐我的两本书给你们,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能读完,仅此而已。一本是诗集,名叫《月亮的故事》,另一本就是《沙之书》。至于其他书,你们尽管忘掉好了。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会不胜感激,因为我已经把它们忘记了。
巴恩斯通在辛辛那提,当一个崇拜者对你说“愿你能活一千岁”时,你回答“我高高兴兴地盼望着死去”。此话怎么讲?
博尔赫斯我是说当我心绪不佳的时候——这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常事——我就自我安慰:再过几年或再过几天,我就将死去,到时候一切烦恼就都无所谓了。我盼望着被抹掉。但是如果我想到我的死只是一个假象,死后我还要继续老下去,那么我就会觉得非常非常难过。因为,我的确已经对自己感到厌倦了。当我想到死亡的必然性,想到死亡,我便满怀希望,满怀期待。可以说我贪图一死,我不想每天早晨爬起来发现:哦,我还活着,我还得做博尔赫斯。
西班牙语里有一个词,我想你们知道,但不知现在是否还用。在西班牙语里你不说“醒来”,而说recordarse,意思是,记录你自己,想起你自己。我母亲过去常说:“我要在八点钟想起自己来。”每天早晨我都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已经多多少少不存在了。再有,一当我醒来,我总是觉得失望,因为我还活着,还是同一个愚蠢而又古老的游戏没完没了。我不得不做某个人,我不得不做得惟妙惟肖。我有某些义务,其中之一就是活过这一整天。当然,在你年轻的时候你不会有这种感觉。依我看,人们之所以有不同的感受,是因为很多人认为不朽是一种幸福,也许是因为他们尚未意识到这一点。
巴恩斯通他们尚未意识到哪一点?
博尔赫斯没完没了地活下去这件事,可以说,简直可怕。
巴恩斯通这会成为另一座地狱,就像你在一篇小说中说的那样。
博尔赫斯是的,会成为的,是的。既然俗世生活已是地狱,我们何必还要从一座地狱走向另一座地狱,受更多更大的罪!
巴恩斯通但是你一生中显然也有过兴高采烈的时刻。
博尔赫斯是的,我想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时刻。但是我拿不准。依我看那些时刻或许比你所记得的要更美好,因为在你快乐时你会忘乎所以。人们只有在心绪不佳时才有所意识。
巴恩斯通 一个人会从白日梦走向噩梦。
博尔赫斯几乎每天夜里我都做噩梦。今天早晨我还做过一个,但那不是一个真正的噩梦。
巴恩斯通什么样的梦?
博尔赫斯是这样的:我发现自己在一座巨大的建筑里。这是一座砖造的建筑物,有很多空房间。巨大的空房间。砖砌的房间。于是我从一个房间进入另一个房间,但好像都没有门。我总是不自觉地走到院子里。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又在楼梯上爬上爬下。我呼喊,可是没有人。那座巨大的不可思议的建筑物空空荡荡。于是我就对自己说:怎么回事,我当然是梦见了迷宫。所以我也不必去找什么门,我只需坐在其中的一间房子里等待就行了。有时我醒来,我的确有时醒来。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我就自言自语道:这是一个关于迷宫的噩梦,由于我知道这一切,所以我不曾被迷宫所迷。我只是坐在地板上。
巴恩斯通等着噩梦结束。
博尔赫斯我等了一会儿就醒了。
巴恩斯通你还常做其他噩梦吗?再讲几个!
博尔赫斯有两三个噩梦我是常做的。我现在可以说,迷宫是我常做的噩梦,此外还有一个,与我的失明有关。这是一个我想读书而又读不成的噩梦,我会梦见每一个字母都变成了别的字母。当我想弄懂开头那些单词的意思时,它们便暴躁起来。那是些长长的荷兰文叠元音单词。有时我也会梦见那些文字的行距变宽,然后字母伸展出枝枝杈杈。在异常光滑的纸页上,那些符号有黑有红,它们长得那么大,简直让人受不了。等我醒来,那些符号还要在我眼前晃一阵子。于是我会想好久:我再也不可能忘掉它们了,我会发疯的。这种梦境大概常常出现,特别是在我失明以后,我老是梦见我想读书而读不成,因为文字会活起来。另外一些梦是关于镜子,关于戴面具的人的。我想我有三个基本的噩梦:迷宫、写作和镜子。我几乎每夜都做。有时在我还没有完全入睡之前我就已经身在其中了。
巴恩斯通你是个很有趣的人,博尔赫斯。你很孩子气,你会寻开心,你非常幽默。
博尔赫斯哦,不管怎么说,我应该如此。我不知道我到底长大了没有。我觉得大家都是孩子。
巴恩斯通不,我们都不是孩子了。过去,每当我心情沉重,在爱情,在一些诸如此类的蠢事上……
博尔赫斯不,不是蠢事。这类事情是人人经验的一部分。我是说爱别人却不为别人所爱,是每一部传记都要写到的,不对吗?如果你来对我说你爱上了某某,而她却拒绝了你,我就会告诉你:每个人都会这么说的。每个人都曾被拒绝过,也曾拒绝过别人。这两者支撑着人的一生。某人回绝了某人或者被回绝,这种事情始终都在发生。当然事情若发生在我们身上,正如海涅所说,我们的心情就会非常沉重。
巴恩斯通你什么时候有过恐惧感?
博尔赫斯现在我就有恐惧感。我怯场。
巴恩斯通还有别的时候呢?
博尔赫斯嗯,我对美也有恐惧感。有时在阅读斯温伯恩、罗塞蒂、叶芝或华兹华斯的作品时,我会想到,哦,这太美了。我不配读我手上的这些诗。但我也感到恐惧。在动笔写作之前我总是想:我算什么呢?居然要写作?我对写作能知道多少?然后我就自己愚弄一下自己——但我已写了好多次,再写一次也无妨。当我面对一张白纸时我也会有这种恐惧,除了写下去我还能干什么呢?既然文学看起来已经成了——我不愿意说“命运”——已经成了我的工作,而我对它又满怀感激之情。这是我敢想象的惟一命运。
巴恩斯通你可否谈谈友谊?你曾多次谈到它。
博尔赫斯我想友谊或许是生活最基本的事实。正如阿道弗·博埃·卡萨雷斯对我说过的那样,友谊有优于爱情之处,因为它不需要任何证明。在爱情问题上,你老是为是否被爱而忧心忡忡。你总是处于悲哀、焦虑的状态,而在友谊中则不必如此。你和一个朋友可以一年多不见面。他也许怠慢过你,他也许有过躲开你的企图,但如果你是他的朋友,你知道他也就是你的朋友,你不必为友谊而操心。友谊一旦建立起来,它便一无所求,它就会发展下去。友谊有着某种魔力,某种符咒般的魔力。实际上,当诗人爱德华多·马列亚写出一本名为《一段阿根廷热情史》的好书时,我自忖,那本书写的一定是友谊,因为这是我们真正拥有的惟一的热情。然后我就把书读下去,发现那不过是一个爱情故事,这让我颇感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