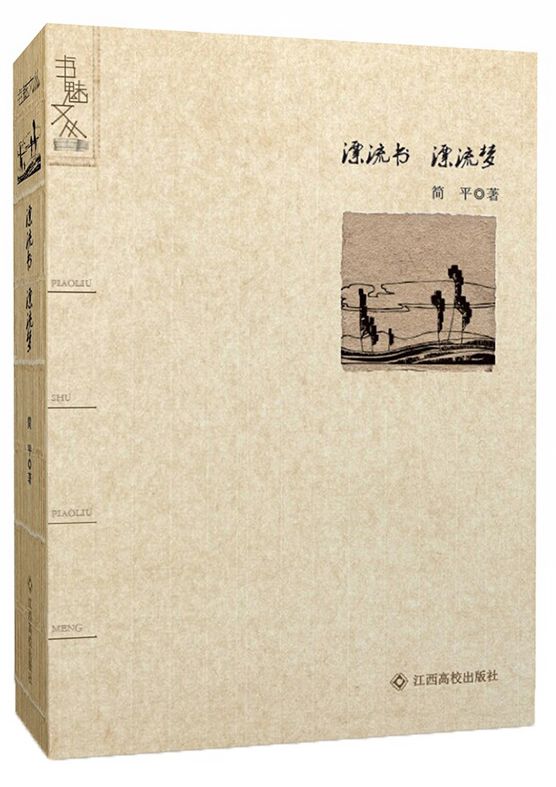
《漂流书漂流梦》简平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
简平的《漂流书漂流梦》是一部散文随笔集,集结了一百三十六篇他与书交集的散文。他在书中写到的刻苦认真的读书生活,写到的与书友交流的温暖故事,写到的阅读的心得与体会,都是他生命历程的记录,更是他灵魂轨迹的留痕。正如评论家靳逊所言:“我读这本书,感觉真诚、朴实,尤其是他驾驭语言的准确程度,实在让我敬佩。他的文章好在自然、典雅,而情趣盎然,这其中有他生命的体温,更有让人动容的生命质感。”
■简平
阿多尼斯的拥抱

作者与阿多尼斯之间生命的拥抱
2013年夏天,最让我难以忘怀的一个瞬间,莫过于与我心仪的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的热诚相拥。
其实,我只是阿多尼斯万千拥趸中的一名普通的读者。我们总是说,所有的相遇都是注定的缘分,因缘际会不是偶然。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我是在2009年的夏天,第一次读到阿多尼斯的诗歌的,“我曾浸没于爱的河流/今天,我在河水上行走。/如果爱把它的竖琴折断/赤脚行走在断琴的遗骸上/什么将会改变?/我向谁发问:/欲望的黎明或是它的夜晚?”我被这样的诗句所打动,觉着聒噪的蝉声在那一刻悄然消遁。
仅仅过了两年,我却在那个冬天跌入了寒冷的深渊。一切都来得非常突然,我毫无准备,因而束手就擒。当我从胃癌切除手术的全身麻醉中醒来,眼前飘舞的飞天在白色的背景后面,向我抛来鄙夷的目光,那一瞬,我彻底崩溃。我整天整夜地不能入睡,精神恍惚,胡思乱想,我感到日月星辰、春夏秋冬都已弃我远去。有一天,迷糊朦胧中,我忽然想到了阿多尼斯,还断断续续地记起了他在《愿望》中的一些诗行:“但愿我有雪杉的根系,/我的脸在忧伤的树皮后面栖息,/那么,我就会变成霞光和云雾/呈现在天际——这安宁的国度。”我一句一句地拼凑着这些温馨的诗行,仿佛回到了童年,像个孩子一样搭建着一层层通往遥远天际的积木。
就是在那天,我接到了来自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编辑陈红杰的电话,我向她说起了阿多尼斯,说起了那些美好的诗句,说起了我将开始创建心中的安宁国度。陈红杰在电话里默默地听着,我不知道就是在那个时候,一心想为我做点什么的她,已经在心里为了我许下了一个愿望。2012年十月,秋高气爽的一天,陈红杰再次打来了电话,她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我们社刚刚出版了阿多尼斯的一本文选《在意义天际的写作》,他从巴黎远道而来,出席他的新书发布会。我拿着他的书,跟他说,有一位中国作家非常喜欢您的作品,可他现在却躺在病榻上,不知您能否帮我达成一个愿望,为他签个名,并写上您的祝福。阿多尼斯听后,立即让我把你的姓名用英文写下来,他再用阿拉伯语写在书上,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可能他怕你看不懂阿拉伯语,所以为你在书上画了一幅图呢!”我很快就收到了陈红杰用快递发来的饱含友情的礼物,看到了阿多尼斯在书的扉页给我的独特的题签。那是一幅象形画:一只张着有睫毛的大眼睛的海豚,在水中遨游,喷出的水柱直冲云空。我想,只有内心保持着赤诚的童真和爱的人,才会有如此动人的丰蕴的想象力。
虽然我心怀感激,但我从未想过有机会当面向阿多尼斯表达我的谢意。2013年夏季,八月里最酷热的一天,我忽然得到民生现代美术馆将举办“阿多尼斯朗读交流会”,届时阿多尼斯会亲赴上海的消息。我当即便去打听了,没想到,这场朗读交流会的策划者居然是我先前的同事及好友王寅。我跟他说,我会去参加,见见我心仪的这位大师。王寅得知我和阿多尼斯的那段故事后,对我说,那你就当面向他致谢吧。在王寅的热心安排下,我得以在朗读交流会开始前,单独与阿多尼斯见了面,我对他说,我感谢您,同时也感谢诗歌,感谢生命。我说,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已经走出了冬季,在这个夏天活着见到了您。当阿多尼斯诗歌和文选的译者、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主任薛庆国先生把我的话翻译给阿多尼斯听后,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笑容可掬地向我张开了双臂,我们相拥在了一起,彼此感受着生命的呼吸和律动。王寅将这个瞬间定格在了他的相机里。
更让我惊喜的是,同样是杰出诗人的王寅,向我提议说:“你想不想过会儿在朗读交流会上朗诵一首阿多尼斯的诗歌?”我欣然答应,还有什么比用这样的方式向可亲可钦的诗人致敬更有诗意呢?我与阿多尼斯邂逅于夏天,相拥于夏天,因此,我便选了他的《夏天》——“在晴朗的夏夜,/我曾对照着我的掌纹/解读星辰;/……夏天说:/让我伤心的是——/有人总说/春天不懂得忧伤。/夏季的太阳坐在树下,/乞讨着微风。”我在朗诵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声音有些发抖,但并不飘忽,我想,那是因为,我或许对生命仍然有着些许的忧伤,但我会在阿多尼斯给予我的温暖中,坚守自己对于生命的信念和方向。
“老顽童”任溶溶
2014年4月15日,一早,我就坐上地铁,前往上海电影广场。这天上午,将在那里举行2013年度上海文艺创作和重大文化活动颁奖仪式,这是上海市政府对本市文艺创作的最高规格的奖赏。我是获奖者,同时,我知道我们儿童文学界还有几位获奖者,其中就有任溶溶先生。我很想今天能在颁奖仪式上见到他,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去,于是,我给任老先生打了个电话。是他小儿子荣炼接的,他告诉我任老先生今天不会去现场。我想想也是,任老先生毕竟是个九十多岁的老人了,出门一趟不太容易。我还想说些祝贺的话,但可能地铁车厢里手机信号太弱,电话断了。
我一到电影广场五号影棚,就见到了另外两位获奖者秦文君和张洁。我们都很高兴,因为我们都有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任溶溶先生的得奖作品是儿童诗歌集《我成了个隐身人》,同时,他也成为有史以来获得此奖项年龄最大的作家。我告诉秦文君,刚刚与任老先生的儿子通了电话,任老先生今天不会来现场了;秦文君说,她也跟任老先生联系过了,任老先生委托她代为领奖。
任溶溶先生太热爱写作了,他几乎每天笔耕不辍。我每每去探望他,总是见他坐在小小的书房兼卧室里的桌子前,两条手臂搁在桌上,身子微微前倾,而桌上摊着稿纸,他的手上则永远都握着一支笔。他跟我说:“除了写作,我还能做什么呢?”然后,他幽默地自嘲道:“其实不就是无聊,打发时光吗?”我听后笑起来,说:“你哪里会无聊,你有那么多东西要写呢。”他听了,脸色忽然郑重起来,“我还真的有许多东西想写呢!”说实话,虽然任老先生患有老年性支气管炎和哮喘病,我时常劝他多休息,但我的确又希望他能多多写作。
任溶溶先生一直说我和殷健灵、陆梅是他的“贵人”。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去看望任溶溶先生时,他向我抱怨说,自己写得很多,但可以发表的地方却不多,就是那几家熟悉的少儿报刊。我向他提议道,你可以多写些回忆类的散文随笔,这样就可以拓展发表渠道了,比如,《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又比如《文学报》副刊“世纪风”,都是需要这样的文章的,而这两个副刊的编辑殷健灵和陆梅都是儿童文学作家,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如果你不好意思,那我去跟她们说,让她们多多发你的稿子。我真的就跟她们说了,任老先生真的就开始写了,殷健灵和陆梅真的篇篇都给他发了。所以,任老先生很高兴,写作更加勤快了,除了这两张报纸,他还将同类的文章给到了其他几家报纸的编辑朋友。他跟我说:“我现在写了就寄,寄了就盼着发,最好是明天就能发出来。”我听后又笑了起来。
殷健灵身为《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编辑,每个月轮值一周,也就是说,她只能每月编发一次任溶溶先生的稿子,她真的是尽心尽力,一次都没拉下过。可是,有一次,任老先生却像孩子一样耍起了小性子。那是去年的中秋节,我给任老先生打电话祝贺节日,可他却不肯接听电话,荣炼告诉我说,他正在生气。我一听,急了,老人怎么可以生气呢?忙问究竟怎么回事。原来,他写了一篇《中秋话月饼》的文章,发给了殷健灵,殷健灵拿到后,特意安排在中秋节那天发表,还在版面上做了个头条,但是,可能由于划版的原因,不得已删了一些文字,这下,任老先生不高兴了,说是中秋节没给他吃月饼,而是给他吃了一块“豆腐干”。我听后,偷偷笑了。我让荣炼告诉他,我立刻打电话批评殷健灵,而且,还要让她请他吃饭以赔礼道歉,当然,我也会去蹭饭,不过由我买单。荣炼听了也笑了,说其实没事的,一会就会好了。我自然不会给殷健灵打这样的电话,可是,第二天,我还是与任老先生通了电话,他的声音显得很开心的,我心想,那就一定没事了,也就说起别的话题来了。不过,我真的跟他说,什么时候,再约上殷健灵一起吃饭,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在一起吃过饭了,而任老先生是位地地道道的美食家。今年起,任老先生在“夜光杯”另一位编辑贺小钢的版面上也开始发表文章了,我有些好奇,便问他怎么回事,他告诉我说,殷健灵见他写稿积极,干脆将他介绍给了其他编辑,这样,任老先生就可以一个月在“夜光杯”上发两次稿子了。
有一天,听闻儿童文学作家安武林来上海后,去任溶溶先生家索要他的手稿用作收藏,我便开玩笑地跟任老先生说,你可不能把你写给我的信给到别人哦,最好还是给到我本人吧。原来,任老先生不用电脑,写信写稿子都是手写的,他写完后,荣炼就用扫描仪扫成电子文档,然后用电子邮箱发出去。有一段时间,我们电视台想加大动画片的创作力度,所以,让我把任老先生请来开会做做参谋,也让我出面洽购了他的名作《没头脑和不高兴》《天才杂技演员》和《丁丁探案记》的影视改编版权,这期间,他写了多封热情洋溢的信,提出许多很好的建议。而我的研究专著《上海少年儿童报刊简史》在2010年7月出版后,他当即写了长长的信来,给了很高的评价。我想,这些信都很重要,任老先生经扫描用电子邮件发出后,会不会扔了呢?说起来,他的信都是随便写在用过的纸张后面的。
没想到,任溶溶先生把我的玩笑当真了,他让荣炼从一大堆纸里找出了就我研究专著一书而写给我的那封长信,然后,非常正式地贴上邮票,通过邮局寄了过来。当我再次展读这封信函时,我的脑海里重又浮现出一幕让我感动的场景。那时,他非但给我写了“表扬信”,后来,还对时任《文汇报》副刊“笔会”主编的刘绪源先生赞扬了这本书,刘先生听后,建议他写成文章,任老先生当即答应了。可是,文章才写了个开头,他就因病住院了,但他却放不下这事,一出院就打电话给我。由于他才出院,需要家人昼夜照顾,所以他没有回到自己居住的泰兴路寓所,而是住在他另一个儿子家中。他决定让我上门一趟,由他口述后续文字,我记录后再将稿子发给他。当我去后,看见他还穿着医院里的病员服,躺在床上喘着气,心里很是不安。他一边说,我一边记,有一瞬,我的眼睛都模糊了。后来,这篇题为《又看到了这些儿童报刊》的文章发表在了2010年9月2日《文汇报》副刊“笔会”上。现在,他那么当真地把这封长信的原件给到了我,除了感激,我自当好好珍藏。
还是回到2014年4月15日那天。颁奖仪式结束后,秦文君招呼我和张洁一起去为任溶溶先生领奖。下午,我刚刚回到家里,任溶溶先生就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即向他汇报上午颁奖仪式的情况,并告诉他,我们一起为他拿好了奖品,秦文君会给他送去的。他听了非常开心,忽然,他压低声音问我,有没有奖金啊?我说有啊。他追问道,那有多少呢?我说,那个红信封在秦文君那里,可我们都没打开来看过。他笑了起来,说,那又可以吃饭了。我说行啊,等到天气再暖和一点,我请你吃饭,再叫上殷健灵和陆梅。他说,那不行,得我来请客,因为你们都是我的贵人。
友情链接 |
|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 上海静安 | 上海秀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