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飞雕像
庆元党禁虽将政敌驱逐出朝,宰相韩侂胄却招来了朝野的抨击,失尽了上下的人心。与此同步的擅权,仍能听到各种反对的声音。这种情况未随党禁的开放而缓解,反而可能随着言网的松动而加剧。怎样才能保住既得的权位,侂胄有点忧心忡忡、一筹莫展。这时,有人劝他“立盖世功名以自固”,侂胄感到这是个好主意:既能转移反对派的注意力,使他们淡忘伪学之禁的创痛;而自己独揽大权、专断朝政也有了雄厚的资本,非议之声或许会随之消歇。
那么,建立什么样的盖世功名呢?北伐金国,恢复故土,这是自靖康之耻以来几代臣民难圆的梦,盖世奇功莫过于此。于是,侂胄决定发动北伐,收复中原。数十年后,有学者将这一决策与当年策动的燕云之役相提并论,认为“不度事势,妄启兵端”,“误国殄民,前后一律”,指出“小人擅朝,欲为专宠固位之计,往往至于用兵”。在专制独裁政体下,这类出于转移政治视线的动机,以民族或统一的名义,贸然将国家与人民拖入一场“不度事势”的战争,历史上确实并不少见。

▲韩侂胄画像
趋炎附势者窥测到主政者的新意向。于是,边将不时奏报金朝多有变故的消息,逢迎者也游说治兵北伐之计,其中包括久遭禁废而仍图进用的个别官员。恢复的气氛在短时间内便炒热了。
宁宗的态度并不明朗。有记载说:“开禧用兵,帝意弗善”,或许这是他在嘉泰末年的倾向;但他确也认为“恢复岂非美事”,依旧模棱两可,一无主见。然而,用兵开边决不是宁宗首先动议的,则是肯定的。恢复之议日甚一日地升温,有人对侂胄说:“自古君倡而后臣和,从来没有以人臣专大征伐的。以人臣而专征伐,诸葛亮诚然为忠,桓温、刘裕则为篡,你算哪一类呢?”侂胄默然无语。他既不像诸葛亮那样是为了汉室王业,却也绝无篡夺之志,只是为了巩固既得的权位。他将战争视为一种可以不负责任、不计后果的轻率儿戏,至于战前审时度势的见识,战时运筹帷幄的才略,显然是并不具备的。
靖康之变后,徽、钦二帝成为阶下之囚,客死金国;大好河山落入金朝之手。从岳飞那“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仰天悲歌开始,直到不久前去世的陈亮那“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的慷慨吟咏,收复中原故土,重建一统江山,始终是南宋志士仁人难以纾解的民族情结。这种情结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化解,这一时期陆游、辛弃疾的爱国诗词最能凸显这种民族情结的浓重与强烈。
这种民心,侂胄是知道而且试图利用的。在力主恢复的士大夫中,颇有才略可用之士,庆元党禁起,他们即使不名列伪党,也多摒落家居了。禁网弛解后,侂胄网罗四方知名之士入其麾下,其用意有二:一方面让这些知名之士作为他擅权的装饰屏风;另一方面,这些知名人士既是北伐所需的人才,又可作为恢复之举的号召,为其建立盖世功名所效力。

▲宋宁宗画像
陆游、辛弃疾也都与侂胄有较多的往来,另一位辛派词人刘过则成为韩府的座上客。嘉泰二年(1202),陆游应召入朝任实录院同修撰,侂胄对他十分殷勤,宴席上命宠姬四夫人弹奏阮琴,起舞助兴,然后向这位大诗人求作《阅古泉记》。次年岁末,辛弃疾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不久召赴行在,也应邀出席过侂胄在南园的会饮。辛、陆被罗致,最令侂胄得意,他俩思念故土、渴求恢复的新作一经吟成便不胫而走,久被视为主战派的旗帜和叶适、辛弃疾在政治与军事上都有深刻的认识,对战前的准备、战机的选择、战争的后果,就绝不像陆游、刘过那样乐观。然而,他们向来是主战派,当时一般人误认为他们是无条件拥护北伐之举的。稼轩自南归后,一直期待着北伐反攻的那一天,所谓“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对正在从事的伐金准备,不论韩侂胄是否别有用心,稼轩在总体上是赞成支持的。他在军事上有真知卓识,为更确实地了解金国虚实,出任浙东安抚使后,他分别派人深入山东河北实地侦察,而后亲自把侦知的兵骑之数、屯戍之地与将帅之姓名汇总绘在“方尺之锦”上。嘉泰四年初,宁宗召见他,问以盐法后,向他征询目前应否出兵伐金的意见。弃疾回答道:“金国必乱必亡,愿付之元老大臣,务为仓猝可以应变之计。”
这次召见与上言,历来被认为是弃疾支持侂胄北伐的根据。侂胄也确实做了为己所用的理解,认为稼轩在“陈用兵之利”,“元老大臣”无疑就指自己,十分欣喜,便决意开边。但是,弃疾所说的“金国必乱必亡”,并不就是说灭亡在即,他在开禧之际曾说过用兵“更须二十年”,显然认为战前准备相差尚远。而他所说的把应变之计托付给元老大臣,弦外之音即告诫皇帝不应把这一重任交给由侂胄汲引的那些轻脱寡谋之徒;也许稼轩当仁不让地把自己包括在“元老”之列,期望能在备战应变中负起重任。但宁宗不可能真正理会稼轩上言的真义。

▲陆游雕像
稼轩被久废起用后,陆游曾以诗慰勉道:“深仇积愤在逆胡,不用追思灞陵夜”,反用了汉代名将李广复出后追杀当初羞辱他的灞亭尉的典故,劝告他不必纠缠被韩党倾陷排挤的旧恩怨,而应以全民族的深仇积耻为重,为北伐抗金建功立业。辛、陆正是在北伐抗金这点上才与侂胄接近的,双方的出发点与目的并不相同,却在这点上交汇了。因此,赞扬辛、陆的爱国主义,并不等于肯定开禧北伐及其发动者;指出侂胄在开禧北伐上的轻举妄动,也不必把辛、陆等对北伐抗金的支持视为“污点”。
也许,侂胄认为,既然已争取到辛、陆等主战派代表人物的支持,赢得了社会舆论,就没必要让辛弃疾分享自己唾手可得的大功业了。不久便解除了他浙东安抚使之任,命他改知镇江府;开禧元年(1205),在北伐烽烟即将点燃的前夕,又让言官借故将他劾罢。
北伐的舆论宣传也逐步升温。嘉泰四年春夏之际,朝廷在镇江府为绍兴抗金名将韩世忠建庙。世忠指挥的黄天荡战役就是在镇江江面上拉开战幕的,而后直将完颜宗弼的大军逼进黄天荡(今江苏南京东北),给不可一世的金军以沉重打击。如今,选择在北伐前夕在这里为他立庙,显然是意味深长的。

▲辛弃疾雕像
时隔一月,宁宗下诏追封岳飞为鄂王。民族英雄岳飞的姓名本身,在南宋爱国军民心中就是恢复故土、洗雪国耻的一面旗帜。侂胄打算兴师伐金,自然有必要打这面大旗,既激励将士,又振奋民心,更抬高自己。追封制词说:“人主无私,予夺一归万世之公;天下有公,是非岂待百年而定。”追封岳飞,尽管侂胄心存私意,但确是大振民心、大得人心之举,起到了号召军民的积极作用,为即将到来的北伐赢得了舆论上的广泛支持。
侂胄利用一切机会在舆论上鼓吹北伐。开禧元年,礼部试进士,第一名毛自知就因在策论中主张“宜乘机以定中原”,大得侂胄欢心而点为状元的。这年秋天,宋廷又追赠宇文虚中为少保。虚中在建炎初置生死于度外,应诏出使,为金强留。金熙宗皇统六年(1146),金上京汉人俘虏起兵南归,欲推他为首,事泄以谋反罪处斩。开禧北伐前夕,追赠他为少保,也隐然有表彰民族节概的用意在。同时,南渡四大将之一的刘光世也追封为鄜王,光世并无抗金殊勋可言,侂胄追封他仍为“风厉诸将”。
开禧二年初夏,权礼部侍郎李壁上奏说:“自秦桧首倡和议,使父兄百世之仇,不复系于臣子的虑念。宜亟贬夺爵位,改定恶谥,示天下以仇耻必复之志。”秦桧死后,高宗赠封申王,追谥忠献。人民对他的痛恨,与对岳飞的爱戴同样深切。于是,礼部从秦桧后裔处拘取了封王赠谥的告词,追夺王爵,降为衡国公;定谥“缪狠”。谁知侂胄对同伙说:“且休,且休!”也许“狠”字触到了他的痛处,最后改谥“谬丑”。侂胄此举无非继追封岳飞后,再次在北伐舆论上制造轰动效应,这种效应也确实达到了。降封制词中“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立即成为传诵一时的名句。但时论以为:李壁所论不为不公,惜乎只斥其主和,而不论其无君,只是迎合侂胄用兵之私而已。
从民族感情而言,开禧北伐是有社会基础的。之所以失败,固然有韩侂胄方面的种种因素在,例如准备不足,措置乖张,用人失当,等等。但更深刻的原因却是:金人入主中原以后,双方随着“时移事久,人情习故”,已与南宋在地缘政治上形成了一种势均力敌的抗衡态势,谁也吃不掉谁。从绍兴末年金主完颜亮南侵,中经隆兴北伐,直至开禧北伐,不论率先发动战争的是宋还是金,从来都没能如愿以偿过,其间地缘政治的综合因素似在冥冥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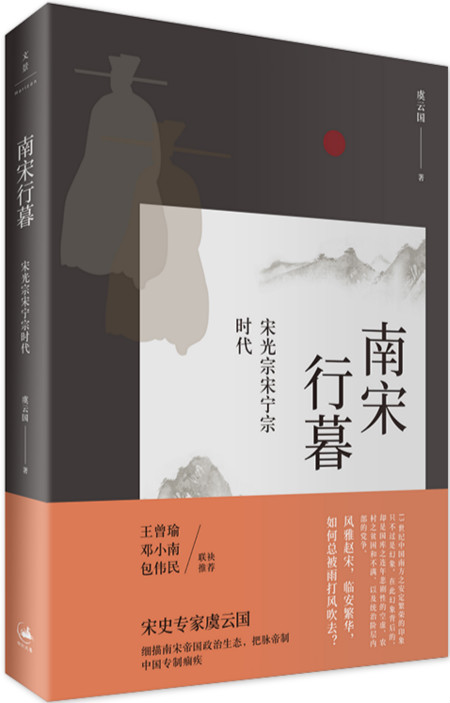
《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
虞云国 著
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版
定价:55元
倘若从稍长时段来分析宋金和战史,绍兴和议前,新的地缘政治平衡尚在建构之中,南宋若能利用岳飞抗金的破竹之势,重建类似澶渊之盟后那种地缘政治上的平衡态势并非绝无可能。及至绍兴和议成立以降,宋金地缘政治的新格局已然确立,任何一方都没有强大到足以打破这种地缘平衡,故而隆兴北伐终致无功。宋元之际,有人曾发感慨:“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循此推论,则宁宗之朝,既无恢复之臣,又无恢复之君,反顾“宁宗之为君,韩侂胄之为相,岂用兵之时乎!”开禧北伐时南宋的综合国力显然不及隆兴北伐之际,再加上开禧君相的因素,宋金地缘政治的格局不可能改变,北伐失利是无可避免的。
宋宁宗对开禧北伐的基本倾向,诚如晚宋周密所说,是“无意兹事”的。北伐前夕,他曾表示“不以为然”,内心显然持反对态度。侂胄败死,他说:“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足见他始终认为对宋而言北伐是不自量力的。然而,一方面出于“恢复岂非美事”的考虑,一方面基于他软弱游移的性格,对权臣韩侂胄一贯言听计从,没有也不可能坚持己见,去制止这种轻举妄动,反而听凭他将国运与生灵投入一场必败无疑的政治豪赌。这场战争的破坏是惨烈的,后果是严重的,“百年教养之兵一日而溃,百年葺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盖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对此,权臣韩侂胄固然难辞其咎,心以为非却听之任之的宋宁宗也应负主要责任。
——摘自《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
作者:虞云国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蒋楚婷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