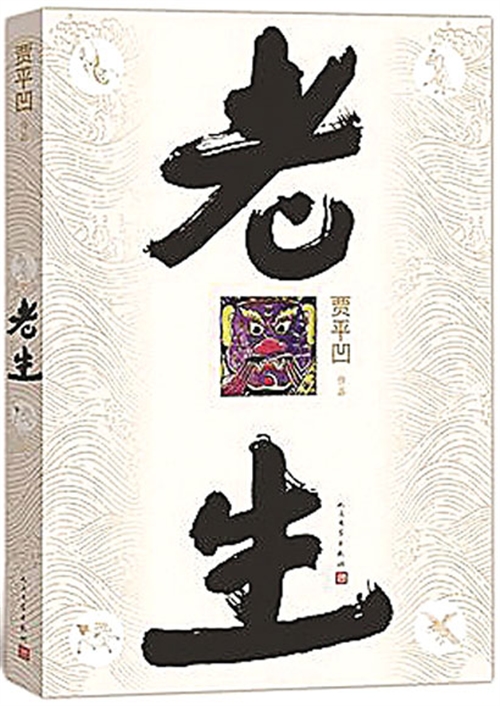
贾平凹新作《老生》。
■文汇报首席记者 王彦
“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里,人物中总有一个名字里有老字,总有一个名字里有生字,它就在提醒着,人过的日子,必是一日遇佛一日遇魔,风刮很累,花开花也疼。”这是贾平凹为其新作《老生》所撰的一段后记。“如此独特审美的语句该怎样转化为影像?”文学评论家徐兆寿的设问引发学者们共鸣,“民间写史手法的探索,小说跨越时间的长度,以及叙述风格的细琐,都让《老生》成为一部很难被改编为影视剧的作品。”
自1987年出版《商州》,到今年9月《老生》问世,27年间贾平凹共创作15部长篇小说。但其中被改编为影视剧的仅有3部,改编后成为口碑之作的更近乎为零。作为一代名家,贾平凹似乎与时下小说改编影视剧成风的潮流格格不入。
对此,在上个周末复旦大学举行的贾平凹《老生》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当今文学界紧缺的恰是敢于逆流而行,让影视剧改编无从入手的纯文学性小说。
“触电”让小说更畅销
徐兆寿举例为证:2012年中国作家海外影响力排行榜上,莫言、余华、苏童分列前三。“作家本身功底之外,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每人背后都有一部由小说改编的经典电影。”在他看来,莫言背后有《红高粱》,余华有《活着》,苏童则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它们既成就了张艺谋,也成全了作家在海外声名鹊起。
“国内书市同样如此,书店的畅销小说半数以上都有'触电'背景。”徐兆寿说,影视与文学联姻,常常能让一些作家为更多读者认识,具有更大的阅读市场,像莫言、王朔、余华、刘恒、刘震云、麦家、严歌苓等等,他们的作品随着影视剧热播在小说热销榜上扶摇直上。
影视对文学作品的推广作用不仅中国有,国外同样早有先河。美国当代电影理论家乔治·布鲁斯东就在著作《从小说到电影》中写道:“《大卫·科波菲尔》在克利夫兰的影院公映时,借阅小说的人数陡增,当地图书馆不得不在一周内添购132册;《呼啸山庄》拍成电影后,小说在2年内的销售数量超出过去92年的总和。”此外,查尔斯·韦布的《毕业生》在电影诞生前,只售出500册精装本与不足20万册平装本小说。但改编电影大获成功后,平装本销售在当年就突破了150万册。
“触电”让小说流传更深广,这几乎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反复被佐证的真命题。
剧本式写作是对文学的伤害
但真命题却叫人爱恨交加。徐兆寿旋即话锋一转:“影视剧走红了,想当编剧、当导演的年轻人多起来,而安静写作的越来越少了。”
徐兆寿的另一重身份是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他一直在留心具有文学天赋的年轻人,但学生们每每志不在此。徐教授很清楚,剧本创作接触到的是声色犬马的物质世界,而真正的纯文学是孤独的精神构建,“可惜现实面前,多数人倾向于物质。”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杨扬同样用“生不逢时”来形容现时的文学环境,“20世纪是属于作家的欢歌,文学占据绝对主力。而21世纪,图像在阅读中越来越重要。”令评论界忧思的现状是,当代年轻人的座右铭不再是文学作品里的一句箴言,取而代之的是影视剧的走红台词。长此以往,纯文学恐会为剧本式写作让位,就如同诗歌曾经的式微那样,那将是文学天大的灾难。
“灾难”是危言耸听吗?王小波的一段话可作注解,他在杂文《盖茨的紧身衣》中问道:“电影时代,小说怎么写?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几十页洋洋洒洒的文字叙述,放进宽银幕后只需几秒。电影让阅读变得轻松,既然如此,何须几十页纸?几页、几行足矣。”王小波不是独自一人,加西亚·马尔克斯终其一生都在拒绝《百年孤独》被翻拍成影视剧。“‘你委身寂静的、完美的处子’,‘你知道铁路工人罢工了吗?’即便我们不知道第一句话出自英国诗人济慈的《希腊古瓮颂》,我们仍可立即判断出——前者是文学而后者不是。前者有具体可感的质地,有特别的节奏韵律,可两者一旦搬上银幕,脱离文字,谁能分辨出纯文学与剧本?”所以,魔幻主义作家宁愿要一本五迷三道的法国新锐小说,也不接受一部《廊桥遗梦》,这是对文字癖好的执拗个性。
永远不要责怪读者变得浅薄,而要想想,是谁帮他们放低了文学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