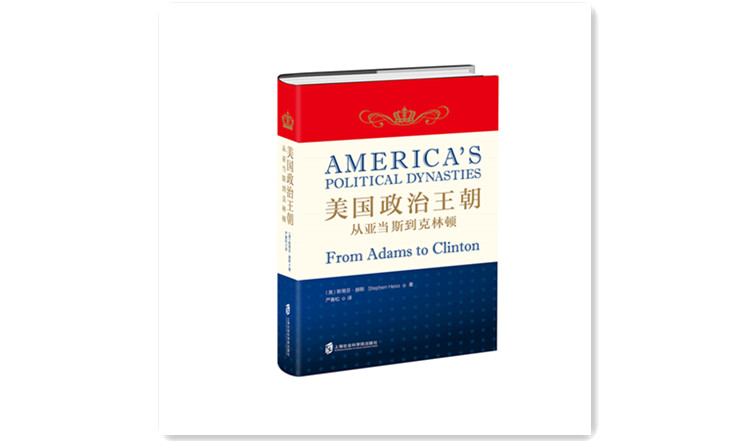
《美国政治王朝——从亚当斯到克林顿》
﹝美﹞斯蒂芬·赫斯(StephenHess)著
严春松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年8月出版
或许年轻的希拉里·罗德姆也想有朝一日去竞选总统。她在芝加哥的一个中产阶级郊区长大,这里的邻居们做梦都想变得比他们现在更有钱,但从未想过去握有政治权力。但在少年时希拉里就积极参与政治——并且是在较比尔·克林顿还小好几岁的年龄。她以赞许的态度阅读了巴里·戈德华特的《一个保守主义者的良心》,让父亲感到很高兴,后者经营一家专为旅馆做窗帘的小企业,对工会、政府、开支,以及税收等方面持坚定的保守主义立场。在1964年戈德华特总统竞选中,17岁的希拉里一户一户地走进固执而难对付的芝加哥邻居家里,仔细搜集关于民主党选民的信息,它有可能有助于通过竞选使他们失去资格。“我喜欢戈德华特参议员,因为他是一个坚强的能够逆政治潮流而动的男人。”希拉里回忆说,她将自己形容为“一个戈德华特女孩,全身一套牛仔女郎服外加一顶牛仔男孩的草帽,帽子上面饰有‘AuH2O’的口号”。同时,她慎重地强调:“我积极参加帕克里奇第一联合卫理公会活动让我的眼睛和心灵关注到他人的需要,有助于在我的信念中注入一种深深的社会责任意识。”
到1971年希拉里与比尔在耶鲁法学院见面时,她已经经历了一个从戈德华特共和党到洛克菲勒共和党到“保守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的心灵”的逐步转变的过程,而在牛津大学的比尔则经历了一场如何避免被征召去参加一场他反对的战争的思想斗争。他们不同的经历却导致了他们惊人类似的观念。比尔对参议员在康涅狄格州竞选失败的影响对他单纯的理想主义是一种打击;希拉里倒向民主党是受到她的社会正义感的驱使,但她并没有完全抛弃她早期保守主义岁月中形成的实用主义哲学。正如比尔后来回忆,他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她既重理想又讲究实际……她同我一样已经厌倦了我们这方遭遇失败,同时她将失败视作是道义德行和卓越的证明”。
他们只约会了几个星期,他们的关系就认真到足以开始指引他们的生活了。希拉里已向加州的奥克兰一家具有左翼倾向的法律事务所报了名,准备夏季到该所实习。比尔获得了一份担任乔治·麦戈文南部各州竞选协调员的工作。由于突然担心失去希拉里,比尔对“终生从政”表示绝望,他向希拉里宣布他要跟她去西海岸,假如她同意的话。希拉里深为感动,之后她不再怀疑。她明白比尔在放弃什么,即使只是为了一个夏天。比尔的决定表明他们的关系已在一个短时间内变得多么认真,它让希拉里确信把自己交给这个男人未必意味着她一定要放弃部分的自己,而可以是合伙关系。
“合伙”的概念对克林顿夫妇是一个规定性的概念。妇女一直是积极参政的家庭中的引导和推动力量,但基本上是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南妮·洛奇,老亨利·卡伯特·洛奇的妻子,对让一位参议院显要人物牢固地确立民主制信念起到了根本的作用。她称他“小指”(Pinky)。路易莎·凯瑟琳·约翰逊,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妻子,认为她不够格(她丈夫不这么认为),所以将她写的自传的名字取名为《一个无名小卒历险记》。而有人具有额外的影响,比如玛莎·鲍尔斯,罗伯特·塔夫脱的妻子,是一位老练的活动家。有些人具有超出其角色之外的影响,比如政治妻子——埃莉诺·罗斯福,毫无疑问。大量的女性为了支持她们的丈夫个人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芭芭拉·布什抽出无数的时间支持乔治·H.W.布什的事业,而且,正如她承认的,这要付出感情的代价。然而妇女的角色在宪法上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直到1920年第十九修正案获得通过才有了改变,但即使是投票权被写入了法律之后,观念仍然有待赶上。在起草宪法期间,阿比盖尔·亚当斯对约翰说,除非妇女的权利也包括在内,否则美国妇女“决心群起反抗”。她说这话的这一天,亚当斯肯定脑子在开小差。
是希拉里的密友,黛安娜·布莱尔,阿肯色大学的一位教授,写了那篇经典的文章《跨过他的尸体》,说明“至少从统计学意义上,对渴望到国会就职的妇女而言,最好的丈夫是死去的丈夫,最好是那个死亡时正在国会就职的人”。“寡妇的接替”是打算用来作为一个非争议性的占位技巧以避免棘手的党内争斗。休伊·朗的遗孀罗斯在参议院任职将近一年也未引人注目,然后悄然退下。
能用来指导希拉里抱负的榜样并不多。她崇拜的偶像之一是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她是第一个在参众两院都就职过的女人。她在国会32年的生涯从接替她丈夫的席位开始。史密斯曾是一名成功的商业管理人员和缅因州妇女组织的领袖,为追随她的议员丈夫,她放弃了她的职业,到华盛顿担任他的秘书。在他死后,她在一次取代他的特别选举中未遭反对,随后连续获胜,而且通常都是以悬殊的优势取胜。这一势头并未保持到她与戈德华特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时候,竞选中她在进入的所有初选中均告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