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7年1月,我头一次产生了一种其他年逾五旬者常产生的念头:我想向别人讲述我的故事,讲述我的经历。在这以前的10年中,我和我妻子芭芭拉以及我们的亲人,曾万里跋涉,从休斯敦到华盛顿,到纽约,到北京,然后又到华盛顿。”
在老布什自传《展望未来》的前言中,他这样交代自己写书的理由。
我是在中国人所说的“多事之秋”中成长起来的——它包括了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开始。这段时期在书中也应该有所交待,而且也应讲讲那段形成我的生活、价值观念和哲学的早期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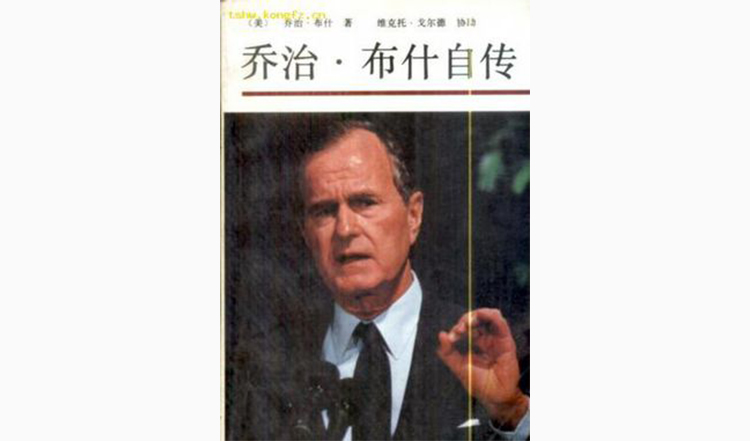
这本自传比较特殊,此书付梓之时,作者才刚刚当上总统,因此书中没有写到那场著名的海湾战争,也没有写到他任期内世界格局发生的巨变,而是有关老布什在过去十年里的“宦海遨游”,其中他在北京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的时光,是本书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1970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任命老布什出任联合国大使,老布什写道:“尼克松把联合国看作世界舆论的论坛。对他来说,联合国大使之职既是外交使命,也是政治使命。这就使得我的政治经验在他眼里成为一个长处,而不是弱点。”
中国恢复联大席位是“美国在联合国遭遇最严重的挫折”
老布什在联合国工作期间,见证了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历史大事件。
1971年秋,联合国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进行投票表决。美国试图拉拢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国家的联合国代表,一起投反对票。

老布什有些记仇地回忆道:
“有一段时间,按我们的计算我们能获得取胜所需的票数。但是临到1971年10月25日,已对我们作出承诺的选票却转为弃权。有些答应支持我们的代表没有出席会议。最后的计票结果是59票对55票,15个国家弃权。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那些原先答应投票支持我们而后却失信的国家。”
“职业外交家的标志是从不让个人的感情影响对自己工作的看法。然而,我不是一个职业外交家。我坐在美国大使的席位上,对周围发生的情况不仅感到愤恨,而且感到憎恶。中华民国,这个曾经帮助建立了联合国的政府,已被驱逐出国际社会,而这一事件却在联合国大会的会场上受到庆祝。如果这里就是‘人类的议会,世界的联邦’,那么这个世界已陷人比我想像的还要深刻的困扰。”
“台湾在联合国的日子到头了。当我看见台湾大使刘锴与他的代表团最后一次走出会议大厅的时候,我受自己个人感情的支配,离开坐位,在他到达大门前赶上了他,我把一只胳膊放在他的肩上,对所发生的一切表示遗憾。他感到他被这一他的国家帮助建立并多年来一贯支持的组织出卖了。”
老布什感觉到自己被华盛顿出卖,他提到1971年夏天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以及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华的事,他觉得“这等于是在我们要求中立国家坚持反对中国之时,我们自己对中国的立场却软化了。”
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认:
“不论我个人对驱逐台湾的感受如何,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和建立与北京的外交接触的高瞻远瞩和明智,是显而易见的。我理解总统和亨利·基辛格正在设法达到的目标。”

老布什还详细记录了他第一次接触中国代表时的情景,一场由美国礼宾专家精心安排的“偶遇”:
“因为美国还没有正式承认北京政府,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会见应该显得是偶然巧合的,而不是预先安排好的。
我坐在联合国的代表休息厅里,取了一个乔冠华(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和黄华(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进入会场的必经之地。当他们经过的时候,我站起来,热诚地而不是过分热情地伸出我的手,并作了自我介绍。
他们都与我握了手,热诚而不是过分热情。这一‘自发’的相互介绍完成之后,我们各走各的路了。然而,重要的是中国大使与我能偶尔交谈几句,因为尽管我们两国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有些地方我们有着共同利益。”
1973年1月布什从联合国卸职,接着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当时陷入“水门丑闻”的尼克松,希望利用布什的从政经验和名声,发动共和党组织的力量,为自己护驾。这是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使布什陷入美国政界互相攻击的交叉火力之中,备受煎熬。
布什认为这一段经历是“一场政治噩梦”。他很想暂时离开这块是非之地,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养好自己心灵的创伤,再返美重新谋求发迹。
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被迫辞职下台,福特继任。
福特总统邀请老布什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讨论老布什应当在新政府中担任什么角色,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抉择时刻:
“当我在椭圆形办公室作客时,总统首先感谢我作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做出的贡献,然后提到有两个重要的外交职位即将出现空缺,一个是驻英国大使,一个是驻法国大使。
但是我另有考虑。戴维·布鲁斯正打算离开他的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的职位。我向总统提出,如果允许我选择的话,这才是我所希望得到的职务。
福特在烟斗里填满烟后抬起头来说‘中国?’显然他感到惊奇。
我再一次说:中国。
到伦敦或者巴黎这些重要的使人垂涎的地方任职对前程是有利的。但去北京却是一个挑战,前途未卜。一个新的中国正在出现,在未来的岁月里,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将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仅是就美国的亚洲政策而言,就其全球政策来讲也是如此。”
毛主席对他说:“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邀请”
1974年,老布什与家人还有宠物狗来到北京。
“联络处位于北京的使馆区,它的庭院使人想起20年代南加利福尼亚的建筑风格:那日落林荫道一半是西班牙式,一半是东方式。两名穿着绿色军装的人民解放军士兵守卫着大门。”
当时,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出行工具是一辆克莱斯勒轿车。但不到一个月,老布什夫妇就决定打破过去美国使节的生活模式。
他说:“我曾想,为什么不能像中国人那样到处走走?”芭芭拉与老布什开始学中国人的样子,在北京街头骑自行车出行。

“王先生(联络处服务组组长)告诉我,他的朋友们把芭芭拉和我称作‘开路者’,因为同中国人一样骑自行车。”
那一年的圣诞节对老布什来说意义非凡,他第一次和妻子芭芭拉分开过节,老布什的妈妈和姨妈则飞来北京陪老布什。
“在圣诞之夜,孙先生(厨师)竭尽全力第一次烹制了西方节日菜肴:火鸡、桔酱及配料;不过他没做南瓜或者胡桃馅饼甜品,而准备了一道别致的中国风味的甜品,叫做‘北京粉糕’。这是一种挤上松散奶油并在上面撒满栗子粉的点心。”
老布什对孙厨师多有赞赏,他特意提到一个细节:“其他使馆没有这样幸运的条件。一位大使夫人经常抱怨他们使馆里厨师烹任水平差,中国人终于把那位厨师调走了——当然他们是不高兴这样做的。他们有好几周没新厨师来,使得大使夫人不得不下厨房。”
最特别的是,他在这一天参观了北京的防空洞。
“一位人民解放军干部和附近街道的官员在指定的路口迎接我。他们领我走进附近的一家服装店,几个货架后面安着一个按钮。按了按钮后,一个活动门便慢慢打开。我们往下走了大约25英尺,穿过蜂窝状的人行道,再穿过几个像大房间的地道。地下有卫生间,虽无通风系统,但主人肯定地告诉我,地下空气很好,并有排水设备,这个地道能容纳所在街道的几千名居民。
我们参观的是地下避弹所,即人防‘洞’。中国人在所有大城市中都在挖这种洞。毛主席曾教导,‘深挖洞’,‘广积粮’。”
1975年10月,基辛格再次访华。

老布什写到自己见邓小平时的情景:“他不停地吸烟和喝茶。他说自己是来自中国西南四川省的乡下佬和大兵。邓小平在同外国人会谈时善于运用韧和柔两手,并且恰到好处。”
21日,基辛格会见毛主席,布什详细记录了这一次令他难忘的经历:
“在10月21日的午宴上,副外长王海蓉有意识地提醒说,前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最近访问时会见了毛。这位毛的侄女补充说,希恩明确地提出了会见要求。基辛格明白了王的意思,‘如果这是正式询问我是否愿意会见主席,’他说,‘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几个小时之后,基辛格在人民大会堂同邓小平进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会谈时我看到递给邓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个中国大字。邓看过纸条后暂停会谈,宣布说,‘你将在6时30分会见主席。’
我们进去时,81岁的毛泽东正坐在一个扶手椅上。他由两位女服务员扶着站起来。这是我到中国后第一次同毛泽东会见。
我是第二个进屋的,主席个子高大,皮肤有些黑,仍显得相当结实,握手时很有力量。他身穿一套做得很好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服装。他脚上穿着棕色短袜和一双白色胶底的黑色便鞋,这种鞋就是千百万普通中国人穿的那种。
基辛格向毛主席问安时,毛指着他的头说,‘这一部分工作得还好。我能吃能睡。’又拍着双腿说,‘这部分的活动不好,走起路来没有劲。我的肺部也有些毛病。’他停了一会儿又说,‘总之,我不太好了。’
我坐在基辛格的左边,基辛格坐在毛的左边。我环顾了一下房间,一面墙上装有拍电视用的照明灯。在我们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本书法书。房间那边的几张桌子上放着一些某种型号的医用橡皮管和一只小氧气罐。
毛神态自若。他说,‘我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邀请。’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领袖竟说这样的话,使我吃惊。
基辛格笑着答道,‘不要很快接受这种邀请。’”

1975年10月毛泽东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
“会见在继续进行,毛泽东看起来更有精神了,也更机敏了。他不时地打手势,把他的头从这边移到那边,好像谈话使他兴奋起来。
会见快结束时,毛把温斯顿和我也拉到会谈中来。‘这位大使,’他对着我说,‘你为什么不来见我?’
‘那将非常荣幸,’我答道,‘但我怕你太忙。’
‘噢,我不忙,’主席说,“我不管国内事务,我只读国际新闻。你一定要来见我。’
五个星期后福特总统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时,我又见到了毛泽东,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那时,关于我即将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任命已经宣布。基辛格会见毛泽东后,我在同联络处官员谈话时提到了毛泽东说要我去见他的事情,并说我可能争取见到他。他们的印象是,这只是毛泽东的外交表示而已,因此,我就没再考虑这件事。然而,一年后——那时主席已去世了——当巴巴拉和我访华时,我向中国政府一位官员谈起毛主席的那句话。
‘你应当按照你想的去做,’他告诉我。‘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不是毛主席想那么做,他是从来不会发出那样的邀请的。’”
1976年,老布什接到华盛顿的邮报:“总统请你接受作为中央情报局新局长的任命。”
面对这份调令,老布什夫妇并不感到欣喜。
“电报中最关键的几个字是‘总统请’,我将电报递给芭芭拉,芭芭拉读完电报还给我时说:‘我还记得戴维营。’她没有说别的话,只说了这一句‘我还记得戴维营’。”
“当时的问题是水门事件,尼克松总统把我叫到戴维营,请我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处理来自白宫西厅的政治混乱。现在,总统又要我离开那个我俩都满意的外交职位,回华盛顿去接管这样一个机构——十年来,敌对的国会对它进行调查、揭发,指责它违反了法律,甚至说它无能。”
芭芭拉不愿意老布什接受调令,就像她在1973年时不愿意老布什接受去全国委员会一样。
“现在,两年以后,芭芭拉知道这次我又只能给总统作出那一个答复。我们不久将离开北京返回华盛顿。在北京工作的13个月期间,芭芭拉渐渐喜欢上了中国,还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历史、艺术和建筑。”
“一年多来,我——我们,因为芭芭拉也像我一样投入了工作——为发展中美之间互相尊重的气氛和友谊,为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民间往来,做了一些工作。我们在消除两国之间的一些引起怀疑和互不信任的障碍方面取得了进展。中国政府将会怎样想呢?当外交官的布什不一直就是那个当过间谍的布什吗?”
但是邓小平的一句话让老布什放下了心中的不安。
“在邓小平邀请的一次私人午餐上。他向我保证,中国将永远欢迎我,然后笑了笑说:‘即使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1975年12月7日,北京首都机场,中方人员送别即将继任中情局局长的老布什
自传的最后,老布什假想了一场记者采访,其中有一个与中美关系有关:
“问:你提到了对外政策,那我们就谈得更具体些吧。凭你在中国的经验,你对中美关系有什么要说的或想法吗?
布什: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就其本身来说就是重要的,而不是从有些人说的美苏关系中‘一张牌’的角度说它重要。当然台湾问题必须和平解决,但那个地区的紧张局势现在已不像过去几年那么严重。此外,还有各种理由应当使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在未来年月中发展和顺遂,因为这在战略上、文化上和经济上对我们两国都是重要的。”
1987年,在老布什当选美国第41任总统之际,这本自传也写完了。
这位出使中国又四次访华的美国总统,曾在联合国反对中国恢复席位,后来用自行车丈量北京,他从敌视到了解并且爱上了中国,深为中国人民所熟悉,2018年11月30日,老布什离开人世,享年94岁。
编辑:周辰
责任编辑:叶松亭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