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座是瓶子堆积的塔,一座是玻璃墙幕的高楼大厦,当两座塔遥对,会蔓延出怎样的故事?日前,作家胡小远携新书《玻璃塔》做客沪上思南读书会,和评论家程德培、出版人章德宁、作家程绍国探讨《玻璃塔》的创作缘起。
《玻璃塔》的写作始于上世纪末,写写停停前前后后历经17年打磨,期间每次改写都几乎是大篇幅推翻重写。但胡小远笃定地说,长篇小说就须得慢慢写。
程绍国还记得,自己读完《玻璃塔》后,曾给当时在柬埔寨行走的胡小远发去了一条长长的短信,感叹小说独到之余还提到很难懂。的确,《玻璃塔》的文风相对晦涩诡异,但在评论界看来,恰是“难懂”也体现了别致之处。“阅读小说《玻璃塔》对读者来说是一个考验,而一旦读完了,会给人一种杂花生树的感觉。”

在胡小远的创作理念中,小说的辨识度极其重要——从故事到语言都须避免同质化。“在书写中创造一种陌生感,从一开始就是写这部小说的动力,为此须得有牺牲。即便写作失败了,也须如颓败、坍塌的吴哥窟,坚韧地残缺在丛林中,这是作家的命。”
程德培认为:《玻璃塔》主张虚构主义、坚持实验精神,敢于自设难度进行创作,冲破模仿论的牢笼,体现了作家对文学本体的追求。“这部结构主义长篇小说,就像是找个篮子把一些看似没什么关系的东西都装在了篮子里,让篮子里的东西互相之间产生联系。小说中的人物很有特点,都是背对着或者侧对着我们的,很少有正面向我们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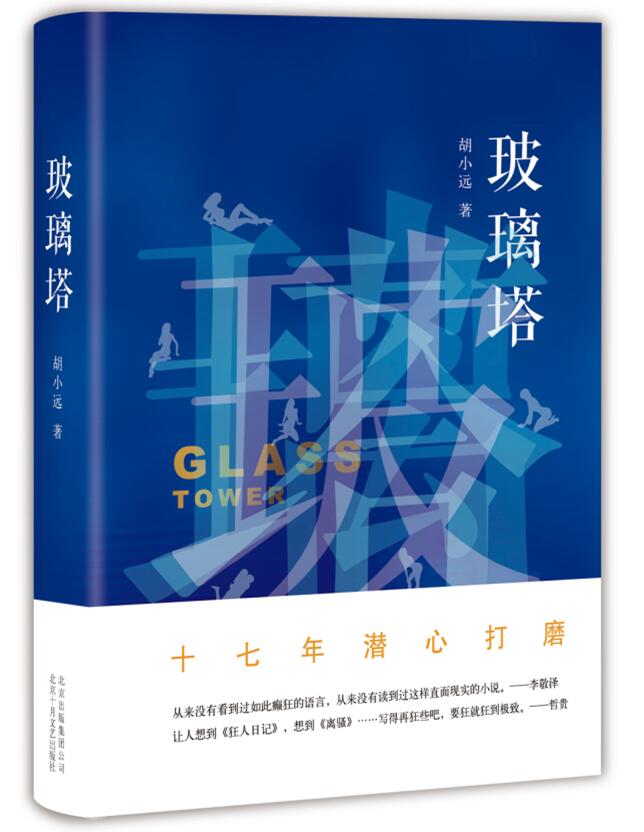
《玻璃塔》
胡小远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在中国悬疑小说的谱系中,《玻璃塔》别具一格,作品叙述空间定位在南方都市和渔村,渔民的生活场景、新奇的渔事渔歌令人印象深刻。作品在现实题材的基础上,加入了部分魔幻想象,比如马龙拥有异于常人的听觉和人鱼互变的特异功能,作为诱鲨人常年生活在海底;马江贵被乌铳袭击,变身大黄鱼逃难海中等,场景瑰丽而莫测。
在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章德宁看来,胡小远在《玻璃塔》中创造出一套新鲜语词,极力制造陌生感,书面语、口语、网络用语、方言土语、现代汉语、古汉语、外语杂糅其间,建起一座语言编织的迷宫。时而极简凝练,时而繁复拗口,时而幽默俏皮,“小说的语言充满动感,如一部多声部的立体声的交响,雄浑壮阔”。

<<<<延伸阅读【创作谈】
小说不应被动地写实,要自主构建私人空间
文/胡小远
写《玻璃塔》始于20世纪末,写写停停花了十多年时间。写好了给敬泽看,他那时在《人民文学》当主编,又在中国作协书记处兼差,两头跑。他这么忙还是看完36万字,在自己家附近找了菜馆做东,一起饮酒谈稿。敬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癫狂的语言,从来没有读到过这样直面现实的小说”,又说,小说叙述的“位置一直很高,有时得低下来,这样才能不隔,不隔才能贴”。
都是很要紧的话,“贴”,是奇诡幻丽时顾及日常细碎,于外相中契入内里。他建议弃用家族小说构架,说“这部小说用案子贯穿到底是聪明的”,不赞成太多小说采用家族或年代线性结构,认为这是艺术的偷懒,小说不应被动地写实,要自主地构建私人空间和意义世界。他还认为小说的不好看,责任不在读者而在作家。
《玻璃塔》与案子搭上关系是肯定了 。但纯文学写案子,与推理小说、悬疑小说既同又不同,纯文学作家写案子不很专心,总要把心思用到其他地方去。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都写到案子,关注点却总是落在复杂的人性上。类型小说以故事引人入胜,经典文学中的聂赫留朵夫、玛丝洛娃、拉斯柯尔尼科夫、苔丝、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其性格和精神的复杂丰富,是类型小说人物难以企及的。纯文学写案子,是要挣开案情束缚,指向多棱意义空间的。
《玻璃塔》中的案子与塔相关。两座塔,两个案件。两座塔都是玻璃塔,一座塔由瓶子垒成。是毫不起眼的小玻璃瓶,庙堂草根各种人等,于瓶里瓶外极尽所能。瓶中人要走出瓶子,瓶外人则封住瓶口,便有了用瓶子垒成的塔。另一座塔通身裹着玻璃幕墙。是频换楼主的摩天塔楼,表象现代,骨里古老。
写到这里,又想起朝垠先生写的“双塔遥对,引领呼应”, 《琴缘》中的遥对是平和纾解的,是人在落寞绝望中不得不领悟的虚空和豁达。《玻璃塔》不这样,《玻璃塔》中的遥对要尖锐许多,戏谑不羁的语言与魔幻绚丽的画面,多重建构交织纷杂,展现了人性内部以及人与自然与生俱来的敌对与抵抗,最大可能地抵近种群的历史宿命和当下处境。
小说的辨识度是极其重要的,从故事到语言都须避免同质化,这是最基本也是最要紧的书写要求,并非越过边界的野心。《玻璃塔》试图用饱满有力的刚性写作,颠覆南方小说固有的阴柔黏涩。《玻璃塔》语言混搭多样,不排斥行内弃如敝屣的成语、形容词,不拒绝同道避之不及的方言、网络语。《玻璃塔》容纳各种色彩,无论这些色彩是外向的光或内敛的影。
文汇记者:许旸
编辑制作:许旸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