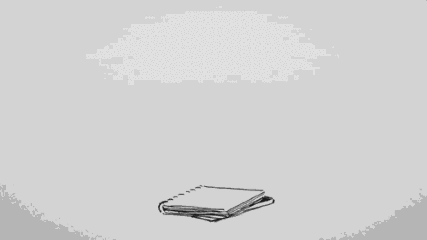
人生海海,每个人的心口都拥着故事。李昕做了一辈子编辑,经手图书两三千,编的都是别人的故事。像他这样阅历的人,走仕途或下海,生活也许更好,但李昕却有自己的选择。“作为一个爱书的人,生活也不差,我满足了。”
作为受保尔·柯察金影响的一代人,人生握紧了拳就不会轻易松手。近日,出版人李昕来到上海图书馆,做书的故事一页页翻开。40年过去,白色在头顶冒出来,谈起做书的日子,他声色爽朗快然,当年清华园里那个爱读书的北京青年分明还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编辑这活儿他是真心喜欢。

给我三年时间,做不成编辑就去当政工干部
30岁之前的十年李昕在东北度过,田地里干农活,挣工分,不下田的时候就看书。1978年,考大学的机会来了,离开庄稼地,坐进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教室。4年后的夏天,他舍弃了留校、赴美的机会,申请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
当编辑是一番自我剖析的结果。自认“才”比不上同学如王家新、高伐林,“学”比不上杨胜群、乔以钢、於可训等,唯有“识”,也就是对作品的判断力、鉴赏力和眼光,“或许不输给其他人”。
就这样,他返回北京,走进朝内大街166号那幢朴素的灰色大楼。
刚进人文社,得到岗位不是编辑,而是人事处政工。一天在大食堂,忽然远远瞥见一个独自吃饭的背影。定神看了几眼,端着碗就坐过去了。原来此人是人文社总编辑屠岸,一向以风度儒雅著称。李昕看他面容和善,张口告诉屠岸,自己“遇到了人生重大问题”。
“我来出版社是为了当编辑,可现在一天编辑没做就要改行,我不甘心。我知道在人文社当编辑不容易,请您相信我有自知之明。如果三年之内,我不能成为一个好编辑,那我一定主动去做政工干部。”
屠岸放下碗筷聚精会神地听。听完伸出一个手指头,目光炯炯地盯着李昕:“一言为定。”后来的事情证明,这四个字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
如愿做起编辑果然顺手,看到好的选题即刻两眼冒光。进入编辑部,一上手就是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等书,《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成为80年代中文系大学生的必读书。刚接手做《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时,为了和唐弢探讨书稿中的遗留问题,他找来了国內出版的四五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以及海外学者夏志清和司马长风的著作,进行对比阅读,试图发现问题。
从一开始,李昕就没有把编辑当成简单的案头工作。好书的出版,是在编辑与作者不断商榷、改良中产生的。日常工作平移到家中,小小房间床头摊得全是书;骑上自行车去敲名家的门,约稿的对象从蔡仪、朱光潜、李泽厚到王蒙、刘宾雁、刘再复,不论资排辈,都郑重其事。
为了促进文艺观念更新和理论创新,和同僚挑灯夜战,编出不少具有百家争鸣姿态的丛书,在文艺界耳目一新,也获得了老编辑的信任。3年以后,李昕做了编辑室副主任。36岁时,做了编辑室主任。从那个时候开始,编辑成了一生的职业。80年代中期出国潮,时任清华大学外语系主任的父亲联系好了美国的大学,他不走。90年代下海潮,赚钱机会就在眼前,他也不走。曾经的下属成为千万富翁,每年请他吃饭。李昕笑问:“你小子,当初咋不带上我玩儿?”
这当然是个玩笑。在回忆录《做书的日子》里他写道——“衣带渐宽终不悔”“一生只为一事来”。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小说出一本畅销一本,好像整个社会都有用不完的精力,花不光的求知欲,文字像不同方向飞射的光束,擦出火星。莫应丰的《将军吟》、古华的《芙蓉镇》、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小说,总能引发大探讨。90年代,新技术改造下,传统的图书生产模式向现代的图书生产模式转变,书籍设计挥洒自如。一本书的热卖,不是件挤破脑壳的事。
李昕赶上了这个时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了14年,被培养成一个训练有素的编辑,以做好书作为理想,不太计较经济效益,成果总是大卖。
李昕常常说,一个编辑需要一个好平台。“你的领导不想出好书,光逼着你去赚钱,这样的平台很可怜,一辈子能做成什么事?”
编辑行当里最重要的,是胆识和执着。眼光好不好,体现编辑的本事。一点点打磨质量,一点点塑造品相,让它变成读者想要翻开的样子,得靠这行当里十年如一日的摸索。
1996年,李昕调任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市场狭小,商业却发达,出版运作与内地相比难度大多了。”前后8年,李昕像在深井里游泳,水既深又冷,然而一旦抵岸,那就是十八般武艺。
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香港,从图书出版到经营管理,李昕迅速积累着经验。作为出版社负责人,全局的视野意味着更重的担子。1998年,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来了。一两年中,香港多家出版社接连倒闭。“在那种环境下,年底一算账,赔了钱,只有炒人。人炒光了,出版社就关门大吉。”
香港三联也在困难中压缩着,但坚决保留编辑力量。李昕明白,编辑人才是最难寻找和培养的,一旦编辑队伍散了,出版社就像失去了骨头。
记不清多少不眠之夜,用使命,智慧、胆识和担当围聚起来的出版社渡过难关。香港三联的出版家们用增加多品种、低定价的小书,分散了出版风险;把图书的编辑和制作向内地转移;最后,坚定地把功夫下在有地域特点的文化上,从电影、戏剧、文学、绘画、建筑、音乐到邮票、钱币、明信片无所不有,出版社成为香港社会的玲珑投影。
8年中许多苦恼,难与外人言。那些年,李昕的脑中常常出现三个幻想——第一个幻象,是小孩子搭积木,已经很高了,但仍忍不住往上加。每加一块,又担心倒下来;第二个幻象是小孩子骑自行车,车闸失灵,无法停下,不能下车,于是只能左右蹬车维持平衡,前景凶险;第三个幻象是小孩子放鞭炮,第一个不太响,第二个还是不够响,总想放一个惊天炮,于是仍然忍不住要继续放。
离开摇摇欲坠的险境,也渐渐离开闪耀夺目的光环。2005年冬天,李昕回到北京,这次报到的地址是北京三联。回忆那段变迁,他念出了苏轼的名词《定风波》: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在北京三联,从副总编到总编辑,相继又有一千多本图书从他手中上市。赞誉反馈回来,化作安定与满足,令他更为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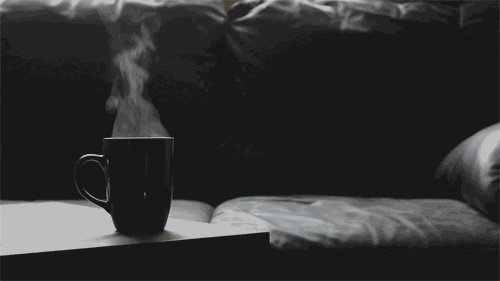
40年后再提笔,难忘的是那些书和人
2014年退休以后,李昕花了一点时间,写下自己出书的往事。今年春天出版的散文集《做书的故事》,一半写人,一半谈书。在流行“最美图书”的今天,这本书朴素得像泥土里刚长出的叶子。翻开,40年丰沛历程化为平实的叙述,道出脑海中的书和人。这体现了李昕所关切的一面: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录,和自己对时代、社会和人的观察与反思。
文学史家杨义至今都认为,若不是李昕当年促成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版,自己早就放弃了做学问。那年他只是个三十几岁刚毕业的研究生,花了5年时间写出《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一个人,厚厚一摞50万字书稿,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事情。看完后,包括李昕在内的几个编辑都赞不绝口。只不过三卷全部出版共150万字,赔钱是一定的。社领导给李昕派下任务:把书变成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写的书,上来就要做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谈何容易?”李昕回想当年,初生牛犊不怕虎。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名义盖上公章写一封推荐信,又找了唐弢、王士菁、严家炎、樊军等四位专家写推荐,蹬上自行车就去了国家教委教材中心。
没请吃饭,没送礼,甚至连一声谢谢也没有说过,心里也没敢抱希望。谁知半年后,忽然国家教委就来了一份公函,里面盖了大章子,事儿就这么成了。杨义一下就解决了后顾之忧,学术道路一片坦途。很久后李昕才知道,杨义十年磨一剑,把前途都寄托在那50万字上,如果不能成书,他大概会去做商人。
值得一提的还有与李敖的交往。从1989年引进《独白的传统》开始,李昕与李敖的合作、交往超过25年。因为主题问题,出版历经曲折。李昕说李敖是一个老顽童型启蒙思想家,吹牛的大话都别有一番深意。编排李敖的故事、与其人打交道,都是考验“情智双商”的事。直至后来写下《李敖登陆记》,重新勾画出一个被“狂狷”“争议”等词所遮蔽的李敖,这个李敖拥有另一面——敢爱敢恨,江湖义气,知恩图报,达观快乐。

▲《做书的故事》,李昕著,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
做书与阅人是不可分开的。提到杨绛,想到的是三件对杨绛先生心存歉意的往事,让他深感为人严谨与公正的重要性;提到王鼎均,念念不忘的是深入灵魂的笔触和史诗般的百年史,让他下定决心为这位长期被中国文坛忽略的文学大家正名;提到马识途兄弟,在出生入死、彼此反目的时代,两兄弟手足情深不改让人难忘;提到《巨流河》,感慨齐邦媛的微言大义与家国情怀……
透过李昕的叙述,不难看见岁月变幻中编辑心中坚定的愿望:让真正说真话,写真事,抒真情的人和书,走向大众,流传后代。
李昕说,对于作者,是绝不敢谬托知己的。即使这样,也能和这些作家和学者一起推开启蒙思想的大门,无疑获得了太多的乐趣。“是这些人,这些书成全了我一个有价值的人生,我无疑是幸福的人。”
最乐此不疲的一件事,就是此生与书相伴。他二十岁的时候,没带多少行李,硬背着一筐书去了东北。干完农活,太阳下山,草草地吃点晚饭,长夜只留给自己和书。从《草原烽火》《苦斗》到《悲惨世界》《第三帝国的兴亡》,芳草环绕的土屋中,一片灵思泉涌。
四十多年后,仍然热爱对人类思想启蒙有益的书,从读者变成编者。被思想的光照耀着,便不会迷茫于缺陷的现实,而能顺着光寻索。当年求知的少年变得愈发有力量,也让知识的启蒙散布更远的地方。一代又一代,寻索中的年轻生命看到星星点点的理想之光从书中升起,好像汪洋之中遇到一艘船,船头站着一个眼神明亮的老船长。
作者:李思文
编辑:李思文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