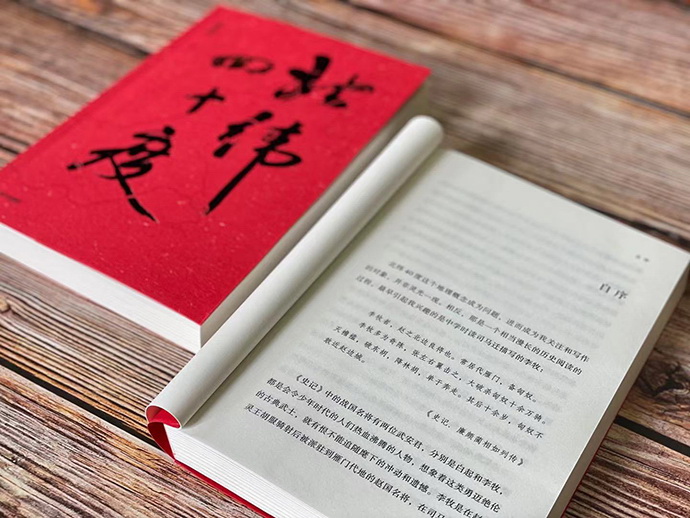
对中国而言,“北纬四十度”是一条神奇的地理带——在它的南方,男耕女织,安居乐业;在它的北方,飞马驰骋,自由奔放。不同的族群、文明通过那一条地理带,相互打量着对方,想象着对方,也加入着对方。
相较于历史记载,文学书写如何抵达这条地理带?近年来文学批评家陈福民陆续在《收获》专栏发表一系列随笔,围绕以长城为标志的“北纬四十度”地理带,“打捞”延展出赵武灵王、汉高祖刘邦、李广、卫青、霍去病、王昭君、刘渊、孝文帝拓跋宏、安禄山、王振等历史人物故事,融入对“民族竞争与融合”的思考,悉数收录进新书《北纬四十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陈福民发现,北纬四十度正好和中国的万里长城基本重叠,“定居于北纬四十度以南的汉民族多次修筑长城,在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交壤的地方,御敌于国门之外。有两次例外,一是蒙古人建立元朝,一是满清入关。只有在这两个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一统中国时,长城失去了抵御外敌的意义。在元朝和清朝之外,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朝代都在修筑长城。”日前,他在沪上思南读书会现场谈到,过去讨论北纬四十度,讨论长城,“多是侧重冲突的,封闭的、对立的存在。从汉匈之争开始,打来打去,但我认为那其实是一条文明交流的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华夏文明是极具包容性的文明,写作也是希望拓宽我们今天对中国和世界的理解。”

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直至17世纪尾声的康熙皇帝,书中所处理的题材,历史跨度很大,话题容量繁巨。“读历史需要很缜密的心思,既要条分缕析,又需要插上想象的翅膀,在更广阔的空间合理想象推断,特别是给历史典籍中的古代人物拓宽容纳的空间。我们读历史,要对历史抱有一种同情,这是文学的强项。”比如,他将司马迁对李广的书写定义为“失败者之歌”,此人基本没有打过胜仗,经常丢盔卸甲损兵折将,但即便是失败者的悲情故事,司马迁特别同情李广,在李广身上投射了自己的情怀。“这也是文学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评价,《北纬四十度》中不仅有大量案头阅读,还有作者真正的实地行走。“他用文字在纸上建起一座文明的长城、文化的长城。书里很多地方作家都去过好几次,从饮食、服装,到文化、艺术、边塞诗等方方面面,写出了他沉甸甸的感受与思考。”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金理观察到一个现象——近年来,非虚构写作升温,大家似乎觉得以小说为代表的虚构门类很难回应急速变动的时代,或是跟公众生活对话,“非虚构给文学输血,文学又能够为非虚构带来什么?”他认为,《北纬四十度》的非虚构书写为当下历史写作作出了积极探索。
“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古代,文学这份事业的自由也带来相应难度,比如说心理分析,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的不同意义。对不少已有定论的古代人物,为什么还需要重新看待讨论?”在陈福民看来,文学可谓农业文明的产物。因为农业文明时代的价值最稳定,文学在处理价值问题时游刃有余,写出来的文学作品足以构成每个人理解世界与自我的知识。但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虚构、非虚构的变化与当下世界的变化也息息相关。
“这个变化没有把虚构的门关死,留了一半,还有一半给了非虚构。”他认为,非虚构确实能把那些鲜活的,打动当下经验的东西,作为初级知识呈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读者求知需求,“但还有一部分是情感需求。虚构如果不能跟上‘位移’,找到稳定的表达形态,就会有一定难度。非虚构就相应填补了其中的缝隙。”

他坦言,写作中要求自己基本事实层面力争不出硬伤,“不能让人家觉得文学就瞎编和虚构,那就是我给文学丢人了。无论是地理学、历史学还是民族学,都有现成的专家。如果你仅仅是想了解这一部分知识,去看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的学术著作就够了,那文学还能做什么呢?在这个前提下,我要做的,就是比他们写得好看。”
陈福民希望,找到一个渠道让高深的知识下沉,在普通读者与知识之间架设桥梁,“让冷门的知识,变成可触摸的、可感受的,同时又因文学而变得特别好玩的知识。”
作者:许旸
图片来源:出版方
编辑:柳青 汪荔诚
责任编辑:柳青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