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是可以读一辈子的》是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傅杰老师主编的《我的读书经验》系列丛书之一种,邀请了荣新江、徐俊、陈思和、陈子善和陈尚君五位在学界极有建树的学者,讲述自己读书的经历和治学的道路。五位主讲人爱书、读书几十年,所阅图书无数,深悉何为好书、如何读好书,其读书分享亦蕴含治学、树人、成才之理,能为身处信息碎片化时代的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提供有益的读书、学习、研究指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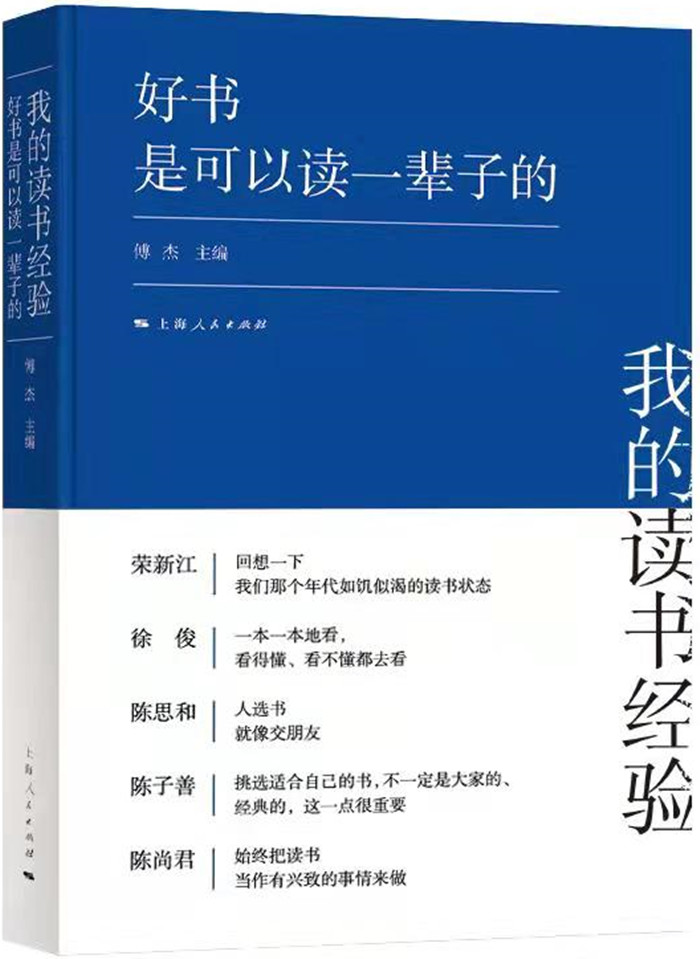
《好书是可以读一辈子的》
傅 杰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今天邀请我来做讲座,这是2021年的第一次开讲,对我还有更特殊的意义,在今年的新年,我已经是第70个年头看到太阳了。
我出生在1952年,今年虚岁70了,但是自己感觉还没有老,所以还在努力地工作,像年轻人一样。当然来讲,我对所有年轻的朋友都心怀羡慕,你们真好。2019年我给夏婧老师的一本书写序,王水照先生在宋代文学年会上说,序文里有四个字他印象特别深刻,“年轻真好”。
我现在70岁,也是可以回顾自己人生经历的时候了。有几个关键点。我中学仅仅上了一年,在务农八年以后,我是在1977年的3月1号到复旦大学的,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高考还没有恢复,所以我得到这个机缘混入大学。但是到第二年,就是1978年的3月,我就报名考研究生,而且当年是以专业分数第一、总分第二,考取研究生的。那是第一届研究生,所以我的同学都比我年纪大很多,我当时算年轻的。
这以后如何在学术上摸索一条道路,做真正有意义的工作,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最初很辛苦地爬职称,我也很特别,从讲师升副教授爬了十年,但是从副教授到做系主任,仅仅只有四年多。在这以后还做了一些自己没有预想到的工作,特别最近几年,我觉得很大的变化就是,以前我觉得比较通俗的文章,或者有一些性情的文章我不太会写,但是最近几年忽然一下子有兴趣了,写得很多,对自己也有新的看法。
我在复旦到现在为止已经是第四十四年了,觉得自己很幸运,但是从回顾人生来讲,我觉得也是充满艰辛的。
虽然我研究古人说起来头头是道,但要回顾自己人生的时候,有时我只好告诉大家,我自己也说不太清楚。因为我自己非常清楚,我在1977年第一次到复旦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学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大学是分科系的,也不知道大学是怎么教课的。
但是仅仅一年多以后,我能够顺利地考上研究生,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蜕变。
我在这里稍微回顾一下自己年轻时候的经历。我的父母是宁波人,但是客居在南通。我小的时候家境还可以,大概是六七岁以前,父母每天晚上带我去看越剧,唱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是从小有这个节奏感。以后读小学,是南通师范学校第四附属小学。
南通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现在经常会讲清末状元张謇在南通办实业,我这些年回顾,可能在南通得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南通小学到中学的教育,以及南通的文化氛围,可能都曾经影响过我。就说小学,教的东西不一定很浅,我记得小学的语文老师,曾经在1940年代做过海安李堡镇的镇长,当时对我还蛮有好感,觉得我考南通中学一定能考得中。
可能是中考没有考好,我就进了南通市第二初级中学,那个中学在南通市属于中等。那时候我很年轻,当然不懂事,但是毛主席有一句话,叫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我当时关心的办法,就是每天晚上或者我一个人,或者陪着母亲,把南通市的一条街的大字报从头到尾看过去,每天都看。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之中,南通的文化氛围对我也会有一些影响。
我自己读书,能够记得起来的,是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向任课老师借过一套线装的《水浒传》,我在小学的时候也读过线装的《三国演义》,看懂了没有,我真的没有办法回忆,就是硬看了一些有趣的故事。当时看的比较多的是连环画。
1969年的3月16号,我们一批知青响应号召到南通海门的江心沙农场——一个靠近长江边上冲击形成的小岛。当时无知到一个程度,总觉得一个岛是站在那个地方,四边都是水。到了那边以后,才从顽童的心理回到现实。最初的三年是被当地的农民管,因为这是国营农场,叫老职工管知青,所以我们真的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苦。
后来四五年,我们知青管老职工,被管着的日子很辛苦,管人的日子很高兴。我还可以和他们农村的孩子们吹吹牛。我当年曾经管过六七百亩土地,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开始叫人家下地,天天站在农场村头布置农活。
我在家里做事或者其他能力都很差,但是在农场这八年,经历了最艰苦的锻炼,自己身上软弱、脆弱、很无知的状态改变了。有些事情现在的年轻人不容易理解,我们当时可以说把自己人生的能量无限放大,体会到中国农民的艰难,和中国农民一起生活,在承担最艰苦的农活之中,经历了体力上和精神上最严酷的考验。
我这么说没有夸张的成分。我们是个大农场,农场里边有几千知青,当时劳动的艰辛,远远超过我们的能力。比方说挑担子,当我挑起担子的时候,我的腿就在发抖,但我挑着担子要走几里路,就这样我还要承担其他的管理工作。比方说我们现在拾棉花,如果现在的学生到农村去,会觉得充满着浪漫情调,但是当你是进行计分的管理,你自己负责一个单位,每天就在那里称量某一个人拾起了多少棉花,进行这样的统计的时候,人的生存可以放到最大的能量。我自己能够自豪地说,我当时作为一个知青,和农民一起工作没有任何的懈怠,自己原来的无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锻炼。在复旦的几十年之中,我对务农的经历和感受,以及生存的状态没有太多改变。中国农民的顽强和生命放大是无限的。
但是,我觉得我到农场有很多很幸运的地方,和别人不太一样。我是初中生,但是我们农场的连队,有一批是南通中学高一的学生,当时很明显感觉高一的学生比初一的学生要成熟许多。他们曾经有个语文老师做过唐宋词研究,很有名,叫严迪昌。他们那时候就经常说严老师如何如何,严老师指导他们读的书,在农场辗转就到了我这里。
在劳动的艰苦中,我身边有一批比我学问好的中学生,真是一件好事,我看到我们的差距,也就跟着读书,整整八年时间。我准确地记得,我是1969年3月16号到农场,1977年的2月26号离开的,八年差二十天时间。这段岁月,我既经历了高强度的劳动,又如饥似渴地读书,而且碰到一批很好的朋友,真是幸运。
回顾当时曾经看过的书,有一部分是1960年代以前留存下来的,比方说社科院的文学史,三册之中我当时看到过第二册,比方说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当时出了第四版修订的第一册,我看到以后很认真地从头到尾仔细地读过。在1970年代前期的时候,看到过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看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我现在研究唐诗,而且稍微有一点成绩,但是我看到《唐诗三百首》的时间非常晚,一直到20岁左右才看到过《唐诗三百首》。当时,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唐诗一百首》也曾经读到,都是知青辗转借来阅读。但是八年的时间我读书不系统,能找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
那时候有一段往事,叫“评《水浒》、批宋江”“评法批儒”,等等。虽然那时候政治运动离我们很远,我们只不过在长江边一个小岛的农场,但是这一类的书,我基本上看到什么就读什么,虽然没有去参加具体的政治运动,但把当时出版的古人原著、一些注本都给看了。那时候上海有个刊物叫《学习与批判》,现在回顾它,说是涉及政治阴谋或者政治宣传,但是它整个的风味,还是和一般的政治刊物有所不同。其中还是有一些有文学姿态的文章,或者是有文史积蓄的文章,当时我几乎每一期都看。我虽然是农场一个很基层的知青,但是当时能够看到复刊的《文物》《考古》《历史研究》,还有其他几种刊物,我都曾经订过, 我也订过报纸。那个时候凡是出的能看到的,我都尽量地去看。
很多的朋友都会问,怎么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事情。我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说,知青之中有许多非常杰出的人才,但在这十年他们的学业中止了。很多最好的年轻人前途被改变了。但至少对我来说,我认识了中国的农民,土地的耕作,庄稼的生长,从具体的技巧到节奏的把握,整个流程我都极其熟悉,我每天都在那边布置,都在那里检查,都在那里带头劳作。就算在这种生活之中,个人依然有成长的机缘。
到复旦以前,和其他的知青相比,我读书算是有一定的量,读得比较多,自学的动力是科班不能比的,但是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或者说精确度,都有很大不足。我虽然在中文系也做过一段时间系主任,但我始终知道一点,自己基础并不是很好,比方说现代汉语最简单的主谓宾、定状补,我就不容易完全说清楚,因为真的没有老师向我系统介绍过。等到我在中文系读书工作以后,又没有机缘再向人家请教。人家觉得你不应该不知道的,但我真不完全知道。
我们这代人可能有个通病,我们自学的时候,对问题的深入、对读书的渴望,那是到了别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程度。但我们的基础又普遍有限,有的时候遇到什么字会读错音, 对一些字意的理解有差别,这些知识上的出入,我们也在努力逐渐改变,但是没办法彻底解决。正因为有这一层,我觉得我算是非常幸运的,八年的农场生活,再早一点从休学开始的话,对我影响非常小。尽管劳作很辛苦,是真正地干农活,但这磨练了我的意志,增强了生存能力,也让我明白了社会上还有这样一种生存状态。这是我读书的第一个阶段。
我的幸运来得也算偶然。如果我不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到第二年全国高考恢复的时候,我是不是有能力通过高考,我没有把握。因为整个初中到高中的数理化,我只读过初中一年级,后面都没学过,要通过高考真是特别困难。但是到第二年参加研究生考试的时候,我在学校里边,可以利用学校的图书馆。我有一个系统的复习,能够把文学史上的各种问题梳理清楚。所以说我这个人,在好多方面都是被动的,不是我想如何,而是有别人在后面推动——觉得我还可以,是个人才,就把我发掘出来,把我推着往前面走。
考上研究生以后,就会发现人和人真的差别非常大。我记得很清楚,考取研究生没几天,我们系里的杨明老师,他比我大整整十岁,很谦恭地拿出了一本他整理的《龙洲集》让我指正,我一看,居然已经成熟到如此程度了,我当时还真是找不到北。
在那段时间里面,我觉得我学习能力不错,动力很足。之前在农场是找不到书、看不到书的,从中外名著到各种学术著作,都和复旦的图书资源不能比的。到学校以后,我觉得在读书上我和其他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始终认为读书是需要靠激情的,所以在复旦第一年,我基本上是以一种很傻的方式,把复旦图书馆里文史方面的书,尤其是和中文有关的,一个架子、一个架子地读,有的时候把书拿出来翻一翻,有兴趣就读,始终把读书当作有兴致的事情来做。那段时间进步非常快。
我始终是一个不太自信的人,但是推到一定程度了,也就希望自己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当时报考研究生,一听说专业课录取一个人却有90个人报名,真的很缺乏勇气。当时记得很清楚,我在学校路上碰到陈允吉老师,告诉他这个情况,我问他我能行吗,陈老师说,你的实际水平,只要好好发挥应该会有机会。考试的过程我觉得还算发挥得不错,拿到考研试卷以后,不觉得问题答不出,而是觉得这些题目出得太简单了。
出了什么题目呢?你想想看,就是出十个名篇,然后要你指出这一篇是哪一个朝代、哪一个人所作。其中有个题目是《秋兴八首》,大家都知道是杜甫作的,这十个题目每一篇的东西我都作答,比方说这一篇,作者是唐代的杜甫,他在哪一年哪一月什么地方写的我都能说出来。后来王水照先生负责阅卷——我年龄比王先生小很多,但是到复旦的时间比他早一点,那时他算是刚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引进,所以辛苦的事情都让他做,考卷也是他阅卷。他说那个地方我发挥得很特别。当时的科目里边,我外语稍微弱一点,但是外语在1978年考研的时候,是可以带词典的,我虽然外语很差,但是词典翻得很快,所以还算蒙混过关。后来辛苦的是,评职称的时候还要进行外语考试,真的是很辛苦。但是还好,我们系里的老好人是蒋孔阳先生,他当时出了一个题目,拿出来一页黑格尔原著要我翻译,我在中文系办公室里,对着词典翻译黑格尔,大致还是蒙出来在讲什么意思,所以蒋先生也给我通过了。
当时考研的时候还有一道十分的题,是谈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当时天天都在讲新长征路上如何如何,我就忘掉这一点,扣掉五分。所以我有机会到复旦,在复旦考研的时候非常顺利进入了专业的道路,是很难得的机缘,自己也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机缘。
但是讲句实在话,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以后,我很清楚知道自己不行,看到进来的各位实力超强。因为第一届研究生的时候,最大的年龄和最小的年龄大概相差近20岁,我们那一届年龄最大的是1937年的,最小的是1955年的。在学术研究上面,有一些人进校的时候成熟程度已经很惊人了。我们系里的游汝杰老师,进校以后参加过一个国际会议,他提交那篇论文的题目是《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布》,他把水稻的读音从日本到印度,穿过中国到东南亚画了一条线,用稻谷读音的语言演变现象,推测出稻谷最早起源的地方是在云南、广西还是东南亚那一带。当时我看到那个文章,惊讶到了。我还不知道方向在哪里的时候,他已经达到那一种程度了,后来知道他是夏承焘先生的内侄,有家学传承。他本人1962年俄语专业毕业,毕业以后就一直做这方面的专业研究。
我这个人最大的好处就是见贤思齐,自己不如别人,就努力补上去。1978年开始研究生学习的时候,读书的气氛非常之好。现在复旦的图书状况已经改变了,当时对大学生开放的图书馆,是现在校内进来左手理科图书馆这个位置。到了研究生的阶段,可以到现在的外办,就是1100号的地方,那边有一个比较好的完整的文史哲参考阅览室, 可以在那儿看书。1977、1978年的时候,整个校内读书气氛非常好,图书馆早晨八点钟开馆,开馆之前就已经排了很长的队,基本上一开馆马上就没有位置了。我当时用的比较多的,是复旦图书馆一楼大厅里边的古籍阅览室。那个地方基本的几套书都在,所以有机会充分阅读,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虽然说起来过程很艰苦。
回过头来说,我从1977年3月到复旦,到1978年9月就进入研究生学习,仅仅是一年多的时间,这个改变实际上和整个社会大环境有关系,1976年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大学里非常明显,可以看到努力读书的风气,大家都是意气风发,追求新的目标,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被裹挟,跟上了这样一种节奏,这样一种步伐。
陈尚君: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任重书院院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著有《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唐代文学丛考》《唐诗求是》《唐人佚诗解读》《贞石诠唐》《行走大唐》《宋元笔记述要》《濠上漫与——陈尚君读书随笔》《转益多师》《敬畏传统》《我见青山》《星垂平野阔》以及文献考订著作《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等。
——摘编自《好书是可以读一辈子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陈尚君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