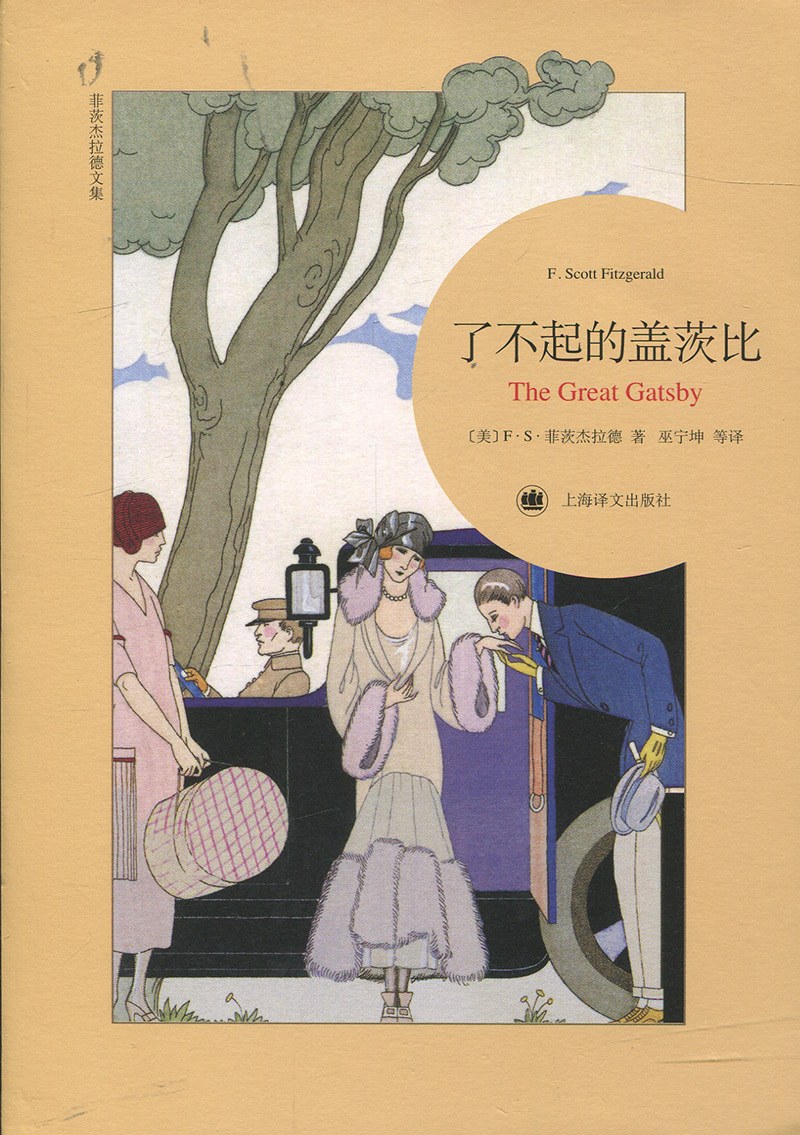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菲茨杰拉德永远的痛。
上世纪20年代初,菲茨杰拉德正春风得意。《人间天堂》的热销和评论界的追捧使他的野心不断膨胀,他渴望享誉世界文坛,更希望赚得盆满钵满来支撑他和妻子泽尔达奢靡生活的巨大开支。1922年,菲茨杰拉德着手策划他的第三本小说,一部能让他名利双收的作品。7月,在跟他的编辑马克斯·伯金斯的通信中,菲茨杰拉德第一次透露了他对新作的期待:“我想写点不一样的东西,一部非同寻常的、美妙的、简约而精致的作品。”此时的菲茨杰拉德还是流行杂志的热门作家,不断大获成功的短篇小说创作经验使他深谙作品畅销的秘籍:“一个作家该为谁而写?应是他同时代的年轻人、下一时代的批评家、以及之后不同时代的中学校长。”1924年8月,旅居法国的菲茨杰拉德在南部小城圣拉斐尔完成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初稿,在寄给伯金斯之前,他又花了两个月对它修改,从故事架构、情节设计、到场景描写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用菲茨杰拉德自己的话来说:“我删掉重写的那些内容几乎能构成一部新小说。”

《了不起的盖茨比》曾被寄予的厚望、倾注的心力、以及精益求精的打磨,多年后已被评论界公认为成就其卓越的缘由。然而,对菲茨杰拉德而言,这些只不过加剧了小说出版后他的失望。1925年4月20日,《了不起的盖茨比》问世后的第十天,伯金斯给菲茨杰拉德发来电报:“书评反响尚可,市场销量不太乐观”。事实上,此时的评论界虽有褒赞的声音,但更多的是不温不火的评价,甚至不乏质疑。有评论称“小说读起来夸张怪异、不时显露出廉价小说的痕迹”;有人将其归为二流作品,因为“小说没有激动人心的沸点、没有醇厚与深刻的回味,作者显得有些无聊和倦怠”,甚至调侃它不如干脆把题目改成《长岛的十个夜晚》;还有批评称“小说过于散漫与孱弱,矫揉造作的刻意感会让它很快被人遗忘”;就连菲茨杰拉德的好友H.L.门肯在肯定小说人物塑造、细节描写等方面的亮点后,依然遗憾地声称“《了不起的盖茨比》难以比肩诸如《人间天堂》这样的杰作”,伊迪斯·华顿私下与菲茨杰拉德通信,指出他对盖茨比的刻画还不够“了不起”,盖茨比最终的结局也缺乏“悲剧性”,读起来更像是晨报角落上的一则“社会新闻”。市场的反应则更令人沮丧,小说出版当年只卖出了两万册出头,不及《人间天堂》销量的一半,而同年其他畅销书的销售体量都是数十万册计的。直至1940年菲茨杰拉德去世时,签约出版社的仓库里还堆着卖不出去的再版库存,要知道再版的数量仅仅3000册。

惨淡的销量给菲茨杰拉德带来的不仅是失望,更多的是困惑。在给伯金斯的信中他自我剖白,将滞销归于小说缺乏正面的女性人物、因而无法引起女性读者的兴趣;他还抱怨说小说之所以反响不好,都是书名的错。因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出版社为小说选定的题目,菲茨杰拉德对此很不满意。在他看来,相比他自己拟定的几个题目——《西卵的特里马尔乔》《通往西卵之路》《戴金帽子的盖茨比》和《一飞冲天的爱人》,《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个题目“含糊其辞且不够充分,虚饰有余而精准不足”。但菲茨杰拉德最终说服不了伯金斯和出版人,妥协接受了这个名字。
期待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让菲茨杰拉德一度消沉,酗酒的恶习再度升级。余生的十几年,他非但没被封上他毕生追求的“伟大小说家”的标签,更是几乎被市场和读者抛弃。1937年,菲茨杰拉德走进好莱坞的一家书店,当他发现书架上连一本他的书都没有,他惊愕与不解,开始自我否定甚至濒临绝望:“我厌倦透了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这个名字,一个与金钱绝缘的名字。我很想知道,人们读我的作品是不是只因为我叫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或者更可能的情况,因为冠上了这个名字,他们不愿读我的书。”
“《盖茨比》还有机会吗?如果把它加进一个畅销书系列再版发行,请一位欣赏它的人(而不是我)为它作序,能否为它赢得课堂、大学教授、或任何英语文学爱好者的青睐?它就这样死了,尽管一点都不公平,它却彻彻底底地死了,哪怕我们曾为它付出了那么多。”这是1940年5月20日菲茨杰拉德写给伯金斯的信。
七个月后,菲茨杰拉德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他不得而知的是:过不了五年,《了不起的盖茨比》成了家喻户晓的小说;仅在上世纪40年代,它就有17个新版或再版发行,并开始走进高中和大学课堂;1960年,《纽约时报》将其定义为“20世纪美国小说的经典之作”;时至今日,它已累计卖出近3000万册,单单电影就拍过五个版本。倘若菲茨杰拉德还活着,他完全可以在版税里打滚儿,而不是拿着最后一笔仅有13美金的版税支票抱憾而逝。

促成《了不起的盖茨比》命运转折的是二战。美国参战后,美国红十字会同出版社合作,推行了一项“口袋书”计划,一批篇幅不长、可读性强的小说印成了小开本,寄往美军前线。截至1945年,共计12300余册《了不起的盖茨比》被分发到了士兵手里,同是一战军官的盖茨比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
这些年轻的战士不仅被盖茨比奋不顾身的爱情故事打动,更透过菲茨杰拉德对一战后美国社会的描述,仿佛预见到他们打完仗回国后的样子——
如果等待他们的和喧嚣的20年代如出一辙,那么在一个国力兴盛、物欲横流、价值真空的社会,他们将何去何从?
如果力争上游、致富成名的梦想本身无可厚非,那么为实现梦想而不择手段、梦想成真后纸醉金迷的生活是否能够自圆其说?
如果盖茨比的执着坚韧令他们心生敬意,那么盖茨比令人唏嘘的结局是否也让他们不寒而栗?
“盖茨比相信那绿色的灯火,相信那年复一年离我们而去的令人迷醉的未来。它在过去曾从我们身边溜走,不过这算不了什么——明天我们将更快地奔跑……终将有一天——”小说结尾,菲茨杰拉德将盖茨比的故事变成了“我们”的故事,为将近一个世纪及未来若干年后的读者举起了一面镜子。
从一个恃强凌弱、暴力与腐败泛滥的世界,一种物质至上、信仰蒙尘的社会氛围,一种贪婪恣意、挥霍浪费的生活方式,“我们”若隐若现地看到了当下。
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一条不断攀爬、又不断下坠的生命轨迹,一种充满乐观与希望、却注定消逝与幻灭的宿命感,“我们”同样或多或少地看到了自己。
一定程度上,这种重现是否也印证了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最后的预言:无论“我们”多么“奋力地向前划”,也无法阻挡“逆流而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或许正是这个不免扫兴的“预言”让《了不起的盖茨比》在问世之初备受冷落,毕竟沉浸于20年代流光溢彩的人们不会相信,经济大萧条的乌云正在积聚,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世纪寒冬。或许正是这个具有跨时代警示意义的“预言”让《了不起的盖茨比》成为历久弥新的世界文学经典,一代一代的读者从中获得启迪,又在不断更迭的新时代一次次看到了似曾相识的过去。
作者:孙璐 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策划:陈熙涵
编辑:徐璐明
责任编辑:柳青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