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危险的间谍:多面特工与大国的核竞赛》
[英]弗兰克·克洛斯 著
朱邦芊 译
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这是关于德裔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的故事,讲述了他由科学家、间谍、普通人三重身份交织而成的复杂人生。文质彬彬的福克斯何以会被称为“最危险的间谍”?他最终又因何而暴露了身份?
牛津大学理论物理学荣休教授弗兰克·克洛斯以战前的纳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冷战为背景,追溯了英国核计划中的重要人物鲁道夫·派尔斯如何将福克斯带入他的家庭和实验室,最终却遭到背叛的故事。克洛斯将叙事的重心放在福克斯在伯明翰、洛斯阿拉莫斯、哈韦尔的三个时期,它们分别代表了他间谍生涯的起步、高潮和结束。福克斯的政治理念与处境是推动事件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他与派尔斯夫妇等人的温情关系,又将他的表面生活与间谍身份剥离开来;同时,各国情报机构的角力从外部促成了福克斯内心的转变,映射出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
>>内文选读
70年后,我们可以从一个与克劳斯·福克斯所在的世界全然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他的一生——也许除了一个方面:原子时代地球生命的存活可能要归功于鲁道夫·派尔斯和奥托·弗里施所预见的、福克斯和特德·霍尔帮助促成的“相对保证毁灭”。1955年,中子的发现者、“曼哈顿计划”英国代表团的团长詹姆斯·查德威克爵士对英国国会议员塔姆·戴利埃尔说:“我非常了解他们(原子弹间谍们)。我虽然不赞成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我理解他们的动机。你们这一代人可能会对他们心存感激。”

▲哈韦尔的资深科学家们,1948年。克劳斯·福克斯站于左侧。
至于福克斯本人以及决定他一生的客观环境,却仍是疑窦丛生。帮助福克斯在英国立足的冈恩夫妇是谁?他为什么在七年的间谍活动后突然招供?还有一个猜谜游戏:如果“维诺那”没能暴露洛斯阿拉莫斯间谍的身份,福克斯在英国机构中的地位会上升到怎样的高度?
首先是冈恩一家的作用,他们是福克斯在布里斯托尔读书期间的担保人和房东,并在20年后他入狱期间与他保持着联系。他们是帮助可怜难民的无辜的、爱好和平的施惠者,还是像军情五处怀疑的那样,是某些更深层次的目标的一部分?
1950年的普遍观念是,福克斯在布里斯托尔期间参与了左翼活动,部分原因是他与冈恩夫妇的关系。我读过罗纳德·冈恩的档案,得益于在那个目光短浅的时代过后半个世纪才看到这些,冈恩明显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这使他在国家处于危险时成为对立情绪的焦点,没有证据表明他是让福克斯在英国立足的长期计划中的知情方。福克斯坚持把冈恩说成是贵格会教徒,这可能是单纯地在保护一个帮助他在新家园定居的人,避免把冈恩拖入泥潭。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最大的谜团:克劳斯·福克斯是谁,他为什么要招供?关于他的性格和动机的观点似乎随着它们第一次显现出来是在哪个时代而变化。例如,最早的作品写于冷战时期,受当时麦卡锡主义盛行的背景影响,将他描绘成一个狡诈的共产主义叛徒。诺曼·莫斯和罗伯特·查德威尔·威廉姆斯更加细致入微地描述福克斯的作品则写于1980年代,其优势得益于当时的偏见少于麦卡锡时代,但他们缺乏军情五处和俄国档案的帮助。我研究福克斯生涯的部分灵感来自已故的洛娜·阿诺德,这位杰出的历史学者在福克斯的哈韦尔时期就认识他了。她坚持认为他没有得到理解,他是一个忠于自己原则的、值得尊敬的人,而这些原则既有人强烈反对,也有许多人表示认同。如何决定“对”或“错”是一个深刻的道德哲学问题,中立的界限本身就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移动。在洛娜看来,福克斯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公正审判的人。我希望能对此有所贡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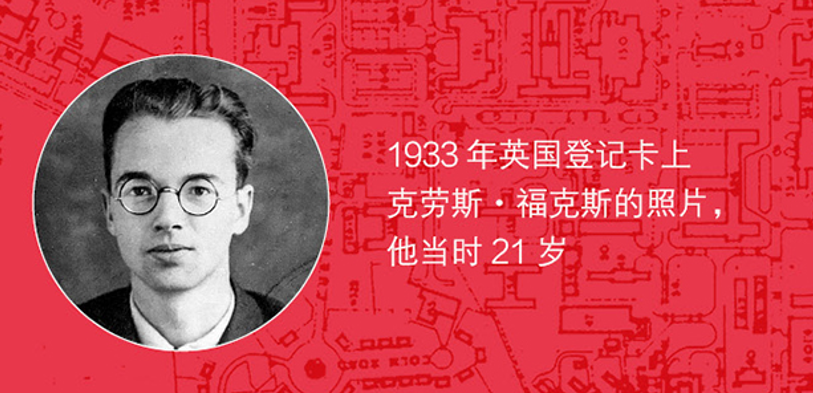 我震惊地发现约谈福克斯的方式如此轻率,而且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感觉,那就是重要的证据仍然秘而不宣,这不是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而是为了掩盖严重的错误。能说明此点的一个例子是,福克斯的家中安装了窃听设备,但吉姆·斯卡登在那里的约谈却没有记录。检方试图在审判前夕影响福克斯的辩护律师,这是一种惊人的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话虽如此,但福克斯数年来蓄意犯法,所以法庭的判决我们无法去指责。评估哪些文件要继续隐瞒,哪些可以公布的决策过程似乎是在撞大运。一方面,费米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氢弹讲座笔记仍被禁止,但在剑桥的其他场所,从洛斯阿拉莫斯,甚至从苏联本身,都可以获得这些笔记!
我震惊地发现约谈福克斯的方式如此轻率,而且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感觉,那就是重要的证据仍然秘而不宣,这不是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而是为了掩盖严重的错误。能说明此点的一个例子是,福克斯的家中安装了窃听设备,但吉姆·斯卡登在那里的约谈却没有记录。检方试图在审判前夕影响福克斯的辩护律师,这是一种惊人的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话虽如此,但福克斯数年来蓄意犯法,所以法庭的判决我们无法去指责。评估哪些文件要继续隐瞒,哪些可以公布的决策过程似乎是在撞大运。一方面,费米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氢弹讲座笔记仍被禁止,但在剑桥的其他场所,从洛斯阿拉莫斯,甚至从苏联本身,都可以获得这些笔记!
对福克斯的审判非但没有全然解决,倒是又提出了许多问题。他是否受到了公正的审判,是否被诱供?前者最好由法律专家来衡量,他们可以评估其供词的意义,他的供词是在没有任何法律援助的情况下写成并签字的,但他是否会因此而被定罪就值得怀疑了。诱供的问题是整个过程的一个主旋律,一些线索表明至少斯卡登引导了他。
我们只有斯卡登对审讯的描述,是他几天后写的,且没有独立的佐证。福克斯在接受约谈时既没有得到任何法律咨询,也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记录。福克斯后来声称,斯卡登撒了个谎,给出确保福克斯能留在哈韦尔的提议——福克斯写信给埃尔娜说道:“我只要承认一件小事,就可以留下来……”——不过福克斯在这里不一定是个可靠的证人。福克斯说,有人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劝告他不要在审判中提出这个问题,他居然就顺从了,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显然,在福克斯承认这一切之前,军情五处只是在追查“一件小事”,与他达成交易仍然存在现实的可能性。然而,当他间谍活动的深刻性质暴露出来后,角力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但有些线索表明,福克斯的声明或许有其可取之处,斯卡登的口头承诺比他书面记录的更多。首先,审判前关于诱供的讨论有记录在案,盖伊·利德尔在确信他们可能会“脱罪”时的轻松心情很能说明问题。毫无疑问,福克斯的预制板房被装了窃听器——这个决定是在1949年10月做出的,而且多次提到听见福克斯“烧火”的声音,还有周围其他动静的记录,都暗示着这些都得益于传声器。然而,斯卡登与福克斯在那个房间里的对话却没有记录,军情五处积累的日常记录中也有几页被扣下,这些都表明有一项关键的潜在证据无法为我们所用。最后,在法庭上提出阿诺德是福克斯第一次供词的来源,这要么是企图转移人们对斯卡登的注意,要么证明斯卡登的叙述有误,至少在时间顺序上是错误的。
至于审判本身,法官戈达德勋爵对“克制型精神分裂症”的说法不屑一顾。虽然这与福克斯的罪责没有关系,但既然我们了解福克斯的家庭背景,在解释他现在如何行动时就不该被轻易忽略。尽管他使用的是这个词在口语中的含义,指的是人格分裂而不是有妄想症状的严重精神疾病,但从其外祖母开始的三代人的自杀——母亲是精神分裂性抑郁症患者,而妹妹克里斯特尔也患有这种病——使得克劳斯很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倾向。他处于极端否认的状态,似乎无法认识到自己犯了大罪。克制型精神分裂症的描述可能比他自己意识到的还要真实,也是他为何能够如此成功地长期过着两种平行生活的原因。“克制型”精神分裂症也许是可以忍受的,只要它仍然受控。福克斯从来没有受到过挑战,直到1949年底,事件第一次不再受他的控制。
虽然我们如今可以比过去更冷静地评价福克斯的间谍活动,或许也可以同情他的理由,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福克斯始终都是一个兢兢业业的间谍,具有这种角色所要求的专注于此的两面性。
他把他的听众想听的告诉他们,而且只有在对他有利的时候才提供情报。例如,他向克格勃否认自己曾向军情五处或联邦调查局承认过传递了有关氢弹的情报,但实际上,正如迈克尔·佩林和弗雷德里克·林德曼所记录的那样,福克斯向英国人承认自己“说出了所知的一切”。1949年,福克斯在斯卡登的压力下,声称他停止间谍活动是因为对苏联在欧洲的野心不满,也是因为他逐渐喜欢上了英国人的生活方式;然而后来他对克格勃声称,这是由于他接触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宣传。他隐瞒证据,或者在时机成熟时一点一点儿地道出事实。例如,斯卡登和联邦调查局给他看有可能是联络人的照片时,他从来都没有指认乌尔苏拉·伯尔东(“索尼娅”)的照片,却挑出了西蒙·克雷默——福克斯知道他人在苏联,鞭长莫及。他在哈里·戈尔德显然已被逮捕之后才指认了戈尔德;在数次约谈中,他关于两人见面的故事一直在变化,有时是一些琐事,比如他管联络人叫什么,但为了保护克里斯特尔的安全,并掩盖他们在妹妹家见面的事实,也有更加蓄意的做法。
一旦怀疑落在福克斯身上,他的唯一目标就是确保克里斯特尔可以逃脱谴责。他试图坚持间谍的规则——隐瞒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联络人的身份,但失败了。福克斯必须隐瞒一个关于他本人的事实,即他开始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期,他成功地做到了。他不断提到1942年,从而污染了斯卡登、联邦调查局对他的约谈和法院审理的记录,这个时间在当时所有媒体的报道中成为根深蒂固的认知,在20世纪后来的(甚至最近的)文献中又变成了“1941年底”。然而,我们现在知道,福克斯早在1941年8月就把情报传给了苏联方面的信使西蒙·克雷默,而且他们在这之前,可能是在库琴斯基的庆祝会上就已经见过面了。不管1941年4月汉普斯特德的聚会上发生了什么,福克斯肯定是应库琴斯基之邀前往的,而且正是库琴斯基把福克斯介绍给克雷默的。此事如果曝光,福克斯也许会被指控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仍有效的时期帮助了苏联,这显然十分危险。福克斯至少在此事上设法把水搅浑了,这也许是得益于英国人无法提供证据,证明1942年之前他就在《官方机密法令》上签过字。
在他双重生活的孤独岁月里,福克斯一定花了很多时间来为有朝一日事情超出其“控制”做准备。他显然知道自己在伦敦和火车上被人跟踪了,埃尔娜对他“最近”的驾驶水平的担忧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在关键时刻从军情五处的视线中消失,比如他在两次审讯后都神秘失踪,而他和尚未摆脱嫌疑的埃尔娜·斯金纳一起离开时也无人盯梢,这些都对福克斯和监视的效率提出了至今无法回答的疑问。
>>作者简介
弗兰克·克洛斯(Frank Close),牛津大学理论物理学荣休教授和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物理学荣休研究员。曾任哈韦尔的卢瑟福·阿普尔顿实验室理论物理学部门负责人、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副主席、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传播与公众教育部门负责人。
作者:弗兰克·克洛斯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