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100年前,中国的考古事业是一片荒野,那么今天,已然是璀璨的满天星斗了。回望这百余年历程,先贤们正是从荒野出发,筚路蓝缕,融贯东西,不仅在“术”(如考古技术)的方面日益精进,更在“道”(如历史观念)的层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从而走出了一条中国考古学的独特道路。对此,近期出版的张泉《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和岱峻《李济传(修订版)》作了精彩描述,读罢令人心潮起伏,若有所思。
回望“第一铲”:初代地质人的馈赠
1921年10月27日,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挖下探索中国史前文明的“第一铲”。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在今后的日子里此举将被反复书写。张泉所著《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让我注意到,安特生是著名地质学家,曾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教授兼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3年,北洋政府创办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后升级为中国地质调查所),特聘安特生为矿政司顾问,勘探铁矿,并帮助中国培养地质人才。安特生不负所望,在河北发现大型铁矿,受到嘉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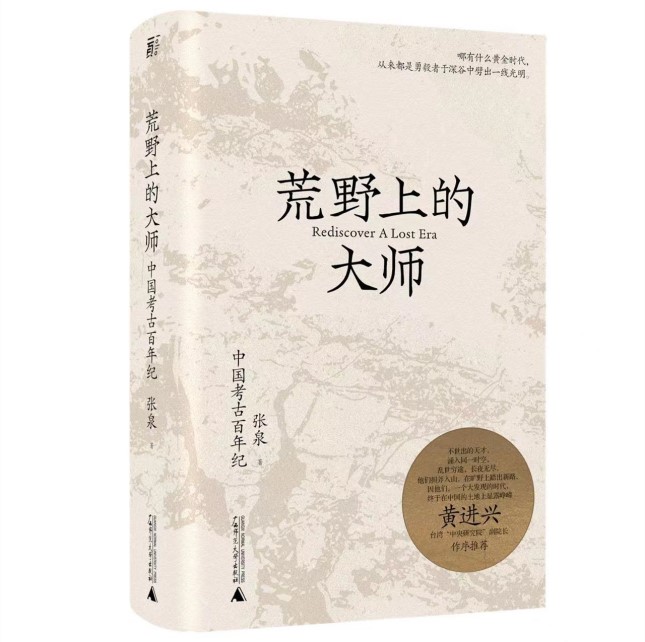
《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
张 泉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期间,安特生对地下的古生物化石产生了浓厚兴趣,进而延伸到考古领域。1920年,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寻到远古石器和陶片,提议挖掘,得到地质调查所和地方政府批准。仰韶文化就此浮出水面。换言之,中国现代考古学里程碑式的“第一铲”是由地质学家开动的。
无独有偶,安特生团队里还有一名拥有地质学背景的学者袁复礼。袁复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硕士,归国后进入地质调查所任技师,并作为中方代表参与仰韶遗址的发掘。而日后主持周口店遗址发掘,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裴文中,则是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加入的地质调查所。如此看来,这个中国第一所地质研究机构,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轫期同样扮演了关键角色。这自然与创办人丁文江的宏阔视野分不开。
丁文江,1887年生于江苏泰兴,获英国格拉斯大学地质学硕士学位,一生抱持科学救国的信念,并付诸实践。据《荒野上的大师》所述,丁文江白手起家,硬是在一片荒原上让地质学这门现代学科落地生根。尤其他为地质调查所培养的“十八罗汉”,奠定了中国地质学科的坚实基础。难能可贵的是,丁文江是位“通才”,关心的不只地质学,举凡考古学、语言学、政治学皆入其法眼,而且都能用现代学术的眼光去衡量,屡有创见。难怪挚友胡适夸丁文江是“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诚哉斯言。
有这样一位先驱,既是地质学也是考古学的幸运。试想,如果换作只知本专业的专才主持地质调查所,面对安特生“不务正业”的考古学兴趣,恐怕将大皱其眉。这“第一铲”能否挖得下去,实难预料。甚至连我国百年考古历程中神一般存在的安阳殷墟遗址,研究轨迹或许也会改变。原来最初主持殷墟遗址的董作宾,学问更接近传统金石学,过度关注甲骨,而对人类遗骸、建筑遗存、先民器物有所忽略。直到李济接手,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发掘,局面才改观。李济为哈佛博士,本行却是人类学,他是在丁文江的鼓励和支持下投身考古学,终成一代大师。

以丁文江的才情,若去国外搞科研,“大师”头衔也是迟早的。但他宁愿牺牲前途,为祖国网罗和培育才俊,奉献一生。丁文江曾向李济自剖心迹,说凭多年努力,“地已耕了,种子已播了,肥料也上得很多了,只待发芽向上长”。以李济、袁复礼、裴文中为代表的中国初代考古学家,正是丁文江这位中国初代地质人悉心栽培的胚芽。他们在茁壮成长。
推翻“西来说”:初代考古人的奋斗
李济从人类学转向考古学,是憋着股劲的。事情还要从“第一铲”讲起。仰韶文化横空出世,固然打破了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没经历过石器时代”的论断,却造就了另一种偏见。原来,仰韶出土的彩陶与中亚安诺文化中的彩陶似乎存在亲缘关系,安特生推论,彩陶工艺是从中亚经西域传入中原的。此后安特生在陕西、甘肃等地发掘了50多处史前文明遗迹,越来越多的证据让他相信推论的正确性,甚至形成了“中国文化西来说”,认为彩陶、石器、青铜、农耕等技术并非中国原创,而是从外部传入。
中国学者自然无法苟同,李济即是其中之一。据岱峻的《李济传(修订版)》,李济生于晚清、长于民初、学于美国,是那个忧患年代典型的中国学者:一方面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服膺科学;另一方面对西方话语权深感不满,渴望用掌握的新知击破西方的误解和偏见,重树中国人的信心。李济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即运用体质人类学寻找“中国人真正的老祖宗”,进而论证中华文明有相对独立的起源。这已然和“西来说”针锋相对,也为李济听从丁文江建议,“半路出家”搞考古埋下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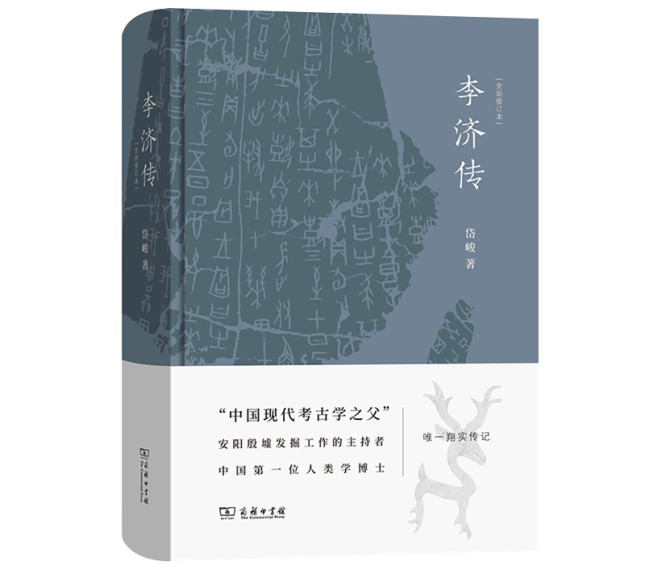
《李济传(修订版)》
岱 峻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6年春,李济和袁复礼赴山西考察,在夏县西阴村发现大量史前彩陶。其工艺之精美,远超中亚出土的彩陶,这让李济确信“西来说”站不住脚。西阴村遗址发掘也是中国人第一次主持田野考古发掘,李济又首创“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奠定了中国考古的基本方法,因此意义重大。李济“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称号亦由此而来。
1929年,李济接手殷墟的发掘工作。相比董作宾,李济眼里不仅有甲骨,也有其他文物,并且注重考察地层分布,追寻其演变脉络。1930年,吴金鼎发掘山东城子崖遗址,确定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史前文明——龙山文化。通过比对辨识,另一位考古学家梁思永按时间序列勾勒出仰韶——龙山——殷商自下而上相互叠压的地层关系,即后岗三叠层。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这一阶段,唱主角的已逐渐换成专业的考古学者。主持城子崖发掘的吴金鼎,是李济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时培养的学生。在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的梁思永,则为中国第一位接受完整训练的考古工作者。李济后来因公务繁忙,逐渐退出殷墟考古一线,梁思永遂成为实际主持人。正是他从错综复杂的地层堆积中明确了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叠压关系,证明中国历史相对连续、文化自成系列,从而有力地撼动了“西来说”。
1932年,安阳殷墟发掘报告荣获国际汉学界重要奖项“儒莲奖”,知识界一片欢腾。傅斯年认为“对外国已颇可自豪焉”,蔡元培更宣布“中国学”中心点已由巴黎转移至北平。这无疑是中国初代考古人奋斗的成果。
培养“接班人”:满天星斗的考古界
从1921年挖下“第一铲”到1932年获儒莲奖,十余年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进步有目共睹。但李济深知,中国考古学起步晚、基础弱,绝不能沉醉于眼前的成绩,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才最重要。而这件事,他早就布局了。

1925年吴宓筹建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教授,并称“四大导师”,李济则为特约讲师。当时李济只有29岁,年纪轻、资历浅,却能与四大导师并肩开课,且拥有独立研究室,薪酬待遇也一致(月薪400大洋),足见吴宓眼界不凡。李济也是满怀憧憬而来。只可惜当时的人对考古毫无概念,加之李济初执教鞭,尚需摸索,不少学生听课如听天书,纷纷打退堂鼓。结果李济实际上只指导过“一个半”学生:“一个”即龙山文化发现者吴金鼎,“半个”是古文字学家徐中舒。
1928年7月,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下辖历史学、语言学和考古学三个组。中国素重史学,傅斯年却将考古与之并置,可谓破天荒。为何如此推重考古?因为在傅斯年看来,老派学者只知埋首故纸堆,“用文字做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他呼吁学者走出书斋,“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运用新方法、新工具,寻找新材料,重建中国史。
放眼彼时的知识界,配得上傅斯年野望的就只有李济了。李济也欣然领命,自此开启了他在史语所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国现代考古学总算有了自己的阵地。
李济是这块阵地上无可争议的总指挥。梁思永是他力邀加盟史语所的,他还栽培李景聃、石璋如、胡厚宣等年轻人,即著名的“考古十兄弟”。抗战期间李济带着老父、妻女及史语所的文物、档案等流寓昆明等地。两个女儿夭折,李济怀着悲痛组织人手在西南调查挖掘,于烽火中推进考古事业。1946年他和傅斯年力荐夏鼐任史语所代所长。夏鼐乃考古界后起之秀,论理属于晚辈,李济却乐得让位,其心胸可见一斑。
事实上,李济是将夏鼐当“接班人”培养的。只是世事难料,1949年以后,两人走上了人生的分岔道。李济在台湾大学创建考古人类学系,张光直、许倬云皆出自门下。夏鼐则成为考古学界的领军人物。1979年李济以83岁高龄逝世,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然走出荒野。
当我读毕《荒野上的大师》和《李济传(修订版)》,仰望考古学的天空,看到的是满天星斗。
作者:唐骋华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