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洋鬼子——一位瑞典地质学家眼中的万象中国》一书是民国初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中国的亲历记。作者于1914—1925年受聘于北洋政府,作为地质学家帮助中国寻找矿藏,亲身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到完成北伐的巨变,也与胡适、傅斯年、丁文江、袁世凯等重要人物有直接的交往,对于袁世凯的统治,张勋复辟,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的争斗,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都有细密的观察和切身的体会与思考。除此之外,作为“北京猿人”遗址、“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者,安特生对于中国史前考古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书既包含作者对中国大历史的梳理,也有他作为亲历者对中国社会变革的记录与反思,对于研究当时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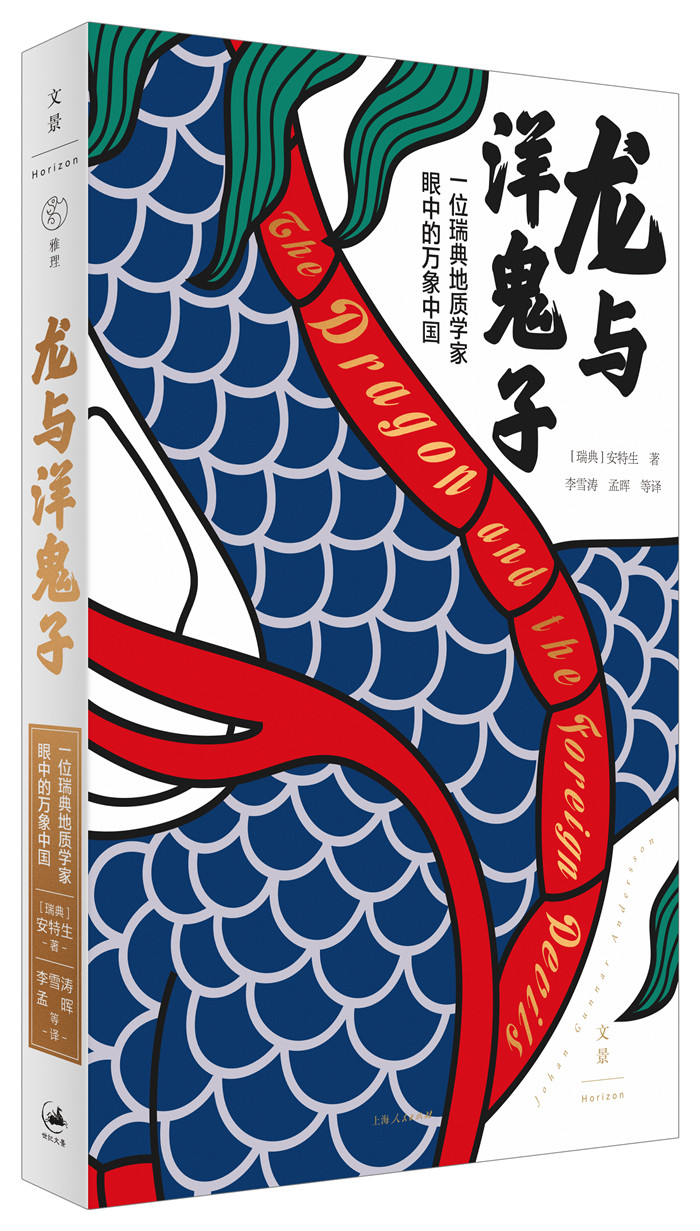
《龙与洋鬼子——一位瑞典地质学家眼中的万象中国》
[瑞典]安特生 著
李雪涛 孟 晖 等 译
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红山插曲
我去拜访朋友新常富的时候,他正熟练地指挥着大规模的挖掘工作。大约50名苦力在狭窄而危险的深沟中不停工作,垂直的槽壁上都尽可能地铺上了木板……一周后,新常富启程前往北平,我陪他走了一天,目睹了两幅对比鲜明的画面:一副是煤烟弥漫、人满为患的工业城镇彭城,位于小山口的一端,煤田里的黏土都用来制造各种陶器;另一幅是风景秀丽的村庄黑龙潭,在小山口的另一端,石灰岩山上大大小小的瀑布倾泻而下,树林葱郁茂密,寺庙风景如画,无比适合坐禅。在这儿,人们可以坐下来喝喝茶,抽袋水烟,没有辛苦的劳作,也没有痛苦和汗水,任时间消逝。
暮色迅速降临,我与新常富就此别过,在两个士兵和一个铁匠的陪同下连夜赶回25公里外的红山。离彭城越来越远,镇子里熔炉燃烧发出的光芒也逐渐隐没于我们的身后,两盏装有牛脂蜡烛的纸灯笼散发的灯光指引着我们在黑夜中前进。我们中途休息了几次,在小客栈里享用了热水,这是游客常喝的饮品。穿过活水乡堡垒般的房屋后,北边的红山便大致可见了。山顶附近有一道光在闪烁。那是我那体贴的仆从为我们上山而放置的指路灯。凌晨一点,我吃完晚饭后就睡下了,同所有疲惫的人一样一夜无梦、熟睡至醒,而后迎来了意外不断的新的一天。
……
午饭后,我在一名士兵的陪同下去山顶做测定。一个又一个时辰便在这一机械劳动中过去了。那名士兵很快发现自己显然有点多余,便躺在斜坡上打瞌睡。我自己也时不时停下来,目光掠过平原,望向隐匿于晴天薄雾中的山峰。
突然,士兵跳了起来,大叫着挥舞双臂。大山西侧深沟里的苦力们都跳了出来,独自一人或是三两成群地朝矿山东侧跑去,那边的空中一阵尘土正随风弥散。
一定是哪条探槽滑坡了。我冲下山坡,一群苦力也与我一道,沿着小路向出事的深沟跑去。
出事的地方是一处新挖出来的沟。原本它看起来像是粗糙的山体表面上一道锋利而精妙的手术切口,现在却裂成了坑坑洼洼的大洞,深沟里排好的木板和支架都被滑坡的石块砸得粉碎。苦力们互相挤来挤去。有些人站在洞边盯着看,有些人则下到洞里去,不停地把土块和石头往两边扒。有个苦力应该是被埋在碎石底下了。为了把他救出来,大家都拼命想办法。据我推测,他头上的土得有两三米深,旁边还有几块大石头,每块都得好几吨重。大家和我一样清楚,这样做也是徒劳,但试一试总比站在那儿什么都不做好。他们在救人这件事上的执着真让人惊叹!塌方口仅可容纳几人进洞,他们靠手里的锄头和铁锹,一刻不停地把沟底的石块锨出沟外。十分钟后,像是跑紧张的接力赛一样,第一棒结束了,几个摇摇晃晃地苦力走出洞口,栽倒在地,浑身是汗。新的替换人员立刻冲进去,在紧张地交接工具时,互相叫喊鼓劲儿。
……
我现在才知道,张署长在没有和我商量的情况下就给武安县长发了急报,要求派遣更多的士兵来保护我们。他以为苦力和村民肯定会把怒火发泄在我身上,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是灾祸的根源。我认为他的担忧毫无道理;在事故现场时,身旁的苦力都没有对我表现出任何不友好的态度。不过,在请求更多警力协助的同时,我还采取了自觉更合当前情况的措施。苦力们极有可能要工作到大半夜,他们需要一顿加餐,于是我派了一个信使到村里去,把他能弄到的食物都带来。过了一会儿,消息传来说,这么晚了这个小村庄里什么食物也找不到,除了到四英里外的活水村再去寻找外,别无他法。
与此同时,我们打着灯笼和火把继续寻找死者。随着沟渠越来越深,发生再次滑坡的危险性也越来越高,狭窄的空间每次也只能容纳几个人进入挖掘。最后,他们挖出了死者的脑袋和上半身。但接着又发生了滑坡,只好又从头开始。几个小时后,尸体再次从泥土中暴露出来,人们试图用绳子把它拉出来。看到尸体像一个被绳子猛拉的填充木偶一样来回摆动,感觉真是五味杂陈。然而,尸体的双腿依旧陷在泥堆里。
劳力被分成几班,一班工作时,其他几班休息。经过18个多小时的努力,到了上午11点,他们终于把尸体挖了出来,随后将其放置在寺庙旁的一间侧室中。
在中国习俗里,死者身旁守候的应该是他的母亲而非妻子。于是,死者的母亲立刻被召了过来,大约中午时分到了山上。我们从寺院里搬出一把扶手椅,让她坐在上面休息。坐在那里的母亲的绝望之情几乎凝成一幅画,一双视力模糊的眼睛无助地望向阳光。署长和死者的工友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她。她嘴里的牙齿都掉光了,一直喃喃自己多么悲痛。周围一片沉寂的忧伤,唯有坐在地上的苦力默默哭泣。
矿区的规章制度就是我们的行事准则。出现这种情况,在事故中丧生的劳工的家属有权得到一小笔赔偿金。此外,丧葬费须由雇主提供。所以严格来讲,我对此不负有个人责任。正式规定应是将报告递到北平的农商部,随后由农商部把一笔补偿金拨到武安县长那里,再由县长的下属送到遇难者家属手中。但是,我知道这笔补偿款的交付过程充满各种不确定性。与矿山监察员以及我的助手(他深受此事触动)讨论过后,我们一致认为这笔补偿款应由我们亲手交给遇难者家属,并最后商定给出20块大洋的安葬费以及60块大洋的赔偿金。60块大洋的赔偿金中,十块给家属用来准备过冬,剩下的50块用于购置田地,为今后的生计做打算。
这件事传遍了街坊邻里。很多人出于好奇从四方赶来,也有一些人,特别是女人,来吊唁死者,前额系着白绸带以示敬意。遇难者的遗体安放在棺材里,于灵堂内供人凭吊。

▲ 石碑(摘自《龙与洋鬼子》第135页,安特生摄)
下午,在六名士兵的护送下,武安县长亲自乘轿子前来吊丧。他穿着红色丝绸长袍,彰显着县长身份。我们自然无法做到礼数周全地迎接这位尊贵的长官。不过,我们还是表示欢迎他的到来,因为这就意味着我们对遇难者家属的补偿方案得到了官方的批准。他还派了一名警察找来遇难者的村长和两个村民,让他们在接下来的一天留在庙里陪伴遇难者的遗孀。
第二天,遇难赔偿所涉及的各方才来商讨处理意见并达成了一致,这位身份尊贵的县长便返回了城里。这次商讨赔偿没有给我造成任何麻烦,反而让我了解了一些当地的风土人情。
寡妇在村子里算得上是个样貌出众的女人。她有个身患坏血病的孩子,孩子长得其貌不扬。寡妇和村民们一上来就在我和矿山监察员面前跪下,他们下跪多半也是因为有县长在场,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人沾了他的光。
遇难赔偿的各相关方都受邀坐在厨房的大炕上,包括眼睛看不见的婆婆、寡妇和她生着病的孩子、死者的朋友、村长、两个见证人、矿山监察员、我的助手和我。当时我太过专注赔偿的细节,忽略了观察各方的行为举止,后来才意识到,当时的我们构成了怎样一副异同寻常的画面:大家聚集在烟雾缭绕、灯光昏暗的厨房里,用各种不同的语言讨论着如何处理这少得可怜的补偿款。
我给这一家人复述了矿山意外赔偿的法规,并解释说在县长的批准下,我们为他们争取到了更好的补偿方案,矿山监察员为我的这番话做了翻译。寡妇又一次下跪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各方也在赔偿款的使用细节上达成了一致。村民们尤为赞同用50块大洋购置田地。按照当时的物价,50块大洋可以买到三亩(相当于2000平方米)土地,足够养活死者的母亲、遗孀和幼子。
到目前为止,赔偿事宜进展顺利,没有异议,但一个关键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赔偿款应该交给谁?
我提议交给死者失明的母亲。她最无助,最需要保护。但那位寡妇立刻面露不安,村里的见证人也极力劝阻我。
之后,我提议把钱交给寡妇。村长立刻说:“不行!让她管这么一大笔钱可不行。一这么干,男人就都来抢着娶她,她肯定会丢下婆婆不管的。”
我又提议由村长代为保管这笔钱。屋内顿时陷入一阵尴尬不快的沉默。我的助手(钟先生)在角落里摇了摇头,也坚决反对。
交涉似乎走进了死胡同。于是我和其他同事、矿山监察员还有钟先生到一旁商量了一会儿,又回到厨房,提出了如下解决方案:(1)将应付给一家人的10块大洋生活费,当着所有人的面交给寡妇,并规定她必须照顾婆婆(婆婆听到这个安排后,显得有些坐立不安)。(2)丧葬费还剩余5块大洋,这个费用连同下面(3)的费用一起处置。(3)用于购置土地的50块大洋,再加上丧葬费剩余的5块,共55块大洋归属于祖孙三人。这些钱放入一个结实的蓝色双缝标本袋里,加盖监察员印章封存,袋子交给眼盲的婆婆,并做如下说明:袋子不可随意打开,所购置田地的价格必须恰好是55块大洋,且应于所有见证人都在场时将袋子里的钱转交给卖家。
这一安排得到了各方认可,洪山插曲到此结束。希望那个蓝色的袋子之后不会有什么问题!
作者:[瑞典]安特生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