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战争、自然灾害、意外事件……从日常生活到国际视野,“不确定性”成为描述当下世界最重要的关键词。当人们普遍感受到自己被巨大的无力感捕获,被弥漫的悲伤和焦虑吞噬,不禁不断发问:“这个世界还会好吗?我还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吗?”此时,美国历史学家特奥菲洛·鲁伊斯的《历史的恐怖:西方文明中生活的不确定性》显得格外应景,单单这个题目就尤为吸引人,毕竟历史通常被认为是启迪当下的一面明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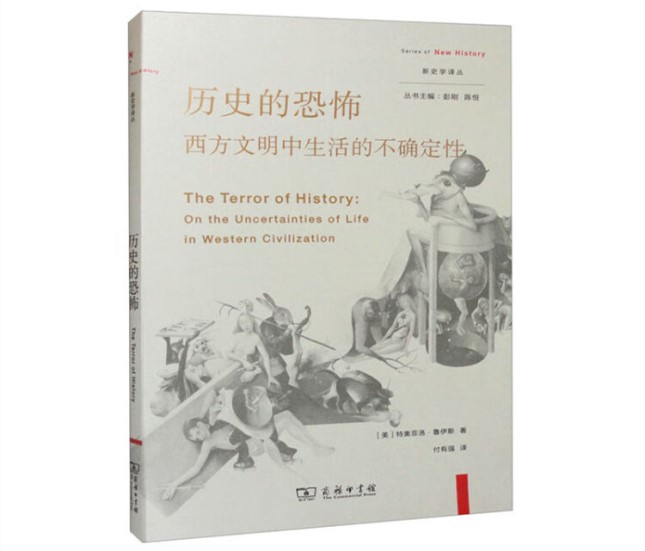
《历史的恐怖:西方文明中生活的不确定性》
【美】特奥菲洛·鲁伊斯 著
付有强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然而,倘若期待从这本书获得破解当下困境的秘笈,你多半会失望而归。因为这本融合了作者个人经历和学术专长的著作,以兼具感性认识和理性论证的方式得出了一个悲观主义色彩浓重的结论:“不确定性”正是人类生活“确定”的常态,每个人的周遭都充满了危险,伤害随时可以袭来,对此,无论个人还是集体的掌控力都有着明显的局限。换句话说,这本书的核心内容不在于揭示“如何能够化解、甚至避免”诸如战争、疾病、种族屠杀等种种令人不安的可怕事件,而在于描述灾难来临后,人们“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应对”深陷的危机。
《历史的恐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著作,更确切地说,鲁伊斯没有采用以考据和计量为主要研究方法的传统史学研究路径,转而以西方新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心理史学为基础,在跨学科的视野下对历史进行了不同维度的深描。从柏拉图到尼采再到维特根斯坦,从荷马到加缪再到托尔金,从诗歌到绘画再到电影,鲁伊斯所关注的历史不再是年份化和数量化的档案记录,而是被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人们不断书写、阐释和再现的开放式文本。
以1348年弥漫佛罗伦萨的黑死病为全书的开篇,以薄伽丘的《十日谈》为立论的出发点,鲁伊斯将历史上人类面对灾难做出的反应归纳为三种方式:一是转向宗教,以谋求对灾祸的解释和解脱之道;二是拥抱物质世界,以狂欢纵欲的方式忘却世界的烦忧;三是投身艺术,在创造性的美学生产和欣赏中获得精神的慰藉。尽管鲁伊斯一再强调自己无意对这三种应对方式进行高低优劣的评判,但对身为无神论者的他而言,“宗教答案听起来是空洞而没有意义的”,而身体的放纵和物质的占有带来的也只是转瞬即逝的快感和无边无界的欲望膨胀。显然,鲁伊斯更倾向于第三种方式。无论对美学家和学者本人,还是阅读欣赏他们作品的人来说,艺术想象和知识生产为身处“恐怖”之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解脱的可能,使其得以藐视(尽管无法逃避)苦难,从而对恐惧和痛苦进行自我消解。

鲁伊斯曾在访谈中坦言,对于人类对世界和命运的掌控力,他是一个(过于)悲观主义者。用他的话来说:“我们一直生活在深渊的边缘……可怕的事情可能即将发生。”如果说未来的不可预测性让生活充满了不确定,那么与此相对的,则是确定无疑的时间的流逝、生命的渺小短暂与必将终结,这是个体的人和集体的人类都无法改变的残酷事实。在鲁伊斯看来,“对抗历史和时间的斗争都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忍受”。因此,人们寻求的应是“忍受”的途径,提升的应是“忍受”的能力,当然,这也是人的天性使然,即人类与生俱来的“要活下去”的本能。
也正是在这个层面,鲁伊斯的探索是一种未竟的事业。因为真正称得上“忍受”的人不是远离深渊或在一旁凝视深渊的人,而是身处深渊的风暴眼却坚持不懈的人。在《历史的恐怖》序言中,鲁伊斯曾提到,在黑死病笼罩下的佛罗伦萨,亦有被薄伽丘和历史学者忽略的“第四种回应”,即留下来悉心照料病人,痛埋葬逝者,并继续着艰难而琐碎的日常生活。相比“逃”往宗教、物质和美学世界的人,这些直面恐怖却咬牙坚持、饱受痛苦甚至牺牲却执着于让世界正常运转的人们更加令人敬畏。但遗憾的是,鲁伊斯并没有展开叙述他们的故事。是什么成就了他们的不屈不挠?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归宿?这对几百年后依然被各种不确定性裹挟、被时常不期而至的恐怖侵扰的我们而言,无疑更具鼓舞和启迪意义。
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因为每一个现在正在成为过去,将来也很快不再是将来。正如鲁伊斯指出的,时间的流逝是人类必须经受的最大的历史的恐怖。反思历史或许无法让我们改变历史的进程,但起码可以让我们认清一些真相,进而或多或少地释怀:即使我们无法左右恐怖的降临,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藐视恐怖实现自我和解;即使我们无法阻挡时间的行进,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创造意义留存生命的印记;即使我们无法避免生活的不确定性,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追求美和善坚守对希望的执着。
作者:孙 璐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