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传统法秩序》为日本法制史学者寺田浩明多年来研究中国法制史的集大成之作。作者从中国传统社会实际出发,借鉴西方近代法理论,总结了19世纪末以来中国法制史、社会史研究中各种论点,着眼于其中的法秩序,如诉讼、听讼、断罪等环节,考察了传统中国法的诸多面向,特别是清代中国的家族法、土地法、裁判制度与刑罚制度,总结了传统中国的契约与诉讼社会的特点。
书中言必有据,理论深刻,将法史考察与法理分析巧妙融为一体,深入浅出地利用清代法律文献对各议题进行精辟的阐发,无疑是一本近年法制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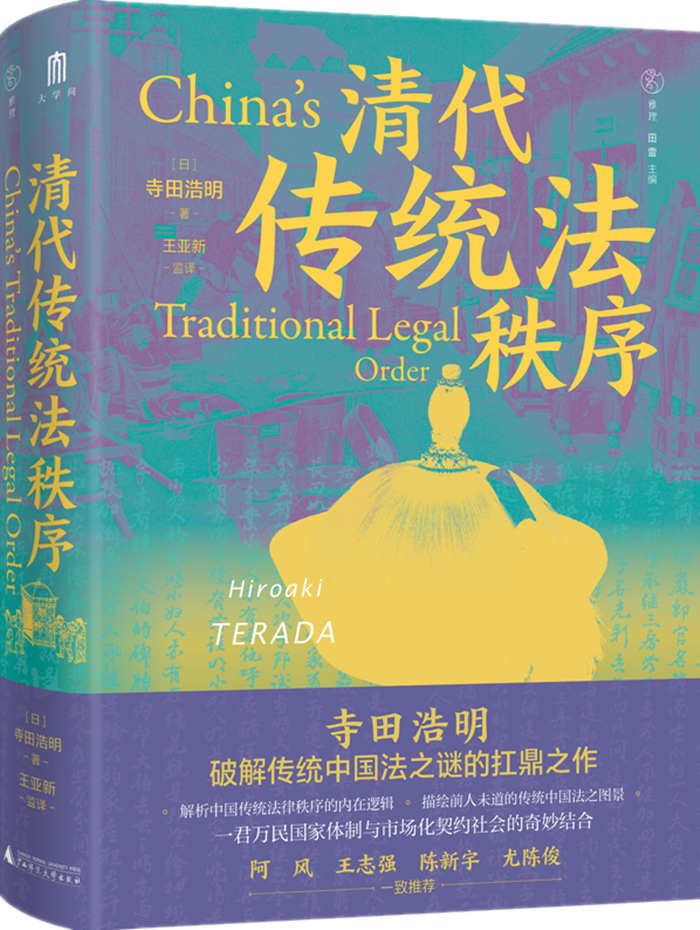
《清代传统法秩序》
[日]寺田浩明 著
王亚新 监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日本的“家”与中国的“家”有何不同?
与日本一样,在传统中国,人们也和近亲聚集在一起生活,此种生活单位中文也称之为家。不过,传统中国的家与近代以前日本的“家”,虽然因使用了相同的汉字而容易混淆,但它们在内涵上具有相当大的差异。如果带着错误的意象进入接下来的讨论,将会导致讨论的内容变得混乱,因此,这一点必须在开头处就予以厘清。
日本的“家”在传统日本里,如同“承‘家’”这句话所显示的,所谓“家”,指的是从祖先那里承接而来,在自己的世代中守护、振兴,然后交接给下个世代的对象物。在此意义下,它是超越各个构成成员而存在的客观组织体。这样的“家”,具有世世代代必须担负的、职务上或社会上的特定功能(“家业”——世代家传的职业、行业),而人们所意识到的“家”的兴盛,就是此种家传行业的繁荣壮大。
“家”的家长是此种业务组织体(一种公司)的经营责任者,所谓“承‘家’”,意味着家长——公司董事长——地位的交替或交接。此种地位通常由长男承袭,但是对于“家”而言,“家业”的存续是最高的价值,因此有时候能力的重要性会凌驾于血缘。长男没有能力时,由次男以下之人成为家长,甚至可能招入适任者为女婿,使之承“家”。此外,由于只有一人可以成为后继者,因此其他的孩子们会转以公司高级雇员的身份在“家”里面生活(日文称作“部屋住み”)。他们通常无法成为上述意义下的“家”的家长。当“家业”非常幸运地获得扩大时,他们自己可能建立新的“家”(日文称作“分家”)而成为这个“家”的家长。但即使在此种情况中,这个“家”为原本“家”的子公司或分店,分家的任务乃在于扶助本家。
当然,在古代,此种突出而享有盛名的“家”只存在于国家的上层阶级。这一上层阶级的顶点是天皇的“家”,其下则是以侍奉天皇作为“家业”(“家职”)的贵族们的“家”。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后来又增加了武士们的“家”,而且在武士的内部,还设立了大名及旗本以下阶层的“家”。到了江户时代,此种变化甚至扩及一般人民,连“本百姓”(受领主统制的一种农民阶层)的“家”也开始有了承继“田畑家督”(成为农地耕作责任者及纳租责任者的一种地位)的现象。在此,整个国家的体制,被理解为担负此种任务的许多“家”的积累(或者从顶点来看,是许多此种“家”的悬吊),而人们在某个“家”出生后,会守护这个由祖先传下来的“家”,各自钻研其技能(或专业),最终将这个“家”传给下个世代而死去。在此,社会的格局固定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之下,只要人们能够各自守护自己的“家业”,基本的秩序就能够获得维持。
中国的家不知不觉地,我们很容易做出这样的设想:由于日本是儒教国家,而儒教很重视家,因此中国的家也当然具有此种性质(或者日本的“家”具有的此种性质是学自中国)。但是,这样的设想完全错误。
诚然,在无法分割之物(典型的例子是政治支配者的地位)与家连结的情况下,不得已地,只能如同前述日本的情形般采取独子继承制,但在帝制中国里,政治支配者的地位(皇帝一家除外)原则上并非世袭。在此,职业不是由家所固定,而是由形成家且在其中生活的人们,为图自己的生存与富贵而选择。从人民生活的角度来看,甚至连官位、官职也只是如同此般的一种生计。这里,“家”这个汉字,显然指的是血缘相近的人们聚集后创设的、具有共产性质的生活共同体或生活团体自身,而当时机到来,这个生活团体会如同细胞分裂般,分割成几个较小的生活团体。因此,此处所谓家的兴盛,其浮现的意象并非如传统日本般的“家”此种企业体的壮大,而是继承自己血统的人们所形成的家这种生活共同体的增生,犹如蛙卵堆满池底般地满布于大地上。但是不待言地,并非所有的家都能够如愿以偿,实际上,社会乃是此种微小细胞彼此间的生存竞争,当然会发生激烈的变动状况,而社会秩序可以说是经由此种家与家之间反复动态性的重塑而形成的。
因此,虽然同样就“家”或家的问题进行讨论,但应该谈论的内容在中国和日本却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在日本的情形,“家”这种组织体、企业体的内部统制样貌及家长的更替样态等问题,会成为家族法理论的主要议题;与此相对,就中国的家而言,生活共同体的生活原理和该共同体的分裂形态会成为问题所在。
作者:[日]寺田浩明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