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建构。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商业繁荣,市民文化发达,与此相适应,江南的女子们逐渐超越了闺阁的限制,发展出一种新的妇女文化和社会空间。
《浮世精绘:苏州弹词长篇中的江南社会》《绣画——中国江南传统刺绣研究》和《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这三部著作主题接近,展示了明清时期江南女子介入社会生活的三种渠道,以及这三种渠道交织在一起所内含的、历史学家对于中国女性的创造性与主体性的重新认识。
弹词:酝酿着江南女性文化的各种要素
付楠的《浮世精绘:苏州弹词长篇中的江南社会》属于“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丛书揭示了书目与艺人、听众乃至环境间的互动与流动性。《浮世精绘》中有不少笔墨涉及到明清江南的女性文化。
作者解释:“弹词属于说唱曲艺,与评话是相互独立的曲种,在取材上偏向男女情爱、家庭纷争和市井生活的主题,大部分来源于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话本小说,故俗称‘小书’。”所以苏州弹词在情节上会有明显的程序化和雷同性。该书剖析了《玉蜻蜓》《珍珠塔》《十美图》等评弹长篇。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故事中的女性只是成就男性功业的陪衬。相比较而言,晚明大众俗文学追求人性解放,冯梦龙、汤显祖等在男女情感描写上都强调“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但清代的苏州长篇弹词更偏重礼教倾向,而且弹词文本几乎都经过了文人的修改整理再行出版,突出了“青天大老爷”的正派官员形象,以及以科举为导向的择偶观念。然而,其中对于“嫌贫爱富”的抨击,恰恰反映了这一时期士商联姻观念的潜变,说明当时士绅阶层的家庭相当一部分是以财物、权势为计而进行的“买卖”联姻。同理,小姐们“私订终身”的行径,也可视为女性自我意识的一种呈现。
清朝的文化政策相当严苛,从各级政府到大部分士绅阶层,对戏曲表演和市井文学的态度都较为抵触。清代政府屡次颁布民间戏曲演艺的禁令,苏州茶馆被明令不得召集女性入内饮茶,苏州弹词书目遭遇多次禁书运动,弹词艺人尤其女艺人生计难以维持,于是逐渐分散到苏州周边和江浙两省交界的各处市镇乡村码头,遂有“吴宫花草移植沪上”之说。苏州评弹成功抓住了在上海的新机遇,同光年间,居寓租界的苏州弹词因满足了男性对“苏扬之风”和沪上冶游的想象而得到名人和报刊追捧。这种情形说明了评弹表演市场的兴盛和商业社会环境的相关性,同时也酝酿着明清之际江南女性文化的各种要素。

《浮世精绘:苏州弹词长篇中的江南社会》
付 楠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绣画:江南女性“闺阁”空间的扩大化
如果说《浮世精绘》只是对江南女性文化有所提及,那么,许嘉的《绣画——中国江南传统刺绣研究》就是完全围绕这个话题而展开的。
作者解释:“绣画,通俗来讲,指刺绣观赏品中带有文人书画趣味的刺绣,高超者能以绣的技法达到一种如画、甚至胜画的境界。”从事刺绣的群体,或大家闺秀,或普通农妇,或青楼艺妓,于中国江南传统刺绣而言,江南水土的氤氲柔润赋予了她们特有的诗性品格,她们对刺绣的敏感与执著是天生的、自发的、命运般的。“刺绣之艺,吴中为盛。其传则自云间之上海。”绣画起源于上古江南吴地,成熟于宋,发展于近代松江,该书专论的晚明顾绣和清丁氏《绣谱》的发生地均在松江。
顾绣的诞生和兴盛并非偶然,与时代地域背景、审美理念及明中后期整个文化艺术界的繁荣和文人雅士的密切参与有关。晚明盛产“大玩家”,追求优雅精致的“时玩”,或是原有样式基础上的创新的艺术样式,松江府服饰的艳美风靡一时。明中后期的商业意识和启蒙思想改变了妇女的传统观念,女性逐渐敢于发挥自己的才学灵慧,大胆参与社会文化活动,闺秀女红开始作为商品生产交易。除了深层的社会经济原因,家族的文化积淀及个人的艺术修养等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顾绣女眷耳濡目染于家族的文人氛围,优越的家庭生活条件和艺术文学修养使她们有闲暇寄情刺绣,怡情悦性,并且把自己的刺绣技艺与文人书画相结合而成就“绣画”之道。如画之境、如天之工、如染之色,是公认的顾绣三大特点。
《绣谱》的作者丁佩,本人就是清朝中期擅绣画之闺秀。该书不仅是丁佩几十年刺绣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江南地区包括顾绣在内的绣种的梳理总结,更是在传统六艺基础上对刺绣艺术的创造性点评。丁佩将刺绣与“才人笔墨、名手丹青同臻”,纵观全书,以书画诗文及其他艺术门类喻刺绣之处比比皆是,最后一章更是将张彦远点评名画的方法直接转用于刺绣,“绣近于文”“通于画”,说明在丁佩心目中绣画实能登大雅之堂,丁佩已经有了以绣画为工具,面向精英男性争取女性话语权的主体自觉。
刺绣,自古以来被视作“女红小技”,是“妇功”中的一项技艺,绣技高超是心灵手巧的象征,还象征着贞洁坚忍、悠闲恬静。然而,明清时期绣画的盛行,实际上远远突破了传统刺绣的象征意义。绣画最重要的特点,是它与文人画的结合。这说明了江南地区闺秀良好的诗文书画的修养、女性知识水平普遍的提高,而这些绣画引起社会上文人雅士的赏评与市场化的商品转换,说明了“闺阁”空间的扩大化,知识女性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赋权空间,通过刺绣将自己的主观意识与文艺审美以及市场运作联系起来,把刺绣这种原本属于私人的或同性之间共享的社交活动,延展到了更广阔的社会空间,由此,士绅家庭女性的阶级基础和身份地位因近代性、商业化而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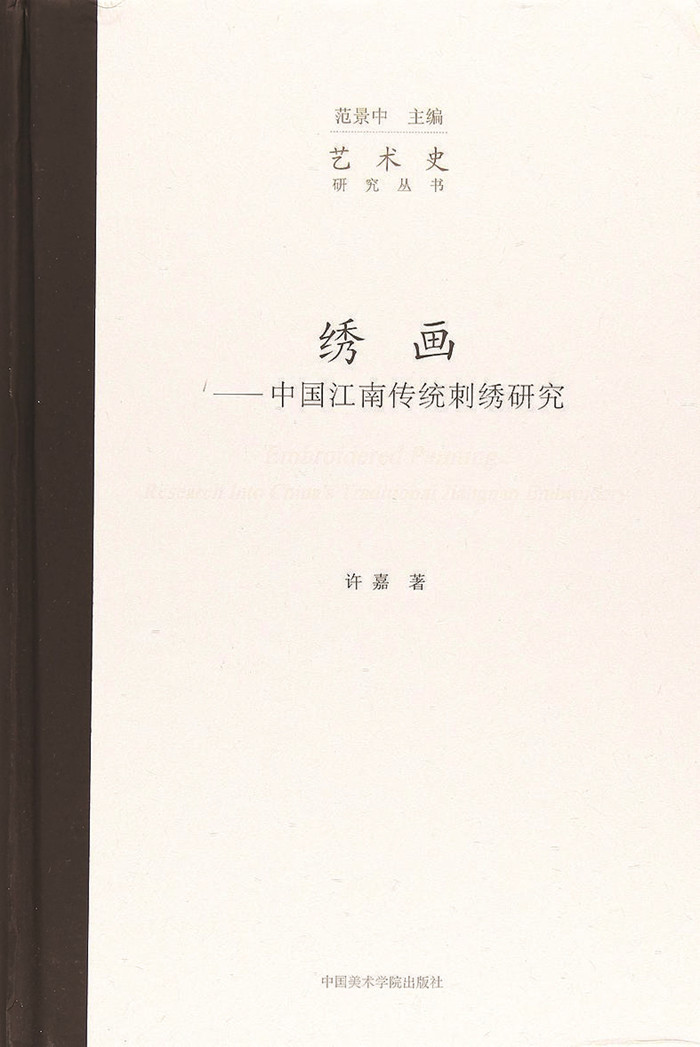
《绣画——中国江南传统刺绣研究》
许 嘉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
闺塾师:对明清江南女性知识传承的观察
如果说《绣画》所体现的江南女性意识仍然显得较为模糊,那么,《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一书对明清时期江南女性研究的挖掘力度就更加明确深刻了。
明末清初江南富裕地区和都城周围,职业女塾师群体的人数出现了明显增长。这些巡游的女性通常都是传统文人家庭的女儿,她们通过为上流人家的女孩传授儒家经典、诗歌艺术和绘画而谋生,被同时代人赋予“闺塾师”的名称,并作为儒家传统中受人尊敬的女学者的精神后裔而获得世人的尊重。
作者指出,闺塾师的生活暗示了一种浮现出的职业模式。女性的学问,特别是诗歌,是一个家庭的传统。许多女塾师生于有学问但破败的江南士绅家庭,并一直被母亲或祖母教育着。实际上,塾师为这些女性提供了一条维持生计之路。作为出版过作品的诗人或得到承认的画家,这些女性在因其声名而获得塾师的工作之前,就已经是职业艺术家了。与儒家视女性为安静和无名的这些限制相反,一个女性的文学名望对其家庭来说,可能是一笔经济财富。
《闺塾师》揭示了这些女性的公众职业生涯和获得的权力。一位女性独立于其父、其夫之外的谋生,威胁了旧有的“三从”基础。塾师的雇佣取决于作为有造诣的艺术家的声望,而“声望”这一概念违背了儒家所倡导的安静和隐居的理想女性形象。闺塾师身体的流动性,颠覆了女性生存空间封闭性的理想。士绅家庭女儿教育的重心所在,证明了当时的教育模式与正统的道德教养出现了竞争。
但是,我们决不能就此将闺塾师认作中国近代女性的先驱者。对女子的教育,有着商业化的考量,是为了增加未婚女子的待嫁砝码、已婚女子掌管家庭的能力,这与《浮世精绘》书中的叙述也是相呼应的。《玉蜻蜓》的张氏出身高门,全篇却只强调她三从四德、打理门户,《珍珠塔》的陈小姐诗书皆通,父亲对女儿的要求却是“略识几个字就罢了”。《闺塾师》书中出现的所有女性,不管是闺塾师还是闺阁里的少女、大家族里的母亲、妻子或寡妇,这些女性基本都遵循“三从四德”。江南士绅家庭重视女子教育,但是,女性知识水平提高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承担为人妻、为人母的职责。归根结底,最终强调的仍然是“重才更重德”。
《闺塾师》的写作目的,是为了涤清“五四”启蒙所建基的直线史观,这种史观将“传统”与“现代”、“落后”与“进步”一分为二,造成了对中国妇女史的偏颇误读。作者认为,不能把“三从四德”简单视为是对女性的压迫,这种长期形成的儒家文化尽管以父权制为前提,但它在实践过程里有很大的弹性。我对作者的论点并不全然赞同,因为文化建构的权力掌握在男性手里,女性的自由空间太有限了。在《浮世精绘》《绣画》里,我们都能发现女性文化背后男性的主导力量,而《闺塾师》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提供了对女性共同体内部文化教育的知识传承的观察。
“闺塾师”原指流动的女教师群体,《闺塾师》赋予它的涵义是扩大化的,除了所谈及的那些江南才女的事迹之外,书中还有很多笔墨谈论大环境。比如,广受欢迎的戏曲如《牡丹亭》、市面上风行的各种出版物的影响,等等。在《浮世精绘》和《绣画》里,我们同样能发现个人的、局部的知识与美学修养是被放置在大环境的影响范围之内的,尤其三部作品都强调了江南地区出版行业的繁荣兴盛和市民文化的广为传播。江南女性受教育、读书、出版和旅行机会的不断增加,是江南女性文化增长的必要条件,一个相当大的文化女性群体的存在,也给江南地区的城市文化留下了持久的印记。弹词、绣画、闺塾师,以及其他各种与女性相关的世俗工作渠道的出现,增加了女性自我满足和拥有富有生存状态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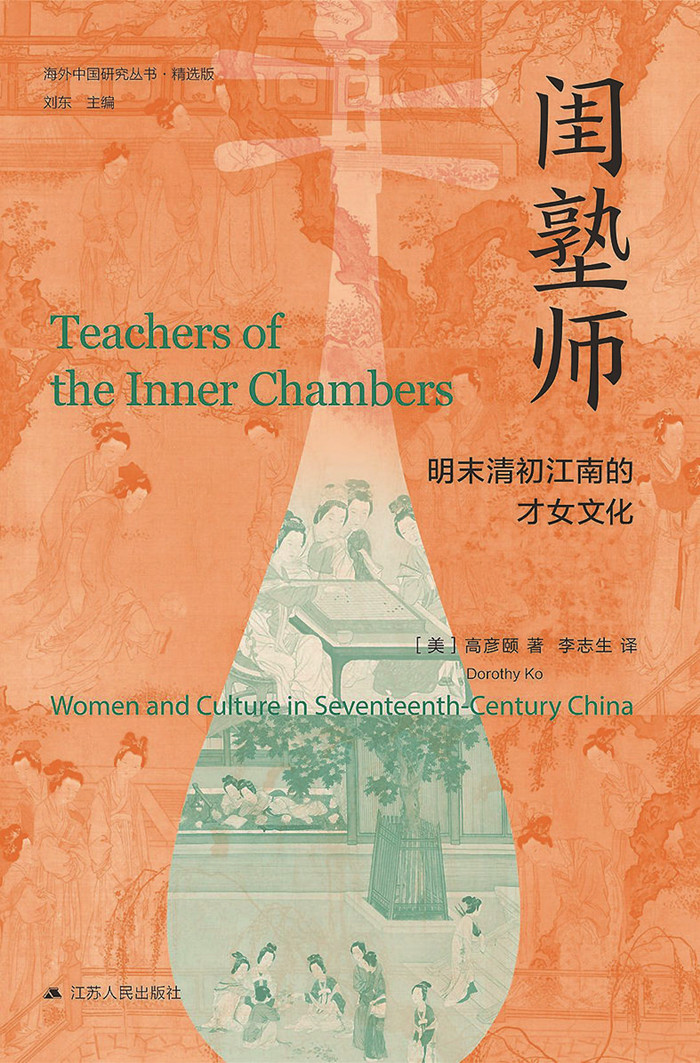
《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
[美]高彦颐 著
李志生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叶 晨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