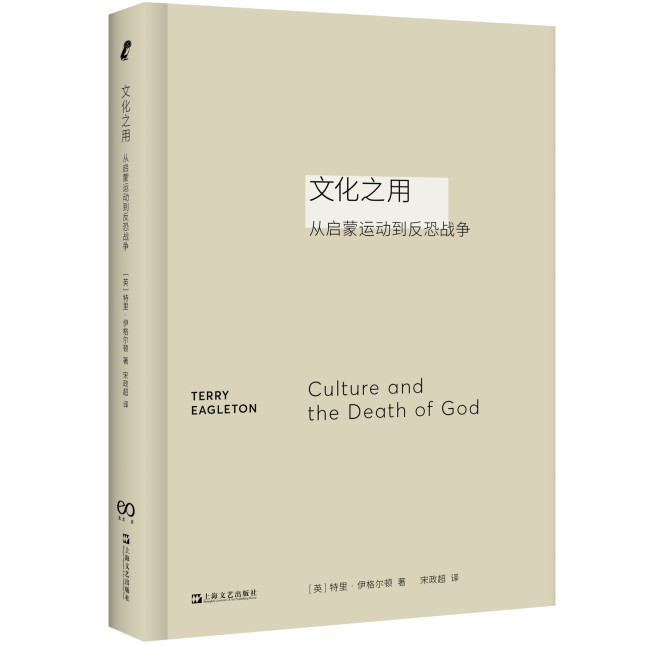
《文化之用:从启蒙运动到反恐战争》
[英]特里·伊格尔顿 著
宋政超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伊格尔顿在本书中探讨了现代社会自启蒙运动至今面对信仰的种种应对方式及其困难,深入浅出地梳理了理性主义、唯心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一系列理论流派的思想家们为提供超验的替代形式做出的努力。作者强调无神论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它总要承担时代具体的意识形态任务。在本书中伊格尔顿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当下精神生活源流的重要参考和风趣解说。
>>内文选读:
宗教懂得如何吸引大众,而德国哲学不懂。
民族主义是作为总体性的文化概念的主要来源——作为个人或者族群的完整生活模式。然而同时,它也促进了派系性的文化理念。这是种极为罕见的结合。对席勒而言,如我们所见,文化和派系偏见是世仇。对马修·阿诺德来说亦如是,他的观点在我们之后讨论的话题中会提到。民族主义,相比之下,表明了立场,但是以文化之名。民族生活方式可以构建一个共同体,但它也是残忍异见的起源。
诗人是不被承认的人类立法者,时下这个角色是被银行和跨国公司继承了。
浪漫主义对分析性思想的厌恶在这个运动的后期阶段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光明就在我心中,”雅可比辩称,“然而一旦我试图将其置于我的理智之下,它就消失无踪了。”曾努力拜读其作品的人将会非常明确地理解他的意思。
在某种意义上某些早期哲学家曾经梦想的大众神话最终以电影院、电视机、广告和大众出版的形式实现了。
阿诺德公开承认自己是个俗气的人或者中产阶级的成员;然而由于他也是那群唯利是图、心智粗俗的群体成员中那个持不同意见的,好像可以从外部对他所属的生活方式作出批判。对自身信念的玩味的疏离正是文化人的一个标志;但它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因为“雅各宾主义的两个突出标志——它的凶猛以及对抽象系统的沉迷,文化是这两者永恒的对手”。

现代主义将上帝之死体验为一种创伤,一个公开侮辱,既是痛苦的来源还是庆祝的理由,而后现代主义则完全没有这种体验。在其世界中心没有一个上帝形状的空洞,但在卡夫卡、贝克特或者甚至菲利普·拉金的中心都存在。
对现代主义来说,神的荣光让位给审美的灵光,而后现代主义的科技艺术又将后者驱逐。唯一苟延残喘的灵光就是商品或者名流,这些现象并非总是轻易被辨别出来。
鉴于其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倾向,资本主义,尤其是在其后工业化时代,是一种本质上无宗教信仰的社会秩序。对其运行而言,过多的信仰既无必要也不值得。信仰是潜在有争议的事务,既无益于贸易也无益于政治稳定。对商业而言它们也是多余的。创立制度时所需的这些热诚的意识形态修辞随着制度的展开而消退。只要其公民投入工作、承担赋税并且不去袭警,他们可以相信随便什么他们乐意相信的。
作者:特里·伊格尔顿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