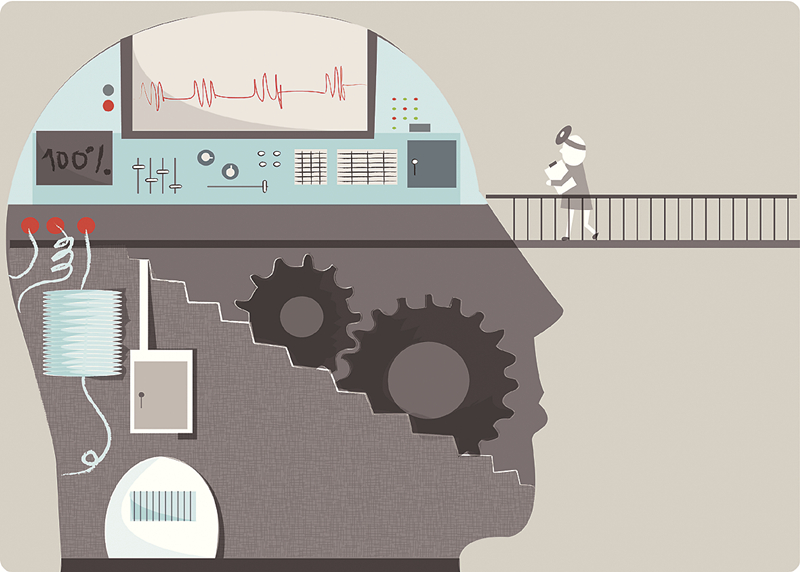
日前,教育部认定了612个项目为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在推进新工科建设上持续发力。与此同时,社会上关于“新工科”的大讨论也持续进行,大学在对于新工科的认识上,时有新发现,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
热闹之后掩卷深思,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一个核心问题:对新工科的顶层设计和具体的教改举措,到底是在原有人才培养方案上修修补补,还是“凤凰涅槃”? 是基于“老工科”打造升级的2.0版,还是诞生于新时代、脱胎于新要求的“新”工科人才培养生态?“换汤”和“换药”是有本质区别的。
新工科是学科交叉的产物,突破高校在学科交叉上的制度瓶颈和行政壁垒,是新工科必须跨越的一道坎。
新的科学技术的诞生,无一例外地来自于人类惯性理解框架下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例如量子通信,就是量子物理和信息技术结合的产物;生物信息学,就是生命科学和计算机学科的混血儿。此外,诸如机器人、自动驾驶、智能建造等新技术的出现,都不同程度地来源于不同的传统领域之间、传统领域和新兴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伴随新工科的出现,很多人会发现,对一些具体的学科,难有精细定义。其实,像“电子工程”这样的专业,究竟涵盖哪些内容,是很难描述清晰的。于是,技术进步和历史进程就这样不断地交叉,然后不断地得到新生,交叉的本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说,学科交叉,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工科建设最普遍的共识。

但是,由于既有的大学治理体系和人才培养框架的束缚,学科交叉融合言易行难,目前,大多数高校在人才引进、研究生招生、职称晋升等几乎所有的环节,都难以在交叉上破题。比如,教师写一篇文章,只要和学科目录里的一级二级或者制定期刊目录范围里对不上号,无论文章本身内容如何,也基本上就是废文一篇。在职称晋升的路上艰难求索的年轻人不仅仅要写论文,还要不断地为写了以后“算不算数”而绞尽脑汁。研究生招生也一样,诸多博士生导师不仅仅是不被鼓励、而且是不允许跨学科带研究生。
当然,还有行政上的壁垒。一般情况下,大学都是依据学科来划分二级学院,例如“机械学院”“材料学院”等等,每一个二级学院都在按照自己的规矩运行,想互相走动合作一下很难,因为考核的规矩不一样,功劳簿记账的方式不一样,生拉硬扯的“合作”之所以不能持久,其根本原因是合作者“各为其主”。
目前,在跨学科交叉合作方面做得比较前卫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其大致的做法是:组建一系列跨学科委员会以及建立大学部制度,有效整合学术资源,跨学科委员会统筹审批和承担重大合作研究项目,积极扶持和培育新的学科交叉的“宠儿”,有的逐渐演变为学科核心,甚至独立建系。还有一个堪称典范的当属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学生们来自方方面面,各种奇才异智云集,有几十个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小组在一起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一流的科学研究成果是不足为奇的。
可以说,本土高校推进新工科建设,需要破的题很多。虽然有的高校也在不断尝试“实验班”“创新基地”之类的模式,但往往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学院归属、文凭究竟谁来发、学生究竟谁来管、课程编号如何编目等老套的路子上。所以,在新工科建设的征程中,我们再也不能掩耳盗铃般地忽视障碍的存在。唯有共识和智慧,才能破茧而出、蚕蛹化蝶。
把学生关在象牙塔里封闭训练,如何去要求培养的人才能够一脚踏入社会,而不会茫然不知所措?
对于学生来说,学习新工科,意味着他们要有满足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必要技能,获取知识和可持续学习的能力,具备与社会进行无缝结合的能力,以及能够不断进行自我革新和自我塑造的能力等。只有将这些内容春风化雨般地融入到新工科的教改中,构筑自适应的新工科建设模式,才会有长久不衰的生命力和源源不断的活力。
由此来看高等教育现状,很大程度上,工科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更新周期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尤其是传统的工科教学实践,课程内容相对滞后,几十年甚至数百年不变的数理化基础课程有死板之嫌疑,而专业课程在知识和技术细节上普遍滞后,学校的双师型人才严重匮乏,有过实战经验、经受过实际工程洗礼的工科教师寥寥无几。
由于技术更新和迭代的速度日新月异,技术的精细化和集成化趋势,使得学校在课本上表达新技术的手段相当缺乏、反应迟缓,加上学生们在工程事件中学习的机会也不多,从课堂到课堂,已经不能适应技术的快速发展。
因此,推进新工科建设,首要之举是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我们不能盲目地热衷于赶时髦,而是要有秩序、有规划地布局专业,并制定对应的人才培养计划。

一个国家工业体系和工程建设体系的建立,必须以强大的工科教育与培养基础为依托,具体包括数理基础、人文基础、工科基础、专业课程、社会实践等等。大到大飞机制造,小到芯片生产,究竟需要如何相对应的人才培养体系? 我们目前的培养模式能够迎合需求吗?
就笔者所知,国内高校汽车专业的学生,大学四年期间没有打开过汽车引擎盖、没有参观过汽车制造流水线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学电子工程的大学生,在毕业之际能说清楚一块芯片的制造过程,或者说参观过一个芯片制造厂的大概也不占多数。
我们的校园里,还有不少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比如,一些科技创新大赛的初衷,是让学生们创新思维、淋漓尽致地发挥专业所学。但是,这些大赛却在操作过程中,被涂上了一些功利化的色彩,和保研、评优等挂钩,于是科技创新的成色大打折扣。还有一些学校出台的政策,大力倡导本科生和博士研究生一样发表各种不同“I”论文 (I,是英文Index的简写,检索的意思),结果一些工科专业的学生临近毕业,除了文档和一些计算机演算仿真技能,几乎没有动手和实践能力,距离社会期待有不小的距离。
试问,我们把学生关在象牙塔里封闭训练,如何去要求培养的人才能够一脚踏入社会,而不会茫然不知所措? 没有一个从认知、技能、知识、道德甚至到理想、情怀的多层次的培养体系,以及来自校园、社会、互联网的全方位人才培养生态系统,如何谈“新”,又“新”在哪里? 所以,新工科是全员的新工科,是全方位的新工科,是全新生态的新工科。要让学生们在新工科的生态系统里尽情地“玩耍”,尽情地施展才华、得到锻炼,而不是填鸭式的课堂和近似无聊的说教。
能够把不同的技术、不同的零部件、不同的人员组织起来,最终建成可使用的产品,就是工程师的能力。
什么是工科? 似乎难觅严格意义的规范和标准定义。按照公众的一般理解,它是一门专门研究利用人类积累的知识和技能来解决实际的生活或生产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的学问。总而言之,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工科人才培养的核心价值体现。
所谓的新工科,就是除了在课堂上培养学生必须的知识和技能,还要通过不同的渠道和不同的方式,训练、熏陶、提升除了书本知识和工艺技能之外的综合素质,这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工程师素养”。
例如,大飞机C919的生产,能够把不同的技术、不同的零部件、不同的人员组织起来,最终建成可使用的产品,就是工程师的能力。另外,工程问题的解决,一定是诞生在特定的历史和经济条件下的,需要“约束的思维”。工程师除了琢磨技术,很多时候也要算经济账,也要充分考虑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的可行性,要把“创新”和“异想天开”区分开来。到人工智能技术出现后,甚至还要顾及人伦道德和法律层面的约束等等。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程师摇篮,他们的一个重要办学理念就是注重学生的沟通能力,认为这是工程师的一个重要特质。从招生开始,学校就观察学生的沟通能力,包括高中阶段的社会和社团活动经历。

法国、德国的一些培养工程师的大学,对学生的挑选和培养几乎苛刻,属于精英教育的典范。他们给外界的直观感觉就是平时的任何学术与非学术活动都注重团队精神的养成。例如,课后作业很多是由小组集体完成的,教学队伍中一半以上的企业兼职教师,还有有效的校外实习安排。
在欧洲,我们还会发现,很多的准工程师们均身怀绝技,吹拉弹唱,总有一样“武艺”,学校交响乐团、合唱团之类的活动丰富多彩。其实,在陶冶情操,增加艺术素养之余,这些活动本身有助于加强学生的沟通协调能力,一举多得。
记得钱学森的老师、20世纪最伟大的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曾经说过,“科学”的意义是发现和探索既有的世界,而“工程”是用来创造新世界的。其实,新工科就可以被认为是一项工程,是一项超脱于自我和狭隘的革新和改造的过程,需要的是参与者高度的“自觉性”。
诚然,让一位教书先生摒弃自己近乎一生相伴的一门专业课程或者一本教科书,与时俱进地去更新知识,甚至还要面临失业的风险是非常困难的,新工科教改的推进中,必然会出现阻力。以传统机械工程为例,且不讨论3D打印是否会取代车钳刨铣,传统的工科教学模式和内容不是不可变革的,但难的是变了以后,实验室和老师怎么处置? 相应的行政和考核体系如何变化? 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说,对于新工科的“认知”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面对的问题,新事物的养成非一蹴而就。新工科的建设需要水滴石穿,唯有脚踏实地、壮士断腕甚至刮骨疗伤,才能持续前行。
在新工科建设的征程上,所有的参与者都是探索者、实践者。煲一锅老汤尚需时辰,何况育人呢?
作者:张轮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授)
编辑:郝梦夷
责任编辑:姜澎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