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社会人文学科的多种领域,尤为历史学、文学的研究者所重视。它在历史学科上“补正史之缺”的价值有目共睹,学界早有共识,出版物中,即有以“史料笔记丛刊”命名的;但其文学性质的讨论似尚不充分,文学史中往往一笔带过,颇有“妾身未分明”之感。我想,笔记的身份认定是多元的,它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互不相妨。
上海师范大学编纂的《全宋笔记》,是近年来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又一重大成果,其包含的学术意义和文献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日渐突现出来,引起学界恒久的重视与珍重。
2006年,我参加四川大学召开的《全宋文》(360册)首发式时,曾经说过,作为一名宋代文学的研究者,对《全宋文》的问世有些特殊的感受。宋代文学研究的主体文学文本,不外是诗、词、文三者。宋代虽然话本小说、戏曲也很发达,但能确认为宋代的文本,至今留存极少。有了《全宋词》《全宋诗》和现在这部《全宋文》这三大“全”,几乎包括了宋代文学的主要文本资料。这三大“全”的鼎足而立,将对宋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时间过去了12年,如今我们可以说,有了《全宋笔记》这第四“全”的加盟,从“三足鼎立”到“四维并举”,把宋代文学的直接文本资料,殆已囊括无遗,在宋代文学研究史上树立了难以磨灭的丰碑,促成了文献资料的完整性、互释性和体系化。
笔记在传统目录书中,被列在史部或子部,自有其学理根据。但从今天学科分类架构的角度来看,能否对其身份认同重新作些考虑。此时此刻,我想到两位前辈学者和一部新著。

▲钱锺书在《近代散文钞》的书评中,对笔记“小品文”有过风趣而机智的解说。他认为这种文体“由来远矣”,开始形成于魏晋之世,是“一种最自在、最萧闲的文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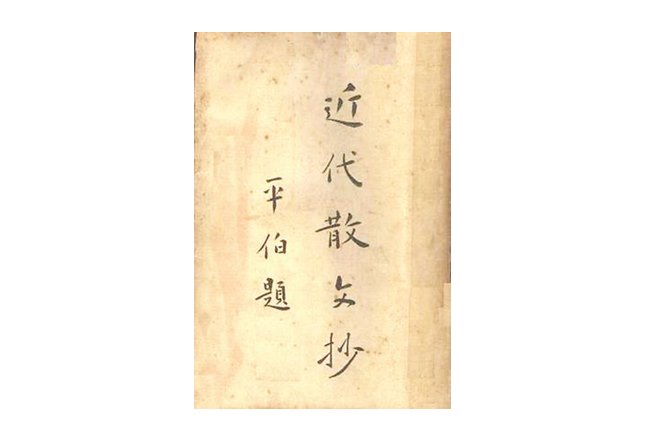
一位是钱锺书先生。他一生激赏于“修词机趣”,倾心于“文字游戏三昧”,擅长“在非文学书中找到有文章意味的妙句”,对“文学”的界域具有灵动、宽泛的视野。在《近代散文钞》的书评中,他对笔记“小品文”有过风趣而机智的解说。他说“小品文”这个称谓可与“一品文”或“极品文”相对举,后者“本‘一品当朝’‘官居极品’之意,取其有‘纱帽气’”;而“小品文”当然也有载道说理之作,然其主要特征在于有“格调”,可以名之为“家常体”,“因为它不衫不履得妙,跟‘极品’文的蟒袍玉带踱着方步的,迥乎不同”。他并认为这种文体“由来远矣”,开始形成于魏晋之世,是“一种最自在、最萧闲的文体,即我所谓‘家常体’”,举的实例就是《世说新语》等包括笔记在内的作品。也就是说,笔记是“家常体”之一。他还说过一句重要的话,认为这种“自由自在的家常体,介乎骈散雅俗之间的一种文体,绝非唐以来不拘声韵的‘古文’”,则将“家常体”和“古文”视作中国古代散体文章中的两大系统,极大地提升笔记小品文的文学地位,具有引人注目的学术启示意义。钱先生的这些观点是符合古代笔记作者的写作初衷的。秦观有部笔记叫《逆旅集》,今已遗佚(否则这套《全宋笔记》可以再增加一种),但他留下一篇序文,交代其书好丑兼存,随机而述,不求永久,与“君子之书”有异,也非“缙绅先生之事”,最后总结他作笔记的原则是:“仰不知雅言之可爱,俯不知俗论之可卑”(《淮海集》卷三九),与钱先生所说的“介乎雅俗之间”“不衫不履”“自在萧闲”,旨趣是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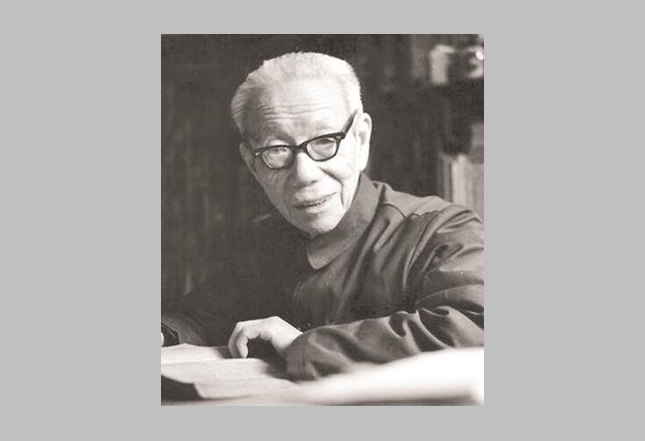
▲吕叔湘在其《笔记文选读》的自序中提出,笔记文“或写人情,或述物理,或记一时之谐谑,或叙一地之风土,多半是和实际人生直接打交道的文字”。

另一位是吕叔湘先生。这位语言学前辈有部不起眼的小书,就是《笔记文选读》。此书是在叶圣陶先生主编的《国文杂志》1943年陆续刊登,选了九种笔记,宋人占了七种。吕先生作此书的初衷是为中学生提供文言文阅读的参考书,因而语文学的知识介绍自是它的重要内容;但处处贯串着文学评赏和分析,不妨说,“文学视野中的笔记”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叶先生在《谈语文教本——〈笔记文选读〉序》中说:“文言之中专选笔记,笔记之中又专选写人情,述物理,记一时的谐谑,叙一地之风土,那些跟实际人生直接打交道的文字,为的是内容富于兴味,风格又比较朴直而自然,希望读者能完全消化,真实得到营养。”后来由文光书店正式结集出版时,吕叔湘先生增写了一篇自序,几乎一字不改地暗引了叶先生的这个概括:“或写人情,或述物理,或记一时之谐谑,或叙一地之风土,多半是和实际人生直接打交道的文字”,只是把叶氏所说的“那些跟”改成“多半是”,稍稍做了些限制;但紧接着加了一句:“似乎也有几分统一性。随笔之文也似乎本来以此类为正体。”叶先生的这个概括,源自李肇《国史补》的自序:“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但六项中删去了“辨疑惑”“示劝戒”两项,把“纪事实”改为“写人情”,突出人、物、时、地四端,特色是“富于兴味”,文风是“朴直而自然”,更贴紧了文学的内涵和功能。吕先生对此不仅完全认同,还进一步指明此乃这类笔记文的“统一性”所在,而且提到“正体”的高度。对于笔记的这种全局性、整体性的评价,尚不多见,是尤应重视的。
在吕先生这本十万字的小册子中,文学视野是一以贯之的。其作家总评和与众不同的专设“讨论”一栏中,要言不烦而精彩纷呈,往往在个别问题的点评中,蕴含重大的文学命题和课题。与钱先生论“家常体”起始于《世说新语》相呼应,吕先生此选亦以《世说新语》开篇,推崇此书记人“盖善于即事见人,所谓传神阿堵者”,“今世言文学,尚性格之描绘,是则此书固宜膺上选也”,径直置于文学范围中予以论述,而“即事见人”“传神阿堵”数语,准确地道出笔记记人手法的文学特点。他论及苏轼,“坡公策论,旧为学文者所宗;时移风变,转觉信手拈来者为有意境有性情,胜彼辩士常谈多多许也”,注重于笔记的随手而成、脱口而出却具“意境”“性情”的特性,击中要害。又说东坡《志林》:“实开晚明小品一派”,“或直抒所怀,或因事见理,处处有一东坡,其为人,其哲学,皆豁然呈现;与本编前后诸家随笔皆不侔,当另换一副眼光读之。”评赏中着意于对象的个性,突现“这一个”。他对作家的总评又能与其具体作品的评析结合起来,如评《记承天寺夜游》:“此篇寥寥数十字,而闲适之情毕见,其意境可与陶渊明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相比,但渊明未曾一语道破,更见含蓄,此则诗与文不同也。”又对东坡自称“闲人”,作了大段警策的阐说,不啻是中规中矩的文学评论。他在全书评论中,又多前后照应、彼此互阐之妙。如论及陆游《老学庵笔记》,说“放翁才情豪放,倾注于诗……出其馀渖,为笔记文,亦清简可喜”;其笔记文的特点,“记人不求传神”,有别于《世说新语》;“记事不穷考据”,则异于《梦溪笔谈》,然而“信笔数语,自饶逸趣,盖初非刻意为书,亦犹是诗人气分也”。此从诗文一脉相承处着眼,而他评苏轼《记承天寺夜游》与陶诗相较,则从诗文不同处落笔,各臻其妙,表达了吕先生独到的文学见解。
限于本书的性质,吕先生的评论大都点到为止,不暇展开,但已指明路径,对于笔记文如何进入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作了示范性的导引,留待后辈循此精进,深入堂奥,以求更具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学史》的诞生。
想到的一部新著是周勋初先生主编的《宋人轶事汇编》。这部“汇编”的主要资料来源就是宋人笔记。在一次有关“笔记”的学术会议上,有位先生说过,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记叙,“正史以骨骼,笔记以血肉”,我深以为然。从人物传记而言,正史中的纪传、各类墓志铭等碑版文字和记人为主的笔记文,三者的文学蕴含、审美愉悦和情感投入程度,表现出逐次递增的趋势。隔代修史,《宋史》为元人所修,是一种具有强烈政治性的政府行为,它的纪传是表达朝廷意志的盖棺论定,立言审慎,叙次合规,大都选取生平履历、立朝大节、重要宦迹等,人物面相单一,史臣以“客观”“可信”为鹄的。笔记写人的手法是“即事见人”,重在轶事,通过种种日常而又含趣味的“轶事”来展示人物的心灵;重在“细节”,用素描式的三言两语来“传神阿堵”。试读《宋史》中的苏轼本传、苏辙所作乃兄的墓志铭及《宋人轶事汇编》中378条苏轼“轶事”,完全是三种不同的苏轼形象。直到今天人们心目中的东坡,大都得益于宋人笔记所形塑。我们曾经说过,“如果要欣赏宋人风度,体味宋人情怀,感受宋人的雅致生活与书卷气息,《宋人轶事汇编》恐怕比《宋史》更为合适”。把此书当作文学书来读,似不为过。《拗相公》就是联缀诸多宋人笔记材料而成的一篇话本小说,毫无悬念地进入文学之林。
前面所说的“四大全”,其文学性质是并不完全等同的。由于诗词在形式体制上的明确规定,《全宋诗》《全宋词》作为文学文本的直接文献,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即使是坏诗烂词,仍是文学研究所面对的对象。《全宋文》中的18万篇作品就不能全部阑入文学史的论述对象,大多数诏诰等官方文字很少有文学因子。笔记情况也与之相类。笔记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社会人文学科的多种领域,尤为历史学、文学的研究者所重视。它在历史学科上“补正史之缺”的价值有目共睹,学界早有共识,出版物中,即有以“史料笔记丛刊”命名的;但其文学性质的讨论似尚不充分,文学史中往往一笔带过,颇有“妾身未分明”之感。我想,笔记的身份认定是多元的,它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互不相妨。《史记》是历史书,但鲁迅评为“无韵之《离骚》”,毛泽东说“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似可兼称。从某种意义上说,《全宋笔记》也可被视作泛文学文本或亚文学文本的文献集成,以纠正文章(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中长期边缘化的缺憾。
《全宋笔记》必将是一部“长命书”,成为宋代文史研究者案头必备之书。一部大型文献整理典籍的出版,往往能促成一项专门学科或专题研究的建立与发展,切实解决学术难点,推动学科走向层次更深、水平更高的方向。对于《全宋笔记》的问世,我们也满怀期待。
作者:王水照(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辑:范菁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