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受访,回忆成长与求学经历。研究生时期,葛晓音师从陈贻焮先生,亦与林庚先生交往颇多。“他的治学有人觉得好像是那种诗人式的、感悟式的成分多,没有太多实证性的东西。但实际上这跟他的理念有关系,这就是他平时跟我说的,不要面面俱到,不要光堆砌材料,要把最重要的观点突显出来。”葛晓音说,“我的感觉是他已经把所有的资料当作酿酒的材料一样,都已经酿熟了,所以挤出来就是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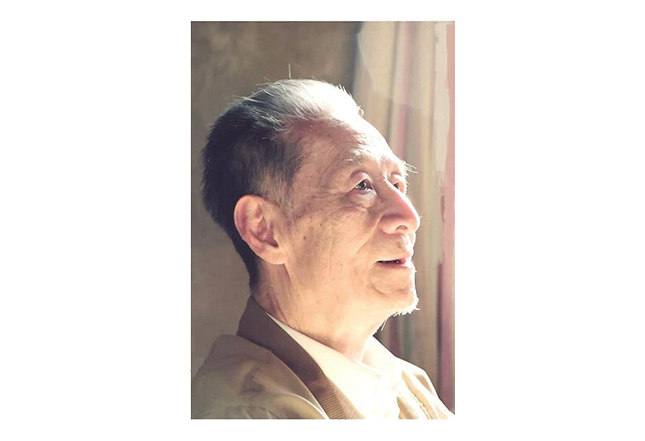
▲“他的眼界非常高远:时空、生命、青春、永恒,都是非常富于哲理性的思考。”晚年的林庚资料图片
1992年,在您的协助下,林庚先生开始《中国文学简史》下卷的编写工作。您是怎样协助林庚先生工作的?与一般的文学书相比,这部书的特色何在?
葛晓音:林庚先生原来的《中国文学简史》只有上册,出版社建议他写个下册,两本合在一起。所以下册主要是宋元明清这部分。林先生开始写这部书时已经84岁了,当时他手也抖,查资料什么都挺不方便的。他提出要我当助手,我很高兴,趁此机会可以向林先生好好学习。以前主要是跟着陈贻焮先生去见林先生,单独跟他见面的机会不多。由于林先生年事已高,写作主要采用他口述观点、由我记录整理的方式。每次我到他家去,就带一个笔记本,我们对谈,他谈我记录,基本就是这样子。林先生谈的时候不看书,那些资料全记在脑子里,有的可能不是很精确,但是大致不差。我的感觉是他已经把所有的资料当作酿酒的材料一样,都已经酿熟了,所以挤出来就是酒。一般来说他只是说重要的观点,但有的时候也会说到一些细节的地方,我就不管他说什么,统统记下来,回来以后将它整理出来,当然还需要补充很多资料,我就去图书馆查书,有的时候我查的资料也能够帮助发挥他的观点。
比如说关于《水浒传》的问题,他原有基本观点,我查了很多资料,经过两人讨论,写成文章,发在1993年《国学研究》第1卷上,题为《从水浒戏看〈水浒传〉》。他坚持要署我的名,我说不,因为大观点是他的,我只是帮他补充了一些资料而已。他还挺重视这篇文章的,最后在文章末尾署“林庚口述、定稿,葛晓音执笔整理”。这篇论文通过九本水浒戏以及《大宋宣和遗事》与《水浒传》的比较,考证出《水浒传》的成书“至早也要迟到永乐末年”,“下限应是在正德、嘉靖之际”,其作者“当然不可能会是罗贯中”,“至于施耐庵有无其人,本来就很成问题,传说他更早于罗贯中,自然也就更不在话下了”。又认为《水浒传》中的“英雄形象乃是市民心目中的江湖好汉融入了传统的‘游侠’理想的产物”,这种人物性格的精神内涵决定了水浒聚义的反势要、立边功的中心主题。文章还根据明代前期重视边功的大量资料解释了120回《水浒传》后半部主题转为招安平辽的原因,也澄清了历来评《水浒》都以为梁山泊“图王霸业”是要另立王朝的误解。
林先生的文学史修养非常全面,除了诗以外,小说研究也有一些精彩的文章,像《红楼梦》《三国演义》的分析都写得非常好,都被我吸收到下册中。写一部文学史毕竟要求比较全面,他讲得也有详有略,像《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只讲一个大的观点,我补充的比较多一点。但大部分我是就他原来的观点发挥,比如《西游记》他原来就有一本《西游记漫话》。这本书一反以往认为小说反映封建社会现实政治和农民斗争的流行说法,分析了《西游记》的童话精神,指出这种童话精神产生于《西游记》已有的神话框架,并且与明代中后期李贽的“童心说”所反映的寻求内心解放的社会思潮相一致。这些观点和《水浒传》研究一样,可称是石破天惊之论。另外林先生在1940年代就出过一部完整的厦大版《中国文学史》,这次写下册,也吸收了其中一部分内容。
我写好下册初稿后,林先生做了细致的修改加工,最后由他定稿。与一般集体编著的文学史相比,这是一部真正属于个人的文学史,观点是非常鲜明的,从头贯穿到底。一般的文学史讲诗的时候讲诗,讲词的时候讲词,各个时代之间也没有太多的逻辑关联,林先生的文学史不是,他认为唐五代以前是寒士文学,宋元明清以后就是市民文学。但前后又是相呼应的,像后期论《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的意义,从作者对寒士阶层的反思这个角度去看,就能认识得更透彻。
比如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为什么把女性写得那么好,对男性那么痛恨,就是因为作为封建社会上升力量的寒士阶层到后期已经腐败堕落没有出息了。《儒林外史》实际是对这个阶层崩溃的总结性描写,从这个角度去讲,真能讲出新意来,能够对《儒林外史》中好多情节作出透辟的解析。书里的人物都是布衣、山人、侠客、不慕名利的公子,这些人在早期寒士文学中都是被歌颂的对象,代表着社会前进的力量。本来走的都是和科举完全对立的人生道路,但是到了《儒林外史》中这些人全变成骗子、恶棍,这就说明连八股以外的这条人生道路也变质了,整个寒士阶层已经不可救药了。
下卷系统而明确地表述了林先生对中国文学史后半部分的基本特征的认识。他认为,宋元以来,新兴的市民文学日益兴旺起来,并越来越居于创作上的主导地位。寒士文学与市民文学之间的盛衰交替,便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鲜明的一个重大变化。这一基本论点与他对先秦至唐代文学的认识相辅相成,和《中国文学简史》上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在1995年把上、下卷合并,定名为《中国文学简史》,成为一部全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林先生是主张读聪明书的那种人,他脑子里记得很多。比如先秦文学,他虽然只做《楚辞》,其实别的经典也读得非常熟,随口就能说出典故出于哪本书,甚至哪一卷。但他不喜欢堆砌资料,主张无论是写一本书,还是写一篇文章,不求面面俱到,而是要重点突出,观点鲜明。林先生对这一点要求非常之高,他看我写的草稿,凡是罗列比较多的地方,他马上就说你不用把材料都堆上去,要突出最重要的论点,观点要始终贯穿在论述当中。这也使我深受教益。
您和林庚先生接触很多,还编选过《林庚文选》,想必对林庚先生很了解,请谈谈您认识的林庚先生和他的治学方法?
葛晓音:我大学本科时是文学史课代表,和林庚先生接触就比较多,读研后跟着陈先生也经常去见林先生,再加上协助他写作文学史这么一段经历,所以,直到林先生去世,我们的交往都是比较密切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着彻骨的清气的人,他是真正的清高,从里到外都散发着诗意,他的精神世界是完全远离世俗的。当然,他也是生活在人间,1950年代以后还挺坎坷的,但我觉得林先生始终以一种超脱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和身边的一切事物。要知道学界多年以来是不平静的,难免会有各种烦扰。可是一到他家,踏进门见到他,你顿时会觉得远离了这些烦恼,心里特别宁静,特别干净,这是我每次见到林先生的一个特别突出的感觉。所以林先生也说,有什么烦恼,就到我家来,我这里是一片净土,我觉得林先生的家真的是一片净土。跟他接触,自己能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净化。
他考虑的问题都非常宏大,所以我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从他的新诗里可以看到,他的眼界非常高远:时空、生命、青春、永恒,都是非常富于哲理性的思考,有时他会把片段的心得写在纸片上给我看,前些年他还把平时零碎的思考结成一个集子《空间的驰想》,这是我最爱读的一本书。一个人经常思考这些问题,那些琐碎的、庸俗的东西自然而然就不会去关注,精神境界也可以得到一种升华。
他其实也遭到过批判,受到过不公的待遇,但是他对那些肤浅无稽的批评,几乎是不屑一顾的。这种人生态度对我影响很大,让我渐渐地也把学术以外的东西看得比较淡,那些人事上的是非竞争,我都尽量不参与,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就行了。这是我从林先生那儿得到的最大的收益。
林先生的治学方法,我觉得一方面是多看书,一方面是不停地思考。我和他对谈时他都不怎么翻书的,偶尔翻一翻,他基本上就是坐在那儿慢慢地想。我去之前他就先想好了和我谈什么问题,然后慢慢地把他的想法说出来。他平时不断思考的特点,也可以从他书桌上的日历本看出来,翻过去的日历背面是空白的,他经常把他想到的东西记在这些小纸片上。有时是成段的,有时就是一些片言只语。他去世之后,我们找到他的一些笔记本,上面记了不少这种片段的想法,其中有的变成了文章,有的是零零碎碎的,不一定能成文章。从这些积累可以看出一个观点在他脑子里要酝酿多久。
书出版了,文章发表了之后,他还在不停地改。我常看到他在著作上不停地改。他的文字极其讲究。这儿用一个什么字,这个字怎么用,有他许许多多的考虑,所以,他永远在不停的修改当中。他的治学有人觉得好像是那种诗人式的、感悟式的成分多,没有太多实证性的东西。但实际上这跟他的理念有关系,这就是他平时跟我说的,不要面面俱到,不要光堆砌材料,要把最重要的观点突显出来。但这并不等于他没有材料,他只不过是让材料站在这些论点的背后,不喜欢把所有的资料都铺排出来而已。正因如此,他有很多观点都是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
(作者为公众号“尔雅国学报”编辑) ■
作者:杨阿敏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文汇报理评部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