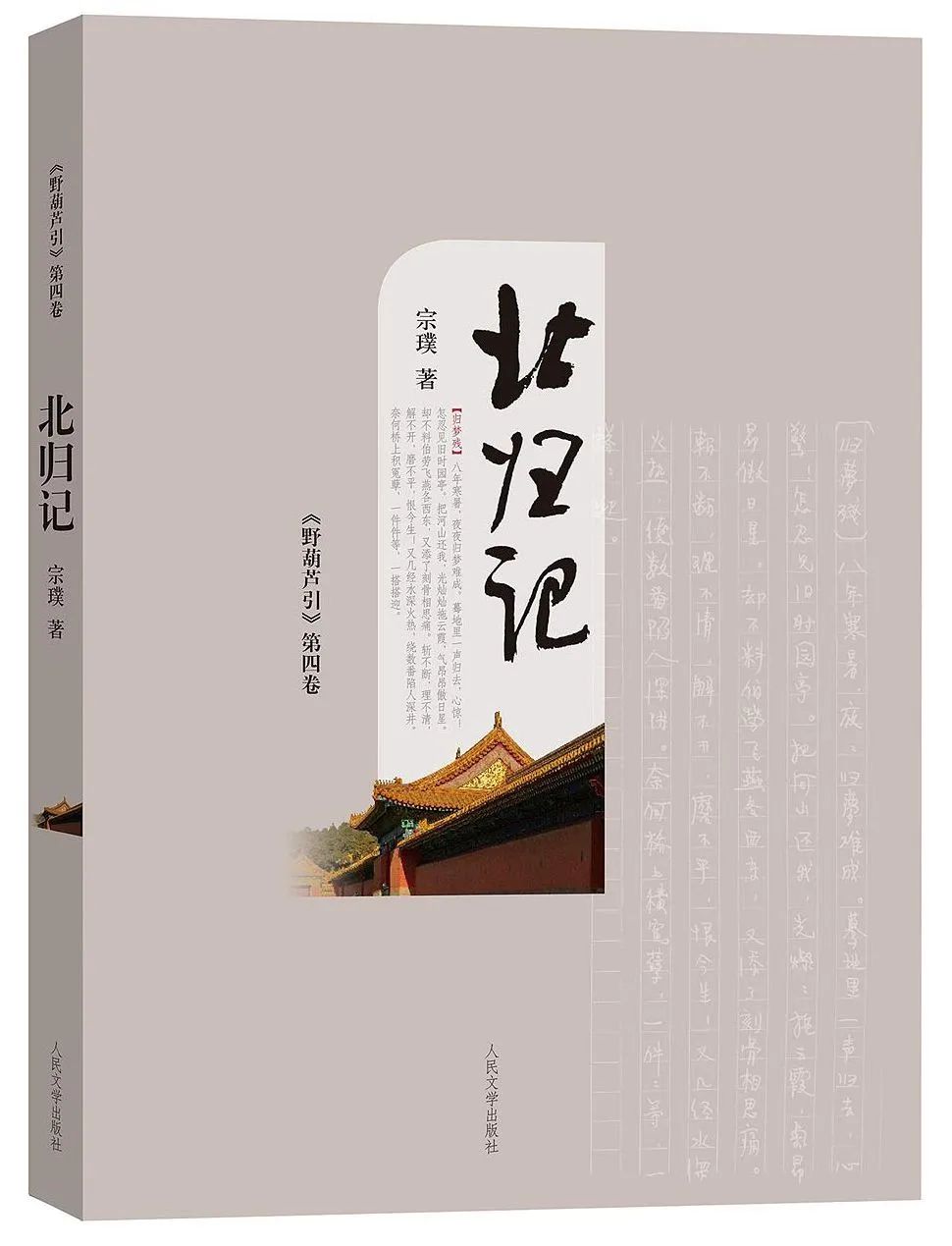
作家宗璞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第二卷《东藏记》,写到相当多“明仑大学”的知识分子。外界一般认为这些人是以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为蓝本塑造的,网上流传着“影射说”,报上也辟专版将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一一对照,引发读者讨论。对此宗璞未置可否,只说应该把眼光放在文本阅读和审美情趣上,影射之说不可考,但这种讨论也很有趣,能增加读者对文本的兴趣。
有一次我拜访宗璞,她忽然问我,你觉得钱明经的原型是谁?我试着问,是不是陈梦家?她点点头,不再多说什么。其实我对考古学家陈梦家知之甚少,作此回答是在《宗璞文集》末尾所附的年谱上,1938年宗璞十岁时,有这样一段话:“6月,与姊、兄、弟随母由北平至蒙自。住桂林街王维玉宅内,与陈梦家、赵萝蕤夫妇为邻。”不过小说里钱明经家与主人公孟家都住在昆明的龙尾村,家隔一条街,同饮一井水。小说里的钱明经是个风流才子,毫不迂腐,对买进卖出很有兴趣,懂文物,玩玉器,后两点同陈梦家确实很合。但小说里浓墨重彩写了他的风流韵事,以至太太要离婚,他“起身拿过一叠文稿,虽是土纸,装订整齐,又是几本杂志,刊登着他的甲骨文研究文章,说:‘那些女人只看我长得好,她们不懂,难道你也不懂!’”
这真是那时代知识分子活生生的写照了。
又有一次我拜访宗璞时,她问我读完2001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风庐小说选》没有。风庐是宗璞书房的名字。接着她提出,后记里自己抛给读者一个问题:《长相思》里的“我”,为什么叫谢娥法?我口拙,一时答不出。
《长相思》也是一个可以找到原型的故事。它写的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万古春归梦不归,女主人公秦宓苦恋着西南联大的数学才子魏清书长达四十年,但才子早已在北京结婚生子,而且找的还是外国女子。“我”谢娥法受秦宓亲友所托,去美国拜访秦宓,告诉她实情。因为魏清书是娥法父亲的高足。秦宓却不相信这个和自己一句话都没有说过的男子居然早已有了家庭。这也是那代人身上才会发生的痴事。
见我一时答不出,宗璞笑着提示说,不是说娥法的父亲是数学教授么!我这才恍然大悟。娥法娥法,代数符号阿尔法也。宗璞给笔下的“我”起了这么个绕来绕去的怪名字,预示着她要解答一个绕来绕去的人生难题!
2018年底宗璞出版了长篇小说的最后一卷《北归记》,又涉及了她热爱的《红楼梦》中的“真宝玉”与“假宝玉”的问题。
宗璞创作长篇小说,一个重要的参考源泉是《红楼梦》。为什么这样说?笔者2013年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青琐窗下——论宗璞六十余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评论:“关于宗璞的小说研究,目前尚有很多空白留待深入探讨。宗璞八岁就读《石头记》(《红楼梦》的别称,因整部书刻在一块石头上),在昆明时,和兄弟上学路上也谈红楼。对回目,你说上面我说下面。《红楼梦》中常有‘贾母因说……’‘宝钗因说……’这样的句式,而在宗璞的《野葫芦引》里,这种句式也屡见不鲜。这就鲜明地表现出《红楼梦》对宗璞在句式运用上的深入影响。而《红楼梦》对其文学创作更多方面深入骨髓的浸润,又一一表现在哪里?”
读了《北归记》,可以得出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藏在《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中。那一回,警幻仙姑命舞女将新制红楼梦十二支演上来,说“若非个中人,不知其中之妙”。针对这一段,脂砚斋评道:“(个中人)三字要紧。不知谁是个中人,宝玉即个中人乎?然则石头亦个中人乎?作者亦系个中人乎?观者亦个中人乎?”
为什么说《北归记》里也有“个中人”?首先,《红楼梦》具有高度的自传性,而且参考了许多前辈的生活体验,《野葫芦引》四卷也如是。现在评论界一般认定,《野葫芦引》中,明仑大学的原型就是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小说中的孟家,带有鲜明的冯友兰家庭的影子。主人公孟弗之,谐音“孟夫子”,就是宗璞父亲、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化身。书中的各位叔叔教授辈,都有西南联大各教员的身影。但《红楼梦》里一些具有高度历史真实性的事件以雪芹之龄是不可能遭逢的,需听取长辈的叙述。这点也与宗璞的创作经历高度相类。宗璞在七七事变爆发时只有九岁,写作《南渡记》乃至第二部《东藏记》时,大量细节描写均来自父兄辈的回忆。
但是问题来了。当大家都把孟家看成冯家时,宗璞在《北归记》里偏偏写了这样重要的一段话:“晏不来拿来热水瓶,往大家的茶杯里一个一个地续好水,又回到座位上说:‘我素来喜欢读冯友兰的书,他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思考,是从共相和殊相的哲学道理来的。在《别共殊》这篇文章里说,西方文化之所以先进,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它是现代的。近百年来我们之所以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的。我们不能照搬一个个体,可是可以从一类当中吸收适合自己的东西。多精辟啊!’”
在这里,宗璞的父亲,以及他的著作,直接现身于女儿的自传体小说之中了。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文学现象。
这里就又借鉴了《红楼梦》的文学创作方法——《红楼梦》里,金陵有个贾府,江南就有个甄府。贾家有个贾宝玉,甄家就有个甄宝玉。两座府第、两个人物处于平行状态,发生的大小事情却历历相同。我认为此即宗璞在《野葫芦引》终卷里让自己的父亲终于从“孟夫子”的身后绕出来,从幕后来到台前,说出一番最精彩深沉的道理的借鉴所在。“孟夫子”是假宝玉,冯友兰才是真宝玉。
因为宗璞热爱父亲,她一定要把父亲哲学思想的精髓摆出来,在最后一卷大放光彩。
所以, 无论《红楼梦》也罢,《北归记》也罢,我辈读者都应体会著者在具体情境下的良苦用心,只有视“个中人”为那个年代普天下一切家世、交游、经历相似者的共同心曲,方能攫取《红楼梦》的神髓,也才能读懂一生挚爱《红楼梦》、学习《红楼梦》的宗璞这饱含心血的一笔!
作者:侯宇燕
编辑:钱雨彤
责任编辑:舒 明
来源:文汇笔会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