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的圣殿:诺贝尔文学奖解读》
[瑞典]万之著
上海世纪文睿公司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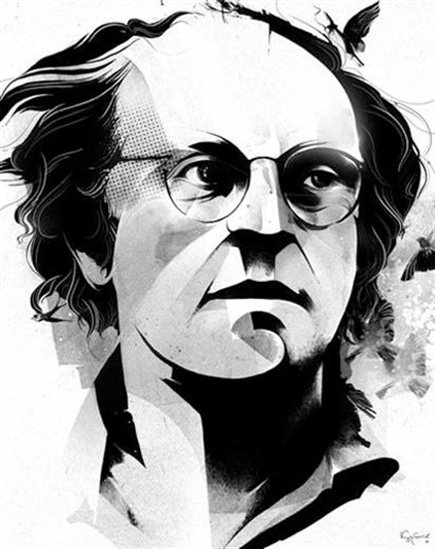
布罗茨基画像
诺贝尔文学奖1901年起开始颁发,传承百年,跨越世纪,迄今为止仍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诺贝尔文学奖授奖标准到底是什么?历届获奖作家加冕文学桂冠的原因何在?本书作者万之旅居“诺奖故乡”瑞典多年,以见证者和评论家的双重身份,拆解奖项授予背后的谜团。书中收录的每一篇文章都重译并解读了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并以之为线索深入探析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理由。
瑞典学院授予布罗茨基诺奖的颁奖词:“因为一种以思想敏锐和诗意强烈为特色的包罗万象的写作。”
不为国王起立的诗人
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个冬日的早晨,走出家门感觉特别寒冷,眼前的整个世界都埋葬在冰雪之中,天空也变得阴沉肃穆。那天早晨,我在瑞典国家电台的广播里听到了噩耗:昨天,1996年1月28日夜间,布罗茨基因心脏病突发,在纽约与世长辞。
布罗茨基生于1940年5月24日,享年只有五十六岁。五十六岁,这本来是一个诗人、一个作家的生命之树最茂盛、最能开花结果的时候,布罗茨基却像是在雷击中轰然倒下,这让我感到了意外,感到吃惊,感到内心的空落。
我想起布罗茨基一首悼亡诗中的一句:“尽管我们的生命可以分享/世上有谁能分担我们的死亡”。死亡不能分担,但死亡可以给依然活着的人,哪怕是个和他毫不相干的人,带来莫名的恐惧和痛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分享着死亡之果。
闭目回想,我依然可以看见一双眼睛,透着智慧,而又真诚;透着善良,而又深沉……
1991年,诺贝尔基金会庆祝诺贝尔奖颁奖九十周年,几乎把全世界能邀请的诺贝尔奖得主都邀请来了。瑞典学院也邀请了所有在世的诺贝尔奖得主到斯德哥尔摩来参加纪念活动。记得除了有些作家如索尔·贝娄因为高龄或身体不好而没有来之外,其他在世的得奖作家都来出席了,其中就有1987年的得主布罗茨基,他在当时来参加诺贝尔奖九十庆典的得主中最年轻,只有五十一岁。因为当时还邀请了几位虽然没有获奖但却是国际知名的作家和诗人,包括中国诗人北岛,而北岛当时英语还不很流利,我应邀担任了翻译工作,因此也参加一些纪念活动,有幸见到所有来出席的得奖作家。这些作家各具风采,都有让人敬重的文人气质,但是让我印象最深、最感崇敬的是布罗茨基。在这些本来就已经光彩夺目的文学明星们中间,他不仅最年轻,又是最有风度、最有个人魅力的一个。别的作家,不论多么优秀,好像我真的都可以淡忘,但是我不会也不敢忘记布罗茨基,尽管我和这位诗人的接触,也就那么一次,唯一的一次。
回想起来,为什么我和布罗茨基只有一面之缘,却终生难忘,原因很多。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中学也学习过俄语,大学又主修外国文学,对俄罗斯文学情感深厚,当然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托娃等等俄国诗人的诗歌。但是我过去从来没有听到过俄语诗人的朗诵,而且是一个真正大师级的俄语诗人的朗诵。就在这次诺贝尔奖颁奖九十周年的活动中,我有幸听到了布罗茨基的发言和诗歌朗诵。他站在讲台上,那么仪表堂堂,那么自信十足。他的动作不疾不徐,说话不快不慢,尤其是最后他朗诵自己的几首诗的时候,他的声音就如徐缓而来的音乐,就如无需伴奏的清唱。我第一次感觉到俄语的诗意表达在音律上原来可以这么优美,抑扬顿挫;我才明白真正的诗歌其实就应该有这样的声音韵律,这不仅是诗也是歌,是语言的艺术也是音乐的艺术。布罗茨基的朗诵让我身心感动,更知道诗歌是要分等级的,有的诗歌可以这么高贵。
另一个原因,就是我这里要写到的一件小事情。也许不值得大书特书,但是这件小事情对我个人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它让我知道,不仅布罗茨基的诗歌是高贵的,他作为诗人也是高贵的。而且这是庸常之人不可企及的高贵。
那次诺贝尔奖颁奖九十周年纪念活动很多,其中有一场难得的音乐会。演出即将开始之前,观众都已屏息安静下来,乐队也都静坐等待。我突然听到一片椅子翻动的声音,众人纷纷起立,这才发现右边设有王室专座的包厢,是国王、王后、公主、王子也来出席了,所以听众纷纷起立致敬。出于礼貌,我自然也赶紧站起来,以免失礼。漫不经心中我东张西望,突然发现坐在我前一排的布罗茨基却纹丝不动,他的夫人也依然故我。
在站立成一片的黑压压的人头中间,这两个空缺的位置在我看来是太醒目了,太招眼了,也让我太吃惊了。布罗茨基和他的夫人没有站起来!这就是我至今难以忘却的一个场面!
后来,我没有在瑞典媒体上看到哪位记者注意到并写到过这个场面,当时也许没有记者看到,而其他在场的人就是注意到,也没有人把它当回事来谈论。我想我大概是唯一注重这个细节的人,而且不断地反复回想这个场面。事隔多年,我已经忘记了那天的音乐会演出的是什么曲目,但是我却一直没有忘记这个场面。
我曾经和一个也在场的诗人谈过这个场面,为什么所有人都起立了,我们都起立了,这是向一个我们正处在的国家的首脑表示尊敬,按理说这是礼仪也完全应该,而布罗茨基和他的夫人却没有站起来。诗人说他根本没有注意,而且,这其实不礼貌。我无言以对。不礼貌也许是一种解释。布罗茨基确实也给某些人矜持傲慢、难以接近的印象,给人一种桂冠诗人身份高贵的印象。白天在瑞典学院有过一整天的研讨会活动,而他也不会和你随便搭话寒暄。他的眼睛看着你,你就知道你应该止步。我后来也听说,布罗茨基某晚应邀参加诗人聚会活动,却一晚上没有和别的诗人说话,因为他根本看不上这些诗人的诗歌。
我总觉得,诗人布罗茨基不为国王起立一定有他的道理,而用不礼貌解释很勉强。我更倾向于把他的举动理解为一种对于世俗权贵的藐视。他确实表现出一种傲慢的姿态,或者说一种令我不得不尊敬的高贵。
我相信我的理解是对的。数年之后,我读到了布罗茨基在《诗人和散文》中的一段话。他写道:“平等的观念和艺术的天性是不相符合的……”他特别谈到诗歌的高贵,谈到诗人其实就应该是不一般的人。布罗茨基确实是有等级观念的,是把人分为等级的人,但那是精神的等级,而不是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的世俗等级,在那里,诗人是最高贵的,国王不值一提。他们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他们是不食嗟来之食的人,他们是天子呼来不上船的人,他们自然也应该是不因为国王的到来而起立的人。那么,我相信,其他人都可以为国王起立,而像布罗茨基这样的诗人确实不应该起立,否则就不是高贵的诗人布罗茨基了!
人有时候确实需要高傲一点,尤其是面对权贵的时候,而这样的高傲,反而会赢得人们的尊敬,甚至是敬畏,因为这是更高贵的人格的展现。
纯粹的个人主义诗人
后来,我找到布罗茨基到斯德哥尔摩领奖时的诺贝尔演讲词讲稿仔细读过。讲稿的命题可以翻译为《美学乃伦理之母》。我在这篇讲稿的字里行间不断地看到闪光的思想,让我共鸣的理念。讲稿开篇,他就把自己形容为一个这样的人:“一个相当保持私人性的人,一个终生偏爱私人状态而不愿担当任何社会重要角色的人,一个在这种偏爱方面走得相当远——至少远到了离开祖国的人……”确确实实,仅仅开头的这几句话,就已经能引起我的共鸣。我也同样相信,文学写作的真正意义就是私人性质的,正如布罗茨基继续说的:“如果艺术能教育我们什么(首先是教育艺术家),那就是人类状态的私人性。”其实,也就像我尊敬的另一位现代作家卡夫卡一样,一个人写下的东西,实际上是可以不用出版秘不示人的,只属于你自己。正如布罗茨基所说:“很多事物可以分享,比如一张床、一片面包、某些罪名、一个情妇,但决非一首诗。”
拒绝担任社会的重要角色的意思,其实也是当代文学中强调个人性的许多诗人和作家的非常多见、非常清楚的态度,例如米兰·昆德拉,或者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帕慕克等等。诗人不必都是战士,更不必成为烈士,不需要总是去面对刽子手面对刑场。转身走开,这是另一种方式的反抗姿态。但是,布罗茨基也明确地说,写诗,本身就是一种不服从,它本身就是拒绝被支配和奴役。
布罗茨基在演讲稿中说道:“审美选择是高度个人性的事务,而审美经验总是私人经验。每一新的美学真实使一个人的经验更为私人化;而这种私人性时常以文学的(或其他)品位的面目出现,自身能够成为一种抵抗奴役的形式,即使不能作为保证。”在这里,私人的写作本身其实就是拒绝奴役,拒绝干扰,个人的自由因此而实现。
当然,布罗茨基也谈到文学家的尴尬感,写作的私人性质和表达的公共性质之间的矛盾,艺术的升华和生存需要的矛盾。他也没想到,像他这样一个强调私人性的诗人,最终会获得如此丰厚的回报,登上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讲坛。这种尴尬感,也是任何一个真诚地从事文学创作而不希望用文学艺术的文字去换取生活费用的人的尴尬感,是我个人也深有体会的尴尬感。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尴尬,我们也就无法读到卡夫卡的作品,也无法欣赏到布罗茨基的诗歌。
当代很多伟大作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种黑色的幽默,从卡夫卡、加缪和贝克特等作家那里,我们都感受到这种幽默。布罗茨基也给我这样的印象,严肃的思想常常用嘲讽的方式表达。因为敏锐的思想能洞察世界洞察人心,而又看到人本身的尴尬可笑,所以采取一种幽默的嘲讽的态度,有时也是具有勇气的自嘲。布罗茨基的一句名言,被瑞典学院在诺贝尔颁奖典礼的介绍中引用,让全场观众会心大笑:“我认为,记忆就是人类在幸福的进化过程中永远丢掉的尾巴的替代物。它指导我们的方向……”
我常常对朋友说,如果我能成为一个易卜生主义者,那是我的荣幸。易卜生主义者,用我们的“五四”前辈胡适先生的定义来说,就是“健全的个人主义者”。布罗茨基的思想特点,就在于他也是一个相当纯粹的个人主义者,他刻意追求的也是属于个人的生命价值,这就是他的诺贝尔奖演讲稿标题“美学为伦理之母”的题旨。
确实,布罗茨基一生一直坚持用俄语创作诗歌,后来也用英语写作其他作品,被称为坐在一座山顶上可以看到东方西方两面风景的诗人,但这只是艺术语言的认同,而非国家民族的自我标记,他在文字中透露出对祖国文化的热爱,但从不刻意表现“爱国”情怀。他在诺贝尔奖演讲稿中这样写道:“文学的优点之一就是它能帮助一个人使其存在的时代变得更特殊,使个人区别于前人和同辈,避免同义反复、千篇一律——避免那种尊称为‘历史牺牲品’的命运。艺术尤其是文学的不同寻常之处,文艺区别于生活之处,正在于厌恶重复。在日常生活中,你可以将同样的笑话讲三次,而且三次都引人发笑,这可以成为聚会的活力,然而,在艺术上,这种做法可称为‘陈词滥调’。”
一个易卜生主义者,一个布罗茨基这样的个人主义者,他们思想自由,个性强烈,绝对不受任何国界的限制,甚至也不归属于任何社会。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们确实可以“四海无家”,而又能够做到“四海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