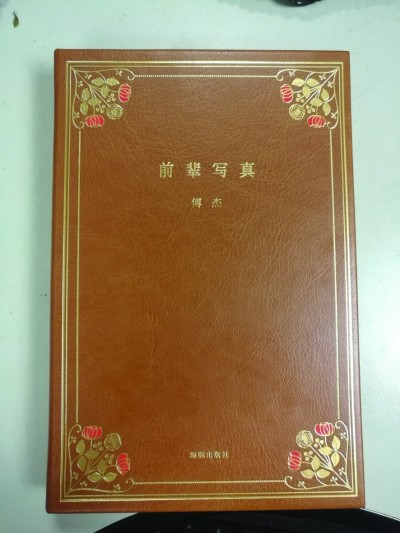
《前辈写真》
傅杰著
海豚出版社出版

黄永年先生
复旦大学中文系傅杰教授在《前辈写真》一书中,为姜亮夫、蒋礼鸿、沈文倬、郭在贻、王元化、朱维铮、程千帆、许国璋、黄永年、朱德熙等多位在人文学术领域德高望重的老师作传。作者从先生们的治学、教书、为人处世等方面入手,生动而全面地展示了大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新颖而务实的教育理念以及谦和的处世态度,让读者能够近距离领略到先生们的风范。
一
1983年我考入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学习中国古典文献学。毕业前一年所里给每个同学发了一本教材,这就是刚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古籍整理概论》。
绝不夸张——这本不厚的书我是一气看完的,因为内容太充实,论断太明快,文字也干净利落,读时常常眼前一亮,读完的感觉就两个字:过瘾!好书常有,而读来有这等快感的并不常有。
黄先生后记称这是他应教学急需在十来天里赶出来的讲义,所以“行文之草率,以及论说之欠精密,自可想而知”。不过这样的假谦虚绝非他的风格,简直就是欲擒故纵的铺垫——这不,其下立刻转折:
好在所讲的都是多年来蓄之于心的东西,自己没有考虑过的,没有弄懂的,决不在这里乱说,也决不用模棱两可之词来敷衍搪塞。个别承用成说之处,则必有所推阐演绎,决不径自抄袭,庶无背于“毋剿说,毋雷同”(《礼记·曲礼》)的古训。在这两点上自己还是感到比较踏实的,不致面对学生心虚脸红。
而对文字他的追求也是自觉的。在自己教材出版的同时,他撰文批评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教材《图书馆古籍编目》,不仅因为其书屡见的“毛病甚至错误”,也因为其书“很多地方白话文言夹杂,很不自然,读起来感到别扭,有些句子更是词不达意,或者可说文理欠通”。
《古籍整理概论》对我影响深远,是我常引用、也是我常宣传的——不仅向门生,也在受命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古籍出版社青年编辑培训班授课时,拿它跟吕叔湘先生的《标点古书平议》一起向学员做了推荐。
二
见到黄先生已是我毕业留校之后的事了。
1986年11月,所里请时任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的黄先生来讲学,连续五次,三次系统的碑刻学,外加两次文史专题。
黄先生个头不高,脸形瘦削,双唇偏薄,因此笑起来有点不怀好意;双目炯炯,因此怒起来有点凶光逼人。
而第一次上课,他就怒了。
那是晚上,被临时征用的大教室里有不知情的学生,原来放了书包,准备吃了饭来自修,一看有人上课,就进来取书包,一进一出,关门开门,前两个黄先生还忍着,等出现第三个他就发飙了:
“谁让你们随便进来出去的?”
原来黄先生视传道授业解惑为天职,自1957年莫明其妙成了右派,他已被剥夺上课的权利多年,因此更珍惜这失而复得的权利,一向兢兢业业,全力以赴——不到下课时间,水都不喝一口,自然不容学生自由散漫,不容上课受到骚扰。
为了消他火气,身份刚转换成教师的我解释这个原是自修教室。不料黄先生误以为我是在为学生自由出入的权利辩护,火更大了,冲着我瞪眼道:
“不管是不是自修教室,他们难道看不见我在讲课吗?”
三
如此不假辞色,论学当然也不可能遮遮掩掩——这只要读过《古籍整理概论》以及他的文章就能明白,只是讲课更加直白无隐,随口而出的往往都是历练多年获得的真知灼见。比如介绍金石学著作,最推崇叶昌炽《语石》,称“老先生文笔很好,看看对提高文字水平也大有帮助”。而文物出版社影印《八琼室金石补正》,这样给专业人士用的书原本无须句读,偏偏多事要加,却“标得一塌糊涂,文理狗屁不通,真丢人!”
由碑刻涉书法,黄先生说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文笔很好,漂亮极了,后人望尘莫及”;但北魏的字真不怎么样,他却“把北魏捧上天,胡说八道,十句相信三句都要上当的”。而“怀素写狂草,不敢恭维,字总要写得让人认识”。他引元好问《论诗绝句》“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教训我们这类字“吃得住的大书法家可以偶一为之”,今天有些小青年真书还不会写,上来就写狂草——他的薄嘴唇上翘起来,嘿嘿冷笑。
那时不知道黄先生的书法篆刻也是功力湛深的,中华书局还曾出版过《黄永年印存》。没好意思开口求他动过刀,但开口求他动过笔——他给我写了楷书(显而易见是学的褚遂良)自作七绝,当然那是后来的事了。
四
黄先生师承有自,而又天才卓荦,加上他不是性格内敛的人,所以自视之高,从笔端到言谈时有流露。然而他也是服善的。他吹嘘过自己在学校里、在社会上仗义执言的事迹,但他撰文说:钱锺书先生参与翻译《毛泽东选集》,指出作者误引《西游记》中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的故事;而他上世纪五十年代读毛选时见毛误引《水浒传》林冲“一棒扫翻”洪教头为“一脚踢翻”却无胆量纠谬。在给我们讲唐代文史专题时涉及《论佛骨表》,对韩愈批评宪宗迷信佛骨想迎以祈福的愚行会“伤风败俗,传笑四方”而不惧差点招来杀身之祸的勇气赞佩不已,坦承“换了我是不敢的”。十年之后,他在《论韩愈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还表彰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壮举”,“其言行一致、不计安危且决不悔改的形象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五
1992年我离开杭州大学,到王元化师兼职的华东师大中文系跟他读博士。
书不可能全部运去,只能精选常置案头的要籍,《古籍整理概论》以及1989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行的黄先生与门人贾宪保先生合著的《唐史史料学》自然都属于随身携带品。
那时的博士生导师不像今天这样泛滥,华师大还给每位导师配备了副导师,我的副导师之一是陈谦豫先生。初来乍到,已留校执教的师兄胡晓明为我介绍新环境,特别提到陈先生是古典文学教授,师母黄世瑜先生是同系文艺理论教授,他们的公子陈引驰在复旦中文系读博士,家学渊源,根柢深厚,可以找他多多交往。
没等我去找引驰,引驰先来找我了,从此成为时常相见、无话不谈的朋友。
1995年博士毕业,正赶上复旦新成立中文博士后流动站,我即提出申请。如今的中文系主任、继章培恒、陈思和先生之后成为第三任中文博士后流动站站长的引驰那会儿还是小字辈,专门等候学术委员会的遴选会议结束,向他的导师陈允吉先生打探了结果,赶回师大向我通风报信:全票通过。
从此更开始了延续至今的同事生涯。
引驰结婚——我还是证婚人,跟太太去游览西湖,我杭州的住所正好闲置着,就让他住那儿。
过两天回来还我钥匙,他突然诡谲地问我:
“我记得你那本《唐史史料学》是划过很多红线的?”
我说:对啊。
“你在手边吗?”
我说:在啊。
“所以”——终于切入主题——“你杭州那本新的是另外一本吧?”
引狼入室,露了富了。
原来早年书的流通渠道不畅,黄先生的著作在杭州的书店根本不见踪迹,《唐史史料学》仅印了一千五百本,我是向出版社邮购的。因为难得,更因为崇拜,怕读破,怕遗失,于是邮购两本,一本带来上海,一本搁在家里。而以唐代文学为研究重点之一的引驰也没有这本书。
事已至此,只好认账。我说:是啊。
“所以”——他脸红了一下——“我拿回来了”。
生米煮成熟饭,索性作大方而高兴状吧——虽然心中隐隐不舍,我说:好啊。
不过确也值得高兴:一来作为唐代文学专家,引驰肯定比我有更内行的解悟,书归他正是得其所,何况我还留着一本。而他做事一向讲究风度,不是受的诱惑太大必不至此——由此也可见黄著的魅力。二来真正众望所归的好书总还是会不胫而走,事实证明我的囤货行为是可笑而没有必要的。复本遭劫之后,我的“孤本”既未读破,也未遗失。而《唐史史料学》经修订,2002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再版,任社长的友人王为松先生送了我一本;2015年由中华书局出新版,黄先生的哲嗣黄寿成先生又送了我一本,所以现在我不止是复本、而是有三本了。
六
几次见面,老缠着黄先生问这书问那书,一天他说:你这么爱书,给你介绍个我爱书的学生,你们可以做朋友,叫辛德勇。
他的嘴角又上翘起来,不过这次不是不怀好意,而是尽形于色的得意,眉飞色舞地夸赞说,这是一个如何如何的书呆子,书读得如何如何好。他的太太——又一个让我陌生而让黄先生自豪的名字——韩茂莉是同行,也是书呆子,两个人去北京旅行结婚,家具还没置齐,把钱都换成书就回来了。
无论各方面的学识,还是对书的在行,我跟得他真传又勤奋过人的德勇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但黄先生的话是不错的,我们果然成了好朋友。
第一次见德勇,是1996年2月下旬,他跟黄先生同来复旦参加纪念谭其骧先生八十五岁冥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会议25日开幕。28日闭幕那天,由黄先生率领,周振鹤先生、德勇和我一起跟他去苏州古籍书店访书。掌管线装旧书的是业内著名的行家、也是黄先生结交已半个世纪的故友江澄波先生。
等一望见书店,像闻着了腥味,老猫开始紧张起来,冲同样虎视眈眈蓄势待发的小猫道:
“辛德勇,等一下进去了,你跟在我后面看。”
谙知师傅手段的爱徒毫不犹豫,断然拒绝:
“那不行,您往左边看,我往右边看。”
哈哈,黄先生一直以德勇能传其学而骄傲而炫耀,不知在那一瞬,他会不会有点儿后悔——虽然还没到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程度。
德勇曾在黄先生大寿之际进贡自己最得意的收藏,但在书店不肯相让——也难怪,没准让一让,他就成为只是来给师傅扛书的书僮了。
虽已年逾古稀,黄先生却精神矍铄,为赶时间,我们来回火车买的居然都是站票。去时黄先生就兴致盎然,一路畅谈;归途更因收获甚丰,毫无倦意。后来在《买书经验杂谈》一文中他还愉快地提及了这次“和辛德勇同学及周振鹤、傅杰诸公去苏州古籍书店买书”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