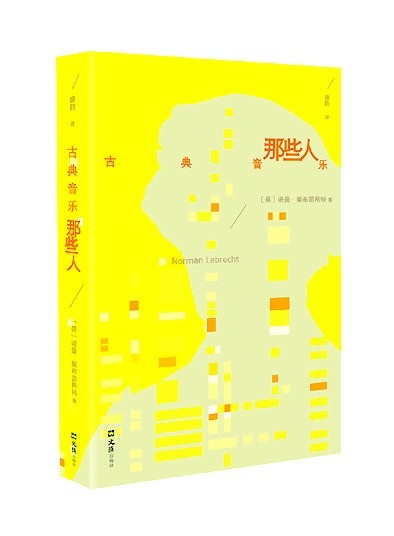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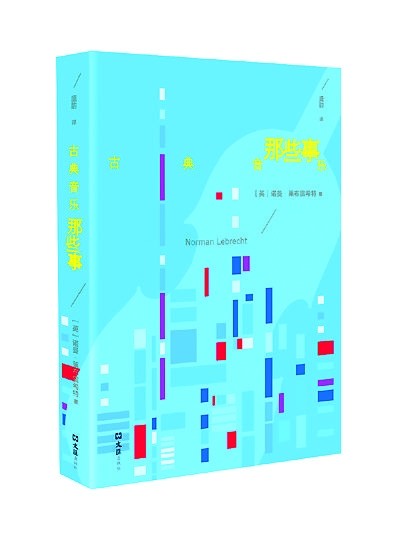
《古典音乐那些人》《古典音乐那些事》
[英]诺曼·莱布雷希特著
盛韵译
文汇出版社2017年8月版
“身处网络时代,为什么我们依旧如此痴迷古典音乐?”英国知名乐评人诺曼·莱布雷希特在这两本书中,为我们梳理西方音乐千年传统中那些独立不羁的灵魂人物和生生不息的精神特质。从大师贝多芬、马勒,到新生代的特里福诺夫;大到音乐产业的生死存亡,小到小镇人民自娱自乐的票友歌剧节……作者以其犀利、幽默,又富有哲理的笔调,为我们展现了那个真实有趣的古典音乐世界。
柏辽兹为什么不招人爱?
柏辽兹向来不招人喜爱。每到他的周年纪念,全球的剧院和乐团会尽职尽责地把他的作品展示一遍,但感觉更像义务而非真心投入。公众对他的评价也从未有过任何改变。
柏辽兹葬在蒙马特公墓,旁边是两任悍妇太太哈丽叶特·史密森和玛丽·莱西奥。曾有人提议将他的棺椁移去先贤祠,结果被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否决了,政客就柏辽兹是否配与安德烈·马尔罗、让·饶勒斯和大仲马这样的法国伟人分享荣耀进行了激烈辩论。
很少有像柏辽兹这样的名人在自己的祖国如此不受待见。巴黎没有以柏辽兹命名的街道,法国无法原谅柏辽兹,因为他不承认法国文化天生优越。柏辽兹在异国寻找灵感,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来自莎士比亚,《哈罗德在意大利》来自拜伦,《浮士德》来自歌德,管弦乐作品来自贝多芬。
正像所有伟大的艺术家那样,柏辽兹只听从自己的内心期待。他父亲是个外省医生,一心要他子承父业,结果他辜负父亲的期望,从医学院退学,转去音乐学院,但很快就对法国音乐机构的意大利式平庸愤怒不已。由于无法让自己的作品得到公演,他只能写乐评谋生,带着“一成不变的冷笑”去参加所有音乐会。被他冷嘲热讽过的乐手故意毁掉了他的《安魂曲》和第一部歌剧的首演。柏辽兹说:“地狱里的人的命运也要好过我。”
他在不安分的天才中找到了一席之地。1830年代的巴黎吸引了无数艺术流亡者:肖邦、李斯特、瓦格纳、门德尔松和海因里希·海涅,海涅说柏辽兹有“硫磺般闪亮的反讽”。李斯特帮他安排了德国巡演,指挥管弦乐队。他的足迹遍及奥地利、俄罗斯和英格兰。1854年在伦敦,柏辽兹与瓦格纳前后脚分别指挥了两支竞争乐团,柏辽兹得到的评价更高。瓦格纳借鉴了柏辽兹的不少想法,却从未原谅他。
柏辽兹野心的巅峰是那出五个小时的歌剧《特洛伊人》。巴黎完全不顾其恢弘壮丽,只上演了其中的三幕。他因失败而沮丧,两任妻子都先他而去世,最后他的儿子也发烧而死。他一蹶不振,写了一本尖酸刻薄的回忆录,指定身后出版。柏辽兹于1869年3月去世,终年六十五岁。他的临终遗言是:“最终,他们会演奏我的音乐。”
人们的确做了,但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柏辽兹的声誉并未因音乐而彰,而是通过一本教科书《配器法》。他拒绝为巴黎沙龙写美妙动听的小曲,而成为了大型管弦乐作品的老法师。马勒和施特劳斯都仔细研读过这部著作,它为里姆斯基·柯萨科夫随后写成的教科书奠定了基础,后者曾和学生一起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如痴如醉地聆听柏辽兹指挥的音乐会。
1890年,《特洛伊人》在卡尔斯鲁厄的两个夜晚首次上演了五幕全版,而将真正的原版设计搬上舞台是在1958年的科文特花园。
柏辽兹交响曲的戏剧效果、大合唱的万种温柔都很符合英国人对壮观和多愁善感的特别嗜好。现代最显赫的柏辽兹诠释者几乎都是英国人,从华丽的托马斯·比彻姆到沉思冥想的科林·戴维斯,后者和伦敦交响乐团录制了一套十二碟的柏辽兹作品精选。而最全面的柏辽兹传记,也出自英国评论家戴维·凯尔恩斯之手。柏辽兹二百周年诞辰时在巴黎上演的《特洛伊人》,由约翰·艾略特·加迪纳指挥。
法国无法忍受如此风生水起、如此独立的灵魂。虽然柏辽兹得到了比才和梅西安的青眼,但现代派主流人物从德彪西到布列兹都偏爱与瓦格纳泥泞地扭打,而对家门口的天才视而不见。柏辽兹在法国依然是弃儿。直到现在还有人说他是疯子,或是用更糟的字眼。他被与撒旦之类的人物相比,乘着《浮士德的劫罚》的乐谱封面佝偻盘旋在蒙马特公墓的上空。
法式矛盾传染了整个音乐世界,人们将柏辽兹视为偶然的艺术,属于个人偏好而非乐史定论。法国固有的小家子气诅咒了它最伟大的作曲家,他被永恒拒斥,尸骨留在边缘墓地。
疯子舒曼
1854年2月一个下大雨的早晨,德国最著名的在世交响乐作曲家穿着大花睡衣,走出杜塞尔多夫的家门,穿过狂欢节的街道,来到市中心一座老桥,纵身跳进了莱茵河。时年四十三岁的罗伯特·舒曼最后从水里被救了出来,人们认出了他,小心翼翼地送他回家,这时他的妻子克拉拉正怀着他们的第八个孩子,含着泪水将他擦干净,送上床休息。
之后的十六天,克拉拉一直守护在舒曼身边,直到医生警告他可能会伤害她,她才忍痛让舒曼住进波恩的一家疗养院。在那里,舒曼的精神病症状不断加重,加上三期梅毒,医生为医治这两种疾病用了过量的汞,导致他两年后去世。他的葬礼在波恩举行,人多得“好像世上没有比这更悲伤的事情了”,舒曼的徒弟勃拉姆斯陪着克拉拉引领了葬礼队伍。
这是欧洲文化的转折时刻,浪漫主义天真之终结的里程碑是死亡,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同年因相似的原因去世,舒曼曾将海涅的诗歌谱成了美妙的声乐套曲《诗人之恋》。舒曼的一生跟他的作品所描述的一样,一个出身林地的天真孩子来到无可阻挡的铁轨和工业化的世界。他追求少女克拉拉的方式好像一个中世纪人,公然反抗她的暴君父亲(也是他自己的钢琴老师),等她一成年就结婚,他们的爱意在信笺和日记中流淌。时至今日,波恩墓地他们合葬的灵台雕塑上,她依然满怀仰慕地坐在他的脚边。
但克拉拉不知道的是,舒曼长期求爱中表达出的过度热情其实是躁郁症的表现。舒曼在狂热与忧郁之间摇摆不定,有时甚至会瘫痪。因为时常记忆短路,他被杜塞尔多夫管弦乐团和合唱团炒了鱿鱼。克拉拉再度怀孕,舒曼陷入疾病频繁发作的痛苦中。悲剧的结局无法避免。
舒曼无疑是音乐史上的关键人物。在交响曲的发展中,舒曼是贝多芬和勃拉姆斯中间的连接;在艺术歌曲形式中,他跨越了舒伯特和理查·施特劳斯之间心理复杂性的鸿沟。若没有舒曼,音乐史会变得难以理解。
然而舒曼永远不可能像莫扎特那样受欢迎,他的音乐也不像莫扎特的那样悦耳。莫扎特的天才故事可以变成滚滚财源,而舒曼的名字暗示着疯狂和自杀。的确,舒曼写下的每一个音符背后都有一股黑暗的潜流。正如所有真正的浪漫主义者,海涅和舒曼无法将爱与死分开,而他们在生命最阳光的时候已经预告了这一切。
人们很难去颂扬这位如此病态地迷恋爱与死的作曲家。舒曼的问题用一个词概括,就是疯癫。我们对超过极限的创造者感到害怕,不管他们是雨果·沃尔夫那样的作曲家,还是拜伦那样的诗人,还是梵·高那样的画家。我们不敢靠近。我们对这样的艺术家敬而远之,于是失去了理解这种洞悉我们潜意识的独特艺术的所有机会。
我能够理解靠迎合公众喜好讨生活的艺术家和管弦乐团为何冷落舒曼。但这似乎是一种可怕的荒废,错失了探索人类经验深度的机会,琅琅上口的简单旋律再度战胜了人类文明的丰富性。
反省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这是年历上最盛大的古典音乐会,全球八十一个国家的六千万观众可以观看电视转播,而且数字与年俱增。然而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核心——维也纳爱乐乐团却面临歧视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指控,埋藏于遥远纳粹年代的肮脏秘密也随之浮出水面。
维也纳爱乐的乐手由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乐手同事中遴选产生。它是世界上最后一支接纳女性乐手的乐团,直到 1997年2月以前一直保持全男班。今天,它仍是世界古典名团中女乐手最少的,一百二十六人中仅七名女性。
维也纳爱乐乐团为性别歧视编造了各种各样的借口,一会儿说有孩子的女性不适合长时间海外巡演,一会儿说她们有碍于整齐划一的音色。他们说,人事变动太多会危及乐团演绎贝多芬、勃拉姆斯、布鲁克纳和施特劳斯作品的权威性。但是性别歧视违反了法律。2011年7月,面对奥地利国会强烈反对维也纳爱乐乐团明目张胆的性别歧视,奥地利政府削减了二百二十九万欧元的乐团预算作为惩罚。然而情况毫无改观。
维也纳爱乐对少数族裔也采取同样的非法歧视。没有亚裔,没有非白人乐手,即便维也纳音乐院校里三分之一的学生来自远东。新日本爱乐乐团的一位大号乐手杉山康人于2003年通过面试加入了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但被拒绝进入维也纳爱乐乐团。三年后杉山辞职,转投美国顶尖的克利夫兰管弦乐团。在维也纳爱乐,会籍往往与业务好坏无关,而是父子相传。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发言人则否认存在种族排斥,指出有两名乐手的父母有亚裔血统。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音乐总监弗朗兹·威尔瑟·莫斯特也是2013新年音乐会的指挥,他曾在一次主题演讲中散播了一种颇为流行的恐惧心理:“我们是要面临‘亚洲化’了吗?就像一百年前‘美国化’那样?”恐外心理植根于维也纳人的DNA中。在维也纳,“外国人”指的是多瑙河盆地之外的任何人。维也纳爱乐可以容忍罗马尼亚人,但俄罗斯人就不行。
种族歧视的指控,令人想起维也纳爱乐在纳粹统治那七年中扮演的角色。2013年3月是希特勒治下德奥合并七十五年,奥地利历史学家提醒报纸读者注意,当年有二十五名维也纳爱乐乐手在1938年之前已是正牌纳粹,不久后乐团里几乎一半乐手加入了纳粹党。十五位犹太乐手或是政治上左倾的乐手被送进了集中营,导致七人死亡。
值得赞扬的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现任主席在1992年的一部史书《国王的民主》中承认了乐团犯下的许多错误。海尔斯伯格许诺,要在爱乐乐团的官方主页上提供更多纳粹时代的信息。
迫于压力,他必将坦白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起源这一高度保密的信息,这项新年活动是 1939年在纳粹的首肯下筹划设计的。第三帝国企图将奥地利降低到行省的地位。维也纳爱乐乐团为了保住自己的国际声誉,动用了许多纳粹党内关系,赢得了至关重要的新年演出特许权。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从诞生之日起,就植根于乐团与纳粹主义的共谋之中。历史事实再加上多年不断的歧视惯例,再也不应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