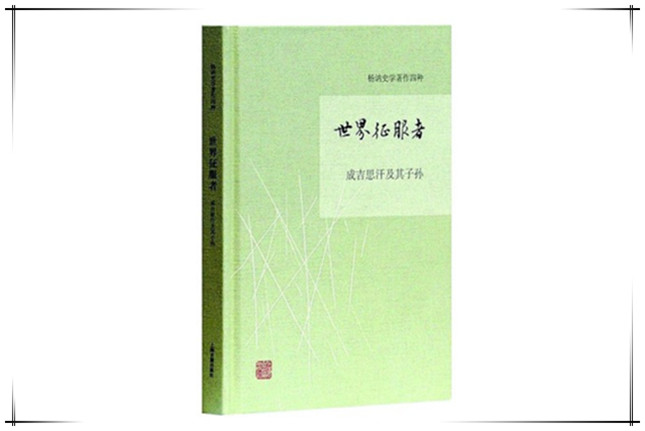
▲《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
金庸的“射雕三部曲”借宋元历史大背景敷陈故事。对小说中出场或提及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对全真教创教者王重阳及其弟子丘处机等全真七子,对朱元璋曾隶属明教教主张无忌的麾下,读者都是耳熟能详的。倘若有人读过小说,还想究诘这些人或事在历史上是否一如小说的描述,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杨讷史学著作四种”(包括已出的《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元代白莲教研究》《刘基事迹考》与即将出版的《丘处机“一言止杀”考》)就有三种与此有关,值得金庸的拥趸们开卷把读。
由于治宋史,也须关注有交集的蒙元史,我早就知道作为元史名家的杨讷先生,1980年代已读过他的《元代的白莲教》。时隔多年,他将这篇论文扩充为专著《元代白莲教研究》。其序文说:“在过去的论文里我曾谈到白莲教在南宋的情况,但资料准备不足,写得很简略,篇名不敢兼题宋代。现在这本书虽然在南宋部分有所增补,还是没有勇气在书名上加一个‘宋’字,原因如故。”然而,即便他自谦“简略”的追溯,当年已让我对南宋白莲教有清晰的把握;由此也见他治学的严谨与论史的明快,这些特点同样贯穿于他的所有史著。

▲《元代白莲教研究》
金庸认为朱元璋出身明教,大明国号即出于此,那是采纳了明史大家吴晗的结论。在《明教与大明帝国》里,吴晗从摩尼教(即明教)与白莲教都被统治者斥为“事魔邪教”,又都“不事荤酒,不杀物命,修忏念佛,均托于佛教”,认定“明教之久已合于白莲社”。《元代白莲教研究》一方面以大量史证说明“明教并没有与白莲教混合”,彻底否证了前贤的定论;一方面对朱元璋曾拥戴的韩林儿之号“小明王”出典于“明王出世”,对朱元璋之所以定国号为“大明”,有理有据地揭示都出自《大阿弥陀经》,那是白莲教崇奉诵读的经典,与明教教义没有丝毫关系。
在金庸笔下,全真教三代教主王重阳、丘处机、尹志平俨然是正义的化身,在金国、蒙古南侵中,成为南宋民众的北方盟友。他的这种定位也有所本,即陈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其中将“汴宋遗民”的身份泛加于全真七子。这部名著撰于抗战沦陷中的北平,陈垣自称“有感于宋金及宋元时事,觉此所谓道家者类皆抗节不仕之遗民”,有点“以古人自况”。《丘处机“一言止杀”考》则认为,可以理解史学大师的用心与感情,但仍须坚守“就学术论学术”的求真原则,以史实力证其“遗民说终究是不能成立的”。至于号称“一言止杀”的丘处机,据说乾隆帝也大为赞佩,为撰联语云:“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丘处机“一言止杀”考》同样无可辩驳地坐实:这一谎言不过是其后继者接踵叠加的“故事新编”与“故事补编”,无非“借抬高父师来抬高自己”。丘处机在蒙古入侵中原时扮演的角色,充其量指望在中原“建立一个由蒙古操控的刘豫式傀儡政权”。总之,丘处机不仅不是“汴宋遗民”(且不说他出生时北宋灭亡已有21年之久),也从未有过“一言止杀”的济世义举。而成吉思汗也从没收敛杀心,临终遗言还特地交代:西夏都城出降之日须将其国君与居民全部杀尽。

▲杨讷著《刘基事迹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对成吉思汗能否称得上英雄,《神雕侠侣》结尾曾借郭靖之口有过评断。成吉思汗家族人才辈出,“射雕三部曲”还写到其子辈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与孙辈蒙哥、忽必烈。蒙古铁骑西征南侵,所到之处刷新了欧亚大陆的政治版图。《世界征服者》全景勾勒了铁木真祖孙三代充满血与火的征服战争,叙事要言不烦,举重若轻,行文深入浅出,明白晓畅。对金庸小说涉及的成吉思汗祖孙事迹与战绩感兴趣的读者,也一定会开卷有益的。值得一提的是,在末章《千秋功过》里,著者提纲挈领地介绍了中外史学界对蒙古征服史极具争议的不同评价,明确认为中国史学界在评论蒙古南侵与西征上采用了双重标准,即“把成吉思汗的南侵作为中国的内部问题来处理,而把西征作为对外问题”,并重提鲁迅说过的老问题:成吉思汗是不是我们中国的汗。他的看法对近年“崖山之后无中国”的热议颇有启发性:
历史的流程是自上而下的发展,古人是按他们那时的状况区分内外的,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观念和国界去划定古人的行为空间。如果我们的史家能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就会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成吉思汗祖孙三代对南对西的征服活动,我们的评论也将会更加符合历史实际。
“射雕三部曲”没写到刘基,《碧血剑》里则有年老盲者唱曲道:“神机妙算刘伯温,算不到:大明天子坐龙廷,文武功臣命归阴。”作为神化人物,刘伯温在民间的知名度几与诸葛亮相埒。他身后之誉云遮雾绕,历600年而不衰。这种美誉,据《刘基事迹考》归纳,一是对明朝开国的贡献,被誉为所谓“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一是有超乎常人的智慧,被型塑成占卜星象、预测吉凶的术士与精通兵法、多智善谋的军师。著者以翔实的文献与严谨的推理,采取考证与叙事相辅相成的手法,廓清了明代以来给刘伯温笼罩的光环,令人信服地指出:“刘基对明朝开国的贡献并不那么大,他的智慧也不那么超人。”至于神化的根子首先“出在朱元璋”,朱皇帝之“嘉许刘基预知天命,是为了烘托自己”;刘基死后20余年,由其孙辈操刀而托名黄伯生的《故诚意伯刘公行状》出笼,一方面编造了刘基的许多荒诞故事,一方面掩饰了他的某些真实事迹。其后,他的后代与乡人意犹未足,几经哄抬,终于将其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还不包括《烧饼歌》之类的民间附会)。
“杨讷史学著作四种”论述的人与事都进入了民间传说或历史小说的领域,但或真伪混淆,或聚讼纷纭,让人有莫衷一是之慨。倘若读者不满足于小说或传说的层面,还想进而了解其历史真相的话,这套小丛书无疑是值得信赖的上乘之选。
文:虞云国 责任编辑:蒋楚婷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