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5月9日,是王元化先生逝世10周年纪念日。
作为思想家的王元化,不是生活在书斋里的老学究,而是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他的思考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现实穿透力,他提出的问题,往往是紧扣国家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问题,他的观点一针见血,直接进入问题的实质和要害。”然而在我看来,王元化的思想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文字的力量。若从“全人”的环视角度考察,我们会对王元化著述的特殊性产生一种新的、更有意味的认识。
见过王元化先生的人都有一种印象:他的身上固然有英锐、激烈的一面,然而更多、更典型的,则是他沉潜、雍容的特质。他是一个不断思考着,不断产生问题意识,并且为此真正体会到“快乐”的人。他曾解释说: “什么是乐呢?就是达到一种忘神,你不去想它,它也深深贴入到你的心里边来了。使你的感情从各方面都迸发出一种热情……”王元化先生始终保有一种年轻、开放的生活态度和宽容豁达的理性精神。虽然是一位老者,但是他对新事物新思想充满了热情,从来没有泥古不化的偏执;他研究古典学问,但是这种研究给人新鲜、深刻的现实启发;甚至他平时的装束也常常是轻松的款式,头发总是梳理得整整齐齐,金丝边眼镜后面睿智的目光炯炯有神。总之,他的身上焕发着热爱生活的光芒。他既是一个思想深刻的人,也是一个讲究“形式”的人。

▲王元化著作《思辨录》
2004年12月,中国美术学院于上海美术馆举办了一场“清园书屋笔札展”,同时还举行了汇集展出作品的《清园书屋笔札》一书首发式。王元化先生时年84岁。我在《“敬正”之美》(载《文汇报》2010年11月21日)一文中说:“这次展出的51幅书法作品,皆为王元化先生著作语要的抄录,内容涉及思想、行旅、往事、谈艺、诗作、楹联,所有墨韵均由元化先生于当年夏秋之际挥毫书就。此事沪上多家媒体作了报道。许江先生在介绍文章中写道:‘王先生之笔札的意义首在为文与书写的敬正。这些文字作为语要及其思想的载体,有书写的清纯、有运思的节度,蔚然而成楷正的气象,披露一代思想者的胸襟。’这段文字中让我眼睛一亮的,正是‘敬正’二字。”“‘敬正’是元化先生为人精神的写照,也是他对待学问和编辑、出版、装帧等事宜的态度和追求。”

▲王元化书法
与欣赏他的书法作品一样,如果你细阅元化先生的文章,一定还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重视用语规范、辞藻典故、修辞逻辑的作者。读他的文字,会有一种强烈的被推着往前走的感觉,或者说,能体悟到一股孟夫子的文字才具有的那种“浩然之气”。这里可以试举几例:
“就思想体系来说,我认为后一代对前一代的关系是一种否定的关系。但否定就是扬弃,而并不意味着后一代对前一代的思想成果彻底消灭,从而把全部思想史作为一系列错误的陈列所。”
“长期以来,由于公民权利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维护,以致影响到每个公民对于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采取了一种不关痛痒的冷漠态度。这是形成长期缺乏公民意识的主要原因。”
“我是一个用笔工作的人,我最向往的就是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留下一点不媚时、不曲学阿世而对人有益的东西。我也愿意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唯新唯洋是从的风气与40年来教条主义的感染不无关系。教条主义与趋新猎奇之风看起来相反,实则相成。两者皆依傍权威,援经典以自重,而放弃自己独立见解。沿习既久,惰性已成,个性日丧,创造力终于斫伤尽净。”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理念的自我综合、自我发展、自我深化的运动过程。首先,以理念自身作为出发点,然后理念将自己外化,转化为自然界。理念由自在阶段发展为自为阶段后,再进一步返回自身,终于在人身上重新达到自我意识。”
“正像赫兹列特所说的,约翰逊不理解莎士比亚,因为他的理智根本无法掌握美。这种抑扬任声的文体,我姑以‘褒贬格’名之。”
“一千多年前,鸠摩罗什作为一个异邦人来到中土,他以宗教的虔诚传译佛典,自称未作妄语,死后舌不焦烂。我觉得这种对待自己事业的精神,至今仍值得效法。”
诸如以上这些洋溢着修辞之美的精彩语句,在王元化的著述中真是不胜枚举!尽管王元化经常说自己不善于即席讲话,但是他那些往往经过反复锤炼的文字,却实在是十分契合古罗马诗人朗吉弩斯所说的“崇高风格”:“崇高是一种整体的力量,如同霹雳。只有思想庄严的人才会有语言的宏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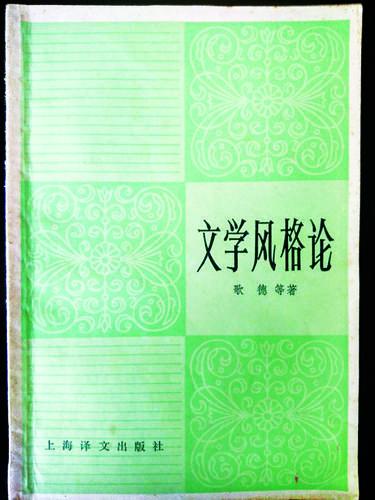
▲王元化著作《文学风格论》
早在1982年的时候,上海译文出版社就出版了王元化翻译的小册子《文学风格论》,这是译者为用作撰写《〈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参考资料而译出的。小册子收集了德国歌德的《自然的单纯模仿·作风·风格》、威克纳格的《诗学·修辞学·风格论》和英国柯勒律治的《关于风格》、德·昆西的《风格随笔》四篇文章。书的篇幅虽然不大,但是却探讨了一系列关于写作的风格和修辞问题,在当时引起了不少人士的注意。元化先生在此书的“跋”中,赞同歌德将“自然的单纯模仿”“作风”和“风格”作为不同等级的艺术作品的特征来看待,他说:“事实上,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到美学的根本问题,即审美的主客观问题”,“‘风格’则是主客观的和谐一致,从而达到情景交融、物我双会之境。因此,歌德认为它是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的境界。”元化先生还引用黑格尔的话说:“黑格尔《美学》认为‘作风只是艺术家的个别的因而也是偶然的特点,这些特点并不是主题本身及其理想的表现所要求的’,‘作风愈特殊,它就愈退化为一种没有灵魂因而是枯燥的重复和矫揉造作,再看不出艺术家的心情和灵感了’。”王元化认为,介绍这些观点可以有效地提高人们的艺术鉴赏力,培养读者纯正的审美趣味。
与王元化打过交道的一些出版家都有这样的体会,那就是王元化对自己的著作在文字、校对、版式、装帧等方面有很高的要求。他对于文字经常一改再改,力求更佳。在自己晚年的精华集《思辨录》(定本)壬辑中,王元化特意收录了四则直接与修辞有关的文章:《文章简繁》《古文朗读》《修辞例一》《修辞例二》,可见作者对文章修辞的高度重视。
在《修辞例一》中,元化先生写道:“我没有钻研过修辞学,但写作时为了达意的准确,也常常对自己的文字进行修改。有时也把修改的经过记录下来,例如《记辛劳》一文,其中倒数第二段最后一句,曾修改数次。”元化先生列出了修改的过程——
(初稿):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天爱才和忌才总是纠缠在一起?
(其后):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天地爱才,还是天地忌才?
(接着当天夜里醒来时,念及此句仍觉不妥,遂改成):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天地爱才,还是天地忌才?为什么命运要将众多的苦恼降在这样一个才气横溢的人的身上?
(过后再读全文,读至此句仍未惬于心,再改成):我不知道这是天地爱才,还是天地忌才?既然这个人被赋予了大量的才华,为什么又偏偏要将众多的苦恼降在他的身上?
(再读仍觉未畅己意,至今天清晨,卧床未起时,伏枕再改成现在的句子):这究竟是天地爱才,还是天地忌才?既然赋予这个人以过人的才华,为什么又偏偏要将众多的不幸降在他的头上?
由此可知,元化先生对文字修辞的重视几到了殚精竭虑的程度。
在《修辞例二》里,元化先生回忆了自己替余秋雨修改相关文字的经过:“余秋雨所撰《长者》,嘱我修订。我向他说,我的修改只限于涉及张可和我本人言行部分(例如,后经我改动的有秋雨记张可嘱他学英文的谈话中,用了 ‘必须’‘应该’字样。我说,据我所知,她从未用过这种社论式的命令词)。文中所记我对张可的评语是经过我反复修改过的。”王元化先生记录道——
秋雨记我所述原文:
张可心中无恨。从不相信斗争哲学,只散布善良、温柔、宽恕。跟我受了几十年的苦,从未流露出一点一滴的抱怨。像我们这种敏感的文化人,只要有一个眼色中稍稍有点不耐烦,也能立即感到,刻下深深的伤痕,但在她的眼睛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眼色。
最初,元化先生只是在原稿上作了一些润色和调整,然而最后终于修改成如下的文字:
张可心里似乎不懂得恨。我没有一次看见过她以疾颜厉色的态度待人,也没有一次听见过她用强烈的字眼说话,总是那样温良、谦和、宽厚……23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无穷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人受过屈辱后会变得敏感,对于任何一个不易察觉的埋怨眼神,一种稍稍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始终没有这种情绪的流露。这不是任何因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为她无法依靠思想和意志的力量来强制自然迸发的感情,只能听凭善良天性的指引才能臻于这种超凡绝尘之境。
经过修改的文字不仅更加具体准确,而且体现了一种非常适合叙述对象的、得体的博雅风格。
语法、逻辑、修辞,曾是西方古代十分重视的“七艺”中属于“文字”的三艺(另外属于“数字”的四艺,是算术、几何、音乐、天文)。西方传统修辞学理论是围绕五个基本主题来组织的,那就是:布局、表达、构思、文体和记忆。修辞以语词为本原,它在整个语词体系中的位置,主要体现在对正确表达(说服)的关注。今天我国大学的中文专业也依旧有语法、修辞、逻辑课,正说明了这类训练在写作时的重要性。反之,倘若失去了这种“文字的力量”,思想的表达自然就会大打折扣。正像元化先生不是书法家,但是写得一手隽永好字一般;元化先生也没有专门研究过修辞学,但是他处处遵循为文的法度、锻炼文字的生气和意蕴,呈现出很高的文章境界。
王元化先生装束的恰宜、书写的敬正、文字的修辞,与其丰沛、深湛的思想一起,构成了一个卓然而立的完整的智者形象。今天,这样的思想家太值得我们敬重了。
作者:李 平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朱自奋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