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就结果而论,缺少的是“学术声誉”;就过程而言,缺乏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氛围与校园文化。
今年我去荷兰特文特大学(UniversityofTwente)访学一段时间,主要目的是对特文特大学是荷兰三大顶尖理工大学联盟3TU 和欧洲创新型大学联盟成员之一,属于在世界大学排名 中名列前茅的“世界一流大学”。
而我访学之际,也正是国内“双一流”建设如火如荼之时。于是,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引发我的思考:特文特大学作为世界一流大学,有何独特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边吃午餐边讨论,在这里是一种生活方式
3月的荷兰依旧春寒料峭,寒风裹挟着雨雪成为这方天地的独特景观。我所在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CHEPS) 的团队要求我每天早上8点到工作室,于是乎,习惯了迟睡迟起的我每天很早就如大多数荷兰人一样,骑着自行车赶往校园。顶着寒风冷雨骑车到工作室似乎很艰苦,但这种艰苦很快被校园里浓浓的工作氛围冲得云淡风轻。
每天早上骑车穿过校园的时候,天刚蒙蒙亮,但透过荷兰特有的阔大的落地窗,我已经看见许多办公室都亮着灯光,灯光下是埋首工作的人们。当我到达自己的工作室的时候,其他CHEPS 团队的工作室大多都已灯火通明。午餐时间,CHEPS的教授们三三两两相约一起前往学校餐厅。大家的午餐都非常简单,奶酪夹面包,外带一碗汤或饮料。并且,午餐时大家会在一起边吃边聊工作中的问题或学术研究动态。换句话说,简单的午餐演变成每日午餐例会。
后来我注意到,特文特大学的学术研讨会 (Seminar) 基本都是安排在午餐时间,大家边吃边讨论。还有的教授午餐时间仍在工作室忙碌着,一杯咖啡或一碗速溶汤端在电脑前,边啃面包、边工作。我问起原因,对方常常回答的是,“要赶时间,因为下午有个会”,或者是因为“要赶一篇文章、赶一个项目”,诸如此类。
记得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说过:“古往今来,能成就事业,对人类有作为的,无一不是脚踏实地攀登的结果。”对于科研工作而言更是如此,相信大家对“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一表述都耳熟能详。不过,在特文特大学,上述表述成为实实在在的每日生活样态。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大家每天看起来都意气风发,丝毫不见苦和累之态。
高效工作,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严格自律
当我向特文特大学的学术同行感慨他们的勤奋努力时,对方哈哈笑着调侃道:“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说明我们效率不高。”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特文特大学的学者们给我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恰恰是他们的“效率”!
这种效率,首先表现为近乎精确的工作日程安排,以更好地利用时间。我抵达荷兰之前,合作教授Don(丹) 即约定了接我的时间与地点。Don约在Almelo(阿尔默洛镇) 的小站接我,他给出的原因是,这个小站人少,我们不会找不到对方,而且这个站距离他家最近,也最方便到特文特大学。
按约定地点与时间接到我之后,在去学校的路上,Don 即与我讨论当天的日程安排以及接下来的研究计划。我表示凌晨方抵达,需要休整。出乎意料之外的是,Don只给了我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事先订好的校园旅店休整,然后就带我熟悉校园环境、逐一认识同事,并参加了午餐学术研讨会。当Don注意到,我这样一个外国人,读起荷兰同行的名字很拗口时,当即让秘书打出CHEPS所有人员的名单,逐一教我如何读这些同行的名字,直到我准确熟练地说出来为止。是的,这是我到特文特大学的第一天,一切准备工作都安排就绪。第二天早上8点,我已经准时到自己的工作室开始工作了,并且可以与CHEPS同行们像“老朋友”一样相处了。
此外,荷兰教授们的效率也表现在工作环节中迅捷的反馈。记得我就“欧洲创新体系与大学的作用”这一专题对M.W.A博士进行了访谈。访谈结束之后,每当就访谈内容需要澄清疑问或补充材料等等,我只要发邮件给M.W.A博士,他都迅速作出回应,从没有拖沓过。在与Don探讨我们的研究课题时,他说会给我一些书和资料作参考。再次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个英文中典型的“将来时”表达,在现实中却是“迅速”或“即刻”。因为讨论一结束,他就直接带我到他工作室拿书了。等我回到自己的工作室,他提供的其他英文资料已发到我的邮箱了。
在以往的高等教育研究中,每讲到大学,尤其是老牌的、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我从书本中获得最多的感知是,大学是具有惰性的,教授们的生活是悠哉乐哉、自由闲暇的———因为只有这样,才会出思想。可见“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荷兰之行使我对大学有了新的认识。
“效率”这一过去屡屡与严苛的体制联系在一起、似乎和大学毫不搭界的词从此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是的,就有形制度而言,特文特大学的教授们享有学术自由,但面对自由,他们是如此自律,他们惜时如金、井然有序地行进在学术之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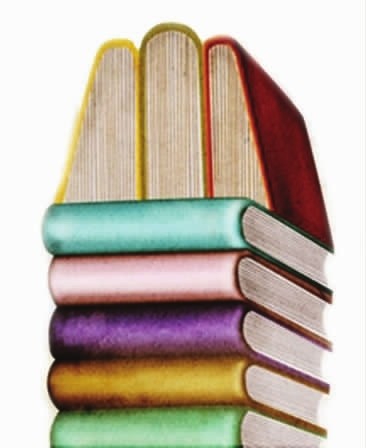
学术结盟是形成“学术共同体”,而非“利益共同体”
在国内,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是“文人相轻”。所谓团队,也常常是导师与自己的研究生而已,这种导师与研究生组成的团队一不留神,即演变成饱受诟病的“裙带关系”。
在欧洲,讲到其学术体制,人们常常喜闻乐道的是“教授讲座制”,教授是某一学科 (专业) 的权威和负责人。我国在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大力推行“学科带头人”制度,似乎学术的发展必须得有一位一言九鼎的“学术大腕”来牵头,但在实践中,学科带头人制度却出现了异化,出现了把持学术界的“学阀”“学霸”现象。
为何“橘过淮则为枳”? 这一疑问通过我对特文特大学CHEPS 日常运作的观察得到了解答。这里的学术队伍少而精,学术队伍之间的研究既有独立,又有交叉。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研究方向并不是完全隔离的,这为彼此的科研合作奠定了基础。他们围绕研究方向,形成了许多研究项目,这些项目既有来自本校和本市企业的,也有来自欧盟和邻国的 (德国、英国居多)。通过研究项目形成了一支支研究团队,并以项目为单位进行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
在CHEPS,项目负责人成为项目团队当然的负责人和学术交流活动的组织者,但这里并没有出现“一超独大”的问题。在实际学术活动中,我亲眼目睹的是“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博士生,只要说的有道理,白发苍苍的资深学术大碗也会认真采纳,衷心感谢。并且,因为大家彼此一起做各种项目,在长期的研究合作中形成了很好的团队精神。
CHEPS成员在日常交往中热情友好,在科研活动中互相研讨,科研工作不分彼此,大家群策群力。我初到这里时,CHEPS的成员逐一在适当的时候到我的工作室与我交流,他们的开场白不约而同的是:“IamDon’sfriend”(我是Don的朋友)。这让我非常惊讶,不明白不苟言笑的Don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朋友。Don对此的回答是:我有一个很好的团队。
事实也确实如此,Don是我的合作教授,但在我完成的CHEPS要求的学术博文出现问题时,不仅Don会给我发来许多有关学术博文写作方法的资料,而且其他同行也利用午间聚餐时,与我一起研讨,并发来相关博文供我揣摩,期间还不断进行鼓励。
在CHEPS的亲身经历使我体会到,“教授讲座制”也好,“学科带头人”也罢,都不过是一种制度的形态,制度是经由人而活化的,大学的学术发展归根结底是学术成员对科研的共同热爱、对学术的共同敬重。以此为前提,倘若真有“结盟”,也是大家对学术的结盟,形成的是“学术共同体”,而不是“利益共同体”。
大学何来“行政权与学术权之争”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关于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争论以及“去行政化”的呼声不绝于耳。为了增强学术力量,加强学术委员会建设已经写入我国教育政策法规。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为何成为了对立的紧张关系? 在CHEPS是否存在政权管理与学术活动的矛盾问题? 带着这一问题,我访谈了CHEPS中心主任Hans(汉斯)。
当我问起他是如何招聘到这么优秀的成员、形成这么好的学术氛围时,他的回答让我豁然开朗———“是他们选择我,而不是我选择他们”。在Hans看来,CHEPS的发展依赖这里的全体成员,尤其依赖于学术的影响力,如果学术不能发展,学校也就不会允许这个中心存在了。同样,一个大学的存在,也在于这所大学的学术发展与影响力。因此,在大学很难说管理,而就领导力而言,那就是他要想方设法让他的团队成员“能够幸福快乐地工作”。
Hans的话通过CHEPS的行政人员 的行为得到了印证。从得到CHEPS的邀请函那天起,一直到访学结束,我得到了CHEPS办公室秘书Mirjam(米立安) 全程细心周到的服务,她包揽了订房、订票、扫描、复印、通知学术活动等一切事务性的工作,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做好学术研究。期间有一件小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有次Don到我工作室讨论一个学术问题,我当时需要用电子邮箱,不知怎么回事,网速很慢,我就说稍后再发吧。没想到Don刚离开,Mirjam就来到我工作室了解网络出了什么问题。她不仅迅速解决问题,而且强调道:“任何时候,只要你需要帮助,只管告诉我,这是我的工作。”
是的,当大学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学术而运作的,大学崇尚的是学术,而不是权力的时候,学者是以学术工作为志趣,而不是把学术作为“稻粱谋”或权力的敲门砖;行政工作只是分工不同,但着眼点仍是学术——让学者更好地做好学术工作,管理因而实实在在地成为“服务”,即服务于学术工作。
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就结果而论,缺少的是“学术声誉”,即是否是世界一流大学有待中国公众广泛认可,有待世界同行普通认同。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就过程而言,缺乏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氛围和校园文化。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学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需要大家共同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一代一代延续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相信有一天,世界一流大学不再是中国大学为之努力的外在目标,而是自然而然的内在结果。总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其背后是长期积淀和努力奋发。(作者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