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一直从事中日比较研究的青年军旅作家王龙,最近正在创作新书《刺刀书写的谎言》,这也是国内首部揭露日本侵华作家真相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在王龙看来,“笔部队”如同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刺刀”,说他们在另一个侵华战场进行了一场不见硝烟的“文化制脑战”,亦不为过。
王龙对“笔部队”的关注,缘起于央视的一则报道。2013年的最后一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专程去电影院观看了一部正在日本热映的电影《永远的零》。这部电影主要表现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神风特攻队”如何实施自杀式攻击的故事,安倍看后给予此片高度评价,并表示“十分感动”。后来王龙得知,《永远的零》是日本的一部畅销小说,上架后狂销300万本,漫画版本也热销400万本,拍成电影上映后一举跃升到日本圣诞新年档票房榜首。
《永远的零》并非孤案。在日本,诸多宣扬军国主义战争狂热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都备受欢迎,在市场上“大获成功”。王龙发现,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命运,甚至局部场面的描写,不但看似“细节真实”,还很有蛊惑人心的作用。作者们有意回避了战争正义或邪恶的因果关系,更逃避了对灾难原因的追问,却通过这种隐蔽的“偷梁换柱”,“把反思变成了颂歌,把战犯变成了英雄,把侵略者置换成了‘受害者’”。
“今天,我们设立‘国家公祭日’,就是为了要牢记法西斯的侵略之害,更不能容忍日本极右势力混淆视听,篡改历史。”王龙说。他决心通过当年日本侵华作家这个独特群体,剥掉极右势力的带血面纱,让世人对这样的歌颂军国主义刺刀的“笔部队”抱有警惕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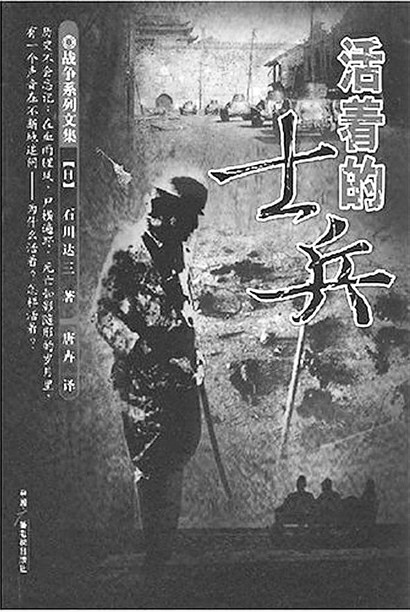
▲石川达三所著《活着的士兵》以报告文学形式,真实地向人们展示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腥风血雨的场面。
被战争异化的日本作家
“战场上虽然有残酷的情景,但也有着美好的场面和丰富的生活,令人难忘。我经过一个村落时,看见一支部队捉住了抗战的支那兵,听到了这样的对话。‘我真想用火烧死他!’‘混蛋!日本男人的做法是一刀砍了他!要不就一枪结果了他!’‘不,俺一想起那些家伙死在田家镇的那模样就恶心,就难受。’‘也罢,一刀砍了他吧!’于是,被俘虏的中国兵就在堂堂的一刀之下,毫无痛苦地一下子被结果了性命。我听了他们的话,非常理解。我不觉得那种事有什么残酷。”
这段令人不寒而栗的描写,出自一位柔弱的日本女作家。行军途中,她还亲眼目睹了一名看上去只有十六七岁的少年兵的尸体,当看到少年瘦弱的身躯被又肥又大的军装包裹住时,她没有丝毫罪恶感,甚至能够十分平静地写道:“实话讲,即便连一瞬间的寂静感情也没有。”
写下这一切的女作家叫林芙美子,被誉为侵华日军“陆军班头号功臣”。她曾无比仰慕鲁迅先生,赞叹过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在此刻,她的人性却被残酷的战争异化了。
侵华期间,一大批像林芙美子这样的日本作家,开赴中国前线进行“笔征”。他们有的直接从军入伍,左手拿枪、右手拿笔,一边亲自参与屠杀,一边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他们明火执仗地鼓吹对华侵略,煽动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大书特书“皇军”的“忠勇可爱”,污蔑丑化中国人民的抵抗运动……他们被称为侵华战争中的“笔部队”,鲜为人知,却影响巨大。
1938年8月23日,在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菊池宽的带领下,12名作家参加了日本内阁情报部召开的恳谈会。内阁召开这个会议,是想动员作家们奔赴中国前线采访。军部原本对会议的结果心中没底,但令他们大感意外的是,作家们在会议上摩拳擦掌,纷纷请战,强烈要求参加这支“光荣”的“笔部队”。
作为唯一的女作家,林芙美子参加了陆军部的“报道班”。出发前,她和其他从军作家一样,从军部领到了高额的津贴、军服、军刀、手枪、皮裹腿等,仿佛是一批出征的将军。林芙美子深感此次责任重大,惟有竭尽全力才能回报这份“知遇之恩”:“决不能给部队造成任何麻烦,而要比他们做得更好。”
事实上,参军前,林芙美子就已感到自己和战争息息相关。1937年11月,她的丈夫手塚绿敏接到“应召通知”,入伍成为了一名卫生兵。离别前夜,林芙美子在深夜的灯光下为丈夫收拾行装,也拿起针线,和其他日本妻子一样绣缝“千人针”。她的眼里,战争不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较量,更无关是非正义,更像是一位妻子保卫自己幸福家庭的责任。她随“笔部队”前往中国的时候,《朝日新闻》刊出了她和丈夫共赴战场的事迹,在日本国内一时被传为“佳话”。

▲在侵华战争中使用毒气的日本军队。
充满矛盾、分裂的“异人种”
作为“社会的良心”,一向被认为具有独立思想和自省精神的日本知识分子,却在侵华战争期间一边倒地沦为了军国主义的御用工具。个中原因,不得不令人深思。
日本著名作家石达川三,曾被认为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深谙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也在一开始就决心摆脱日本军国当局的政治指挥棒,一心从文学艺术的本质出发,想要酝酿创作更为深刻的战争小说。为此,他在南京“逗留期间,跟部队长的寒暄只有一两次,其余时间都一直住在下士官和士兵那里,和他们一同逛街、喝酒,到处看战斗遗迹,听他们讲从上海登陆以来的战斗经历。”在随后创作的长篇小说《活着的士兵》中,石川达三独具匠心地表现了一群日本士兵内心的斗争纠葛,展现了他们人性畸变的复杂过程。
然而,《活着的士兵》发表后,石达川三被日本当局迅速判处4个月有期徒刑,缓期3年执行。这是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发生的第一起、也是仅有的一起作家惹下的“笔祸事件”,在当时的日本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从此以后,像《活着的士兵》这样真实反映日军侵略行为的作品,在文坛基本绝迹了。
石川达三被判刑后,感到了一种“成为罪人的屈辱”。他很快就得到了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变成了粉饰战争的工匠。1938年,他前往中国采访武汉会战,在他创作的《武汉作战》里,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兵一个也不见了,石川达三把战争带来的所有灾难,统统推到了中国军队一边。
在王龙看来,石川达三从未具有真正的“反战精神”。在他战后创作的《风中芦苇》中,石川达三通过主人公苇泽悠平之口,阐述了自己的创作目的:“你们(日本当局——编者注)是把绳索套在国民的脖子上拉着他们走。我们是想做内在的工作,使国民的思想朝着一个方向走。”
“石川达三描写战场的真实,并非为了谴责日军的侵略行为,而是要让国民知晓,战场上的士兵是‘人’,那些烧杀抢掠的野蛮行径,不过是战争驱使下人的‘生物本能’,既然是‘本能’,那就是可以理解的战场行为。”王龙说。
在“笔部队”中,像石川达三这样精神分裂变异的“异人种”不在少数。许多左翼作家刚开始都坚决反对天皇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但在1933年左右被捕入狱后,几乎全都集体“转向”,宣布效忠于日本军国当局。女作家牛岛春子便是其中的典型,她的一生充满了多重人格:从坚定的共产党员,到屈服于法西斯政权的变节者;从在日本受到思想迫害无处安身的政治犯,到在“满洲国”获得“浴火重生”机会的名作家;从经受不住诱惑为侵略扩张高唱赞歌,到战后矛盾纠结的痛苦反省……牛岛春子和许多日本侵华作家一样,始终摆脱不了“异人种”的精神分裂。
牛岛春子天资平平,但在日本当局大肆倡导“文学报国”的伪满洲国,她可谓“生正逢时”,特殊的战时环境竟使她一举获得了第12回芥川奖的“候补”提名,一下从折戟沉沙的革命者变成一炮而红的女作家。尝到了甜头的牛岛春子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这一段经历,也使许多日本侵华作家的精神世界出现了“黑洞”。战后,军国主义的迷狂和幻灭,使他们陷入难以自拔的失落忧郁。对战争责任至死不悟的“集体失忆”,又让他们在痛苦迷惘中难以找到真正的精神出路。被称为“侵华文学第一人”的火野苇平,在中国战场曾受到过日军山呼海啸般的拥戴,日本战败后却落得“门前冷落鞍马稀”的下场。那以后,火野的创作每况愈下,影响力也大不如前。1960年1月,他服下100片安眠药自杀了,并留下遗书:“我要死了,也许和芥川龙之介不同,也许是某种不安。对不起,请原谅,永别了!”火野的悲剧下场,也是侵华作家们无法安妥灵魂的典型。

▲日军在上海屠杀中国人。
反思,在良知和勇气中(附照片)
——访军旅作家王龙

▲军旅作家王龙
文汇报:“笔部队”所创作的这些作品,对当时普通的日本民众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龙:“笔部队”带给日本国民的误导和煽动是巨大的,更进一步掀起了战争狂热情绪。火野苇平《士兵三部曲》发表后广受欢迎的程度,简直令人瞠目结舌。仅其中的《麦与士兵》就发行了120万册,成为红极一时的畅销书。《士兵三部曲》单行本出版后不断重印,销量达到300万册,竟然使日本一家濒临倒闭的出版商一下子起死回生。
此后,这部小说的巨大影响波及到了电影界。松竹电影制片厂为了“跟上形势”,不甘落后地发表“爆炸性声明”,宣布今后将停止拍摄“以恋爱为中心的”电影,而改拍“符合国策的、健全明朗的电影”,以“顺应国民精神总动员体制”。为此,他们决定将《麦与士兵》搬上银幕,并远赴上海和南京拍摄外景。不久,《士兵三部曲》中的《麦与士兵》和《土与士兵》在日本公开上映,影响更大,几乎人尽皆知。当时日本的城镇乡野都流行一首和歌:“《土与士兵》已看完,归途炮声绕耳畔”。
文汇报:日本战败后,在盟军惩办负有战争责任的作家时,一些“笔部队”作家比如石川达三,却因其作品具有“反战”色彩而免于起诉。那么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作家们又是以怎样的态度描写这场侵略战争的呢?
王龙:日本战败投降后,像火野这样在侵华期间异常活跃的作家,对自己在侵华战争中的责任和罪过都拒不认错,三缄其口,讳莫如深。
与之相对的倒是日本文坛非常明显的“被害者意识”。著名学者王向远先生认为,与其说战后许多日本作家是反战的,不如说是“反对战败”。他们抱怨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被打败了的战争”。日本战后派文学极力强调和描写的是,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本身带来了巨大身心创伤,具有强烈的自怜性,却非常缺少对被侵略国人民的理解与反省。整体显得诉苦有余,而反省不足。
对于这种片面强调日本人“战争伤口”的现象,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晚年有更深刻的理解,他在著作《我在暧昧的日本》里就说:
“现代日本无论作为国家或是个人的现状,都孕育着双重性……支撑着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义和放弃战争的誓言,这也是新的日本人最根本的道德观念。然而,蕴涵着这种道德观念的个人和社会,却并不是纯洁和清白的。”
文汇报:同样作为发动二战的国家,德国和日本这两国的作家对战争的态度,具体有何不同?
王龙:德、日两国作家对于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态度,可谓有着天壤之别。在战争期间,日本除了鹿地亘夫妇等极少数人流亡到中国之外,其他的作家根本没有考虑离开日本,而是几乎全部加入了日本法西斯主义政权的附属机构“日本文学报国会”,总人数达4000之多。而德国几乎所有的优秀作家都耻于和希特勒为伍,除了80多名表示效忠法西斯政权的作家文艺家之外,先后共有近30万作家艺术家逃离了德国,并在海外创作起了“流亡文学”。而留在国内的德国作家也没有向法西斯缴械投降,更没有像日本左翼作家那样集体“转向”,为军国主义政府充当侵略者的马前卒,他们宁愿把作品锁在书桌中不发表,也不和希特勒同流合污,因此产生了德国战后才发表的“抽屉文学”。
日本的反战也完全不同于德国的反战。德国反对的是战争本身,而日本,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反对日本没有赢得胜利的战争。战后,德国人对战争的反思极其深刻,同时刻意回避了德国人在自己发动的战争中也承受了苦难这一禁忌题材。日本作家则相反,他们更乐于描写战争给日本国民所带来的灾难,表现日本战后艰难困苦的生活。

▲1938年8月,日本内阁情报部派遣了22名从军作家,称其为远征中国内地的“笔部队”。图为在中国的从军作家(左起)中谷孝雄、片冈铁兵、泷井孝作。
文汇报:在您看来,日本侵华作家的这种整体迷狂,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王龙:“笔部队”的集体盲从,与日本的民族心理相关。日本人有句名谚:“没有亲戚死不了,没有邻居活不成”。作为一个山脉纵横、灾害频繁的狭小岛国,只有团结协作才能战胜自然灾害,得以生存。在日本的集团主义价值观中,只有将自己全部融化到集团中,置身于同一方向的时代潮流,才能找到自我的位置和价值。如果一个日本人被认为是“与众不同”的,那是他最为恐怖和羞耻的事情。
尽管当时有少数日本作家、记者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感到震惊、羞愧与自责,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流露出一些同情,也曾想把他们亲见亲闻的南京大屠杀记录下来,写到报道或通讯中去,但最终,这些良知尚存的记者面对日本当局严厉的新闻管制与残酷的政治迫害,无一不望而却步。日本文人软弱动摇的弱点暴露无遗。连日本历史学家秦郁彦也忍不住感叹道:在日本当局制造的这样严酷的氛围内,“向这一禁忌挑战的记者一个也没有,不免让人感到寂寞”。
文汇报:如果说战时在集体无意识的鼓噪下,人们很容易迷失自己的心灵,那么日本文坛在战后是否有过深入的反思?
王龙:被称为“头号文化战犯”的火野苇平在请求恢复公职的申请书上,曾振振有辞地写下这样一段话:“对于战争结束之后的反思,我很愚钝;对于战争的真正意义,完全无知。我只知道,不管什么意义上的战争,既然战争已经开始,既然祖国危在旦夕,我作为日本人,就必须以身殉国。只要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家庭期待着我,就有一种揪心的痛楚。我想,在祖国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我必须献出一份微薄之力。如果有人说,我的爱国热情是错误的,我也无话可说。”
火野苇平的顽固态度很有代表性。即使对战争和历史有所反省的作家,心理仍显得复杂曲折。在女作家牛岛春子看来,那些热情宣扬“王道乐土”精神,并最终埋尸“满洲国”的众多日本年轻人,和自己一样从内心热爱着那片土地和人民,他们与“侵略主义”毫无瓜葛。她不会理解,对于被殖民的中国民众而言,伪满洲国是水深火热的地狱。
在没有认清侵略历史的情况下,日本文学界对于二战的反思自然也就不可能和德国比肩。而天皇制的保留一方面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体系清理得不够彻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日本平民对于二战的混乱认识,加重了对侵略历史的模糊与淡化。
当代日本文学对于侵略战争普遍选择了“集体失忆”。不仅真心忏悔的侵华文学作家寥寥无几,甚至不乏像林房雄这种战时为侵略战争鼓噪加油,战后依然坚持反动军国主义立场的作家。作为“笔部队”的成员,林房雄战后受到了处分,但他却不思改悔,还炮制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全面地为日本的“大东亚战争”辩护。这样的书居然在日本长期成为畅销书,可见肃清军国主义余毒,是何等任重道远。
文汇报:日本的侵华文学对我们今天的抗战文学艺术创作有怎样的启示?我们如何打赢下一场“制脑权”战争?
王龙:昨天的历史,往往映照着今天的现实。这些年,同样作为二战中深受法西斯之害的国家,我们是否也曾扪心自问过,中国产生了多少影响巨大的作品,能够让那些逃避战争罪责的日本人受到震撼、心服口服呢?
相反,我们眼下的许多“抗日神剧”:花针、化骨绵掌、太极神功轮番出场,取敌人首级如探囊取物,“八路军”徒手将敌人撕成了两半,一个小孩子可以用弹弓消灭鬼子……抗日“神剧”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场“暴力拆迁”,用回避苦难的娱乐打闹取代了严肃深刻的痛苦反思。
我们必须反思梳理中国战争文学创作的成败得失,作家要增强艺术良知和勇气,赋予我们的战争文学作品全新的东方内涵和丰富的人文情感,提升中国战争文学的内在张力和外在传播力,力争在更大的坐标上讲述中华民族的抗日历史。无论中国还是日本的作家,都应该好好品味1949年福克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讲话:“一位作家在他的工作里除了心底古老的真理之外,不允许任何别的东西有容身之地。没有这古老的普遍真理,任何小说都只能昙花一现,不会成功;这些真理就是爱情、荣誉、怜悯、自尊、同情与牺牲等感情。若是他做不到这样,他的气力终归白费。因为他不是写爱情而是写情欲,他写的失败是没有人失去可贵东西的失败,他写的胜利是没有希望或同情的胜利。他不是为遍地白骨而悲伤,所以留不下深刻的痕迹……”
作者:张小叶
编辑:赵征南
责任编辑:朱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