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
★学术就是学术,做学问终究是做学问,科技的发展可能为之提供工具、提升效率,但终究代替不了做学问本身。
去年岁末去沪参加复旦中文学科百年庆典活动时,陈尚君先生赐我一本他的新作《星垂平野阔》。坦率地说,这位现任唐代文学会会长、且尤以致力于唐一代文史基本文献之甄别、研究与建设而驰名的著名学者所涉之研究范围于本人而言是十分陌生的。按常理,面对这些自己完全外行的领域,我的确没有为之写下点什么文字的底气。
然而,本人现在的确就是在不按常理出牌。不仅认真地拜读了全书,而且还不知天高地厚地要围绕这本书写下这则拙文。如此反常,既有出自“私情”的一面,更是因为有些肤浅的感慨不吐不快。
所谓“私情”,不过是尚君先生研究生毕业后的首个正式工作岗位就是我们大学本科时期后半程的指导员,并因此而结下了我们之间37年的师生情。《星垂平野阔》既系拜老师所赐,为学生者没有不读之理;至于所谓“有些肤浅的感慨”则且看下文慢慢道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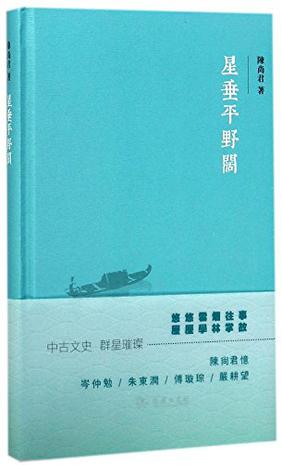
陈尚君 著
商务印书馆
2017.8
作为1976年后首批经过考试入学、且又是师从著名大学者朱东润先生的尚君师刚出任我们班的指导员时,头上还是颇有些光环效应的。但于我而言,这种光环很快就消失殆尽了,其原因就在于这位以唐宋文学研究为专业的青年老师在我们面前实在太爱“炫耀”自己的考据功了,每周到班上来,没几句话就开始喜气洋洋地絮叨自己又从哪里哪里发现了一首被散轶或被错认的唐诗,从某处某处又查到了一条张三或李四某年某年身在何处何处的佐证。
要知道,在那个刚刚开放不久百废待兴的年代,对我这个涉世不深兴趣又多在当代的青年人而言,更有魅力者无疑是那些扑面而来应接不暇的各种“新”思潮“新”学说,而面对如此“炫耀”“呆板”的考据本事实在只能留下一个“迂”的印象。
今天回过头来看,正是这种专注的“迂”成就了尚君师的学术成就,尚君师之可贵不仅恰在于这种专注的“迂”,更在于他的“迂而不腐”。随着时间的推移,尚君师之“迂”更是修成了集专注、拙朴、开放与融合为一体的混合体。
为此,我曾私下里专门请教过尚君师的同行,这位同行真诚地告诉我:尚君师之治学不仅以扎实的史料考据实证为基础,更可贵的还在于一是文史兼修,不为学科所囿;二是新旧并重,不限于传世文献,不盲目追逐新见资料。就此,我不妨冒昧地将其概括成一句:尚君师治学方法拙朴、思维现代、视野国际。
还是回到这本《星垂平野阔》。这部论文集以写尚君师之导师朱东润先生与师祖等几篇为上篇,其他几篇有关前辈学者之文字为下篇,另有几篇书评随笔为附录。在这20余篇论文中,所涉学者及研究范围各不相同,但一一研读下来,不难发现尚君师治学之上述特征则是不约而同地呈现在不同篇什之中。
▲陈尚君在课堂上
以《朱东润先生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一文为例,全文共分九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以时间为序概述了朱先生自己保存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及手稿六个版本之基本情况,第二至第八部分分述以上六个版本各自的基本状况及相互间异同,第九部分则在以上分述比较的基础上概括地提出了四点可供讨论的话题。如果将此文与收入本论文集中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校补本)整理说明》《修补战火烧残的学术》和《<大纲>校补本的新内容》等与此内容相关的三篇论文联起来读,当更可见出尚君师治学之特点,即便是介绍自己先生的一部旧作,依然是一丝不苟不厌其烦地将诸个版本逐一比较后再进行陈述,而读者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清晰地了解到朱先生这部著述成书过程所受到的主观的客观的诸因素之影响。
仅此一例或许尚不足以典型地反映尚君师的治学之道,但说白了,这就是学问,这才是做学问;在这背后,则是方法的拙朴、思维的现代和视野的国际。说到这些,当下不少人或许更青睐于思维的现代和视野的国际,这当然并不为过,但殊不知的是:方法的拙朴更是治学的基础。于做学问而言,如果没有那一点执著的“迂”劲儿,就谈不上“做”,更遑论有什么真正的学问可言。遗憾的是,现如今,有如此“迂”劲儿的执著者日渐稀有,而企望走捷径登龙门者渐多,这才是令人忧虑的。
“板凳硬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曾经是一代又一代学人所追求的刻苦研读严谨治学的一种境界,令人忧虑的是这样一种境界现如今在各种急功近利的诱惑之下正在日渐被消解、被侵蚀。而在当下这个互联网时代,又有种种似是而非的所谓“知识服务”之说披着高科技的外衣同样在为瓦解严谨的治学之道而助力。
坦率地说:每当看到是个人都可以在那里煞有介事地嚷嚷着通过“碎片化”“挖掘知识点”“进行知识标引”“提供知识服务”一类的时髦词儿时,愚钝如我者则不免暗自嘀咕:这活儿难道是谁都能干的吗?没有足够的相关学科专业背景,这“碎片化”从何入手?这“知识点”又从何发现?那“标引”该落在何处?那“服务”又如何提供?

就众声喧哗中所罗列的那些所谓成功的“知识服务”产品而言,究竟有多少真的是互联网时代、数据化时代的“知识服务”呢?无非是读读屏听听文再包装上所谓“大数据”的华丽外衣来个自诩的“精准推送”而已。
需要声明的是:我虽本非做学问者,但也绝不至于“迂”到一味反对“碎片化”“挖掘知识点”“进行知识标引”“提供知识服务”之类的新鲜事儿。我所主张是所谓“挖掘知识点”“进行知识标引”“提供知识服务”既不是谁都可以干的活儿,也不是单一的所谓高科技、互联网和数据化所能承担,“专业人做专业事”这个颠扑不破的理儿在这里同样适用,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个“专业人”在当下更可能不再是某个单一的个体而是复合体;我要强调的是所谓“提供知识服务”固然有做学问的成分,但绝对代替不了做学问本身,如果服务得专业,它确能为扎实做学问者提供某种工具、提升一定效率,如此而已。
再回到尚君师的这本《星垂平野阔》,尽管这部论文集可能还算不上顶级的做学问,但即便如此,也绝不是所谓“知识服务”所能担当。学术就是学术,做学问终究是做学问,科技的发展可能为之提供工具、提升效率,但终究代替不了做学问本身。

▲本文作者潘凯雄
本人之所以不按常理出牌,就《星垂平野阔》写下以上这些肤浅的感慨,无非只是在不合时宜地呐喊一声:
真学问是这样做出来的!
文:潘凯雄(著名文艺评论家)
制作编辑:许旸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