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点提要
在欧美大学的文学系, “非洲文学”通常隶属于英语系或法语系。非洲当下最有影响力的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昂戈,曾撰文谴责19世纪欧洲人的到来“肢解了非洲大陆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为了抗衡“用欧洲语言定义自我”的非洲文学,他渴望看到“用非洲语言写作的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他自身也致力于用家乡方言基库尤语写作。然而耐人寻味的是,非洲大陆上、尤其撒哈拉以南的国家拥有数量众多的语言,如果一个作家选择本土语言来表达,意味着他的作品只能传达给很少的受众。而选择英语或法语写作的非洲作家,相对能接触到国内外的更大读者群,作家的声音被带到更远的远方和更多人中间。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出生在坦桑尼亚的桑吉巴尔岛,在伦敦完成学业,从1987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他用英语写作。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是沃莱·索因卡,他是尼日利亚人,毕业于英国利兹大学英语系,他在尼日利亚用英语从事戏剧创作,被称为“非洲的莎士比亚”。同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弗兹,是阿拉伯语文学的代表人物。莱奥波德·塞达·桑戈尔是非洲现代诗歌的奠基人,他是用法语写作的。近年始终是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之一、也是非洲当下最有影响力的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昂戈,大学就读于英语系,以英语写作进入东非文学界,但是,当他以文学新人的身份参与“非洲作家大会”、却发现斯瓦西里语、约鲁巴语、阿姆哈拉语等大量非洲当地语言的作品被排除在外时,出于抗争意识,他决定转向用肯尼亚老家方言基库尤语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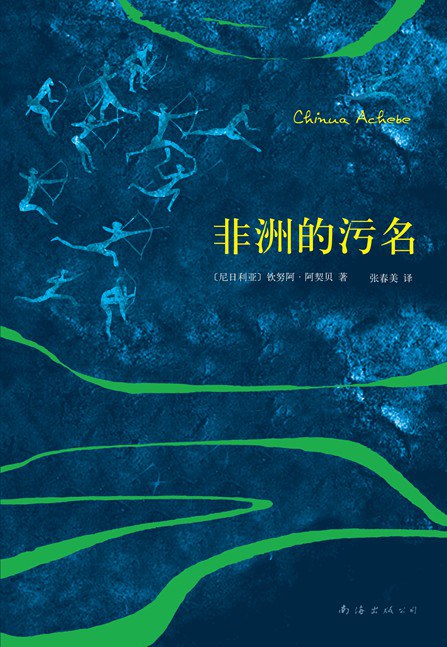
阿契贝《非洲的污名》,南海出版社
语言,是了解和讨论“非洲文学”时一个无法回避的复杂议题。恩古吉·提昂戈在1980年代中期发表过一篇措辞尖锐的文章,谴责欧洲列强“肢解了非洲大陆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导致“非洲文学用欧洲语言定义自我”,在这篇文章中,他甚至对阿契贝和桑戈尔发出质疑。提昂戈呼唤“用非洲语言写作的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固然是渴望文化自信的表达,但有必要意识到,非洲大陆上的多样化民族语言长久只有口语的形式,8世纪伊斯兰移民带去阿拉伯语,19世纪的欧洲人输入英法葡语系,外来的文字系统让当地的民族语言发展出书写形态,甚至,外来语言成为不同部族之间的通用语。仅仅透过“语言”窥视口,我们就可以领教到非洲的作者和他们的写作怎样卷入历史、政治、社会变革的骇浪中。
黑色大陆的文学寻根
出生在加勒比海地区马提尼克岛的非裔作家弗朗茨·法农在《论民族文化》一文中提到,为了回击种族主义者的嘲笑,非洲的知识分子们爆发了文化寻根的热情,来证明这块黑色的大陆曾有过美丽绚烂的时代——“他们怀着巨大的愉悦发现,他们的历史都是尊严、荣耀和庄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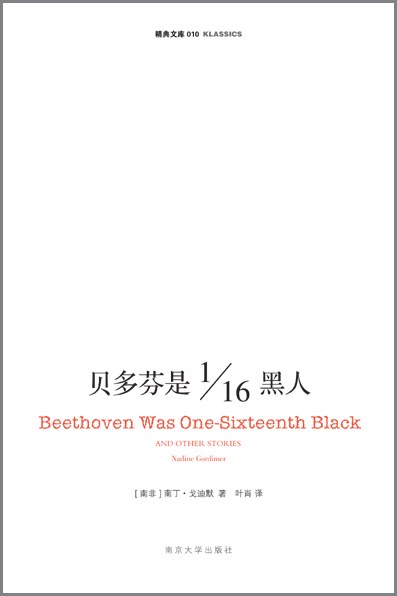
戈迪默《贝多芬是1/16黑人》,南京大学出版社
早在公元前,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闪米特移民越过红海,来到埃塞俄比亚西北部的察纳湖附近定居,移民带来塞巴语字母系统,和原住民的语言融合。在公元4世纪,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会成立,僧侣们用当地语言盖兹语翻译福音书,从希腊文译入包括《圣经》在内的宗教典籍,并创作一种叫作“祁奈”的赞美诗,这是盖兹语最重要的文学成就。公元10世纪以后,衰败的阿克苏姆王朝从南方的埃塞俄比亚高原迁移到北部的阿姆哈拉地区,从此,阿姆哈拉语流通,盖兹语成为非洲的拉丁语,仅用于学术文本。长达400多年的时间里,阿姆哈拉语文学的体裁限于歌颂统治者的战歌和赞美诗。到了19世纪末,埃塞俄比亚皇帝面对欧洲的威胁,意识到要对国家进行全面的现代化变革,包括文学创作,皇帝支持用阿姆哈拉语创作诸如小说和戏剧等欧洲舶来的文学形式。埃塞俄比亚在20世纪上半叶被意大利占领且卷入二战,这对本国文学发展造成毁灭性打击。直到战后,意大利军队战败撤离,阿姆哈拉语文学再度繁荣,其后涌现大量的小说和戏剧。
在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沿岸地区、沿海岛屿,阿拉伯半岛的移民和原住民黑人产生文化交融,这种混杂的文化在当地班图语的基础上掺入阿拉伯语元素,形成特色鲜明的非阿拉伯语言——斯瓦西里语。最早的斯瓦西里语手稿追溯到18世纪,内容以宗教题材的史诗为主,和中东地区的阿拉伯语诗歌集有大量重合。到了19世纪,一个叫穆亚卡的作者写诗声讨阿曼苏丹强加于肯尼亚蒙巴萨地区的宗主权。后世的文学评论家认为,这位穆亚卡把斯瓦西里语诗歌带到民间,开启世俗题材的创作,用文学去记录、回应和评价政治历史事件,书写当代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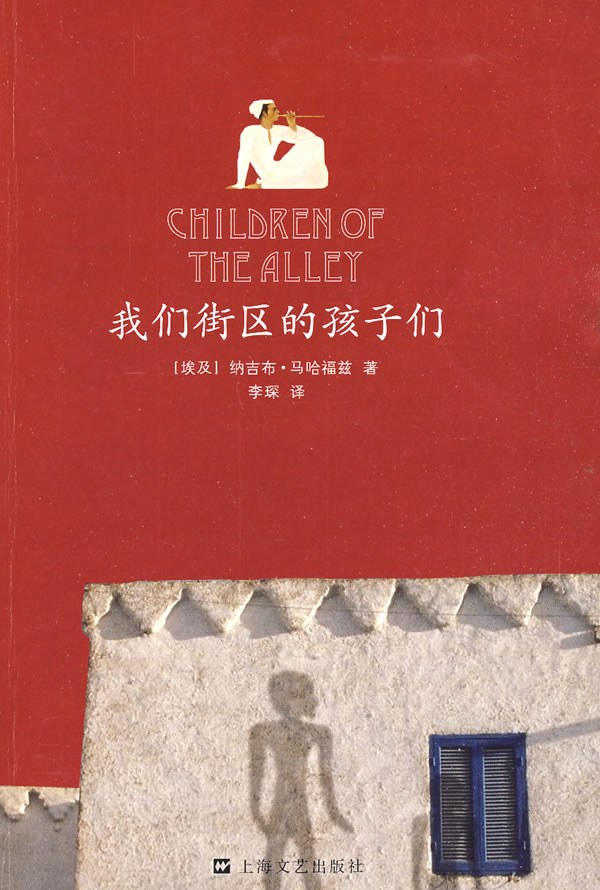
马哈福兹《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上海文艺出版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在英属东非地区推广斯瓦西里语为官方通用语,这种曾经使用阿拉伯语文字系统的语言从此转为使用罗马字母。欧洲的文学样式——尤其小说——也在这个阶段被引入斯瓦西里语。坦桑尼亚独立后,既是政治家也是学者的朱利叶斯·尼雷尔,他用斯瓦西里语翻译了莎剧《朱利乌斯·恺撒》和《威尼斯商人》。在他执政期间,斯瓦西里语成为坦桑尼亚的官方语言,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斯瓦西里语研究中心改造了这门语言,使之适于表达和传播,这激发坦桑尼亚的新生代作家们用斯瓦西里语创作大量探讨时代议题的原创作品。
在西北非,公元8世纪起,陆续有穆斯林迁往撒哈拉以南,到了11世纪晚期,撒哈拉以南的西非大部分黑人皈依伊斯兰教,此后直到18世纪末,阿拉伯语是这一地区书写艺术的唯一媒介。位于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的历史名城廷巴克图在14-16世纪是伊斯兰学术中心,但是1591年摩洛哥人征服廷巴克图之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一蹶不振。18世纪中晚期,从欧洲奔赴当地的神职人员为了在中低社会阶层中传播教义,用民众的语言进行教学和布道,并延伸到摸索本土语言的书面形式,豪萨语从此取代阿拉伯语。直到今天,在豪萨语地区,大部分作家坚守地方语言,《尼日利亚语言》是豪萨语的重要文学刊物。

提安哥《大河西岸》,上海文艺出版社
被欧洲文学推动的阿拉伯叙事
对比东、西非,北非可说是被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塑造的,北非文学是阿拉伯语文学的分支。
阿拉伯-伊斯兰帝国扩张到北非的过程中,阿拉伯语发挥了强大的向心力作用。阿语古典文学的体裁是诗歌,诗歌凝聚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集体记忆,塑造着帝国所到之处民众的身份认同。直到19世纪初,阿拉伯社会面临现代转变,包括重估文化遗产、理解和西方之间渐强的碰撞、建立新的阿拉伯叙事,这些迫使文学表达作出变化。
在阿拉伯历史中,民间故事被排斥在文学传统之外,源自埃及的《一千零一夜》从未在阿拉伯世界取得它在欧洲那样的成功。现代意义的小说和戏剧对于阿语文学来说是全新的,抒情诗传统无法为叙事的发展提供框架,所以近当代阿语小说和戏剧的发展动力来自欧洲文学,这就不奇怪埃及作家马哈弗兹经常被类比狄更斯和左拉。
198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马哈弗兹是北非和整个阿语文学界最重要的当代作家。他的早期作品试图复活古埃及法老时期的历史,这些历史小说实际是针对埃及现代社会的寓言。他的代表作《开罗三部曲》叙述一个开罗家庭几代人的离合,探讨埃及社会的晚近变迁。三部曲有明确的时间背景和清晰的空间意识,每一部以老开罗的街区名字命名,叙事以街区为核心。欧美评论家认为,19世纪的欧洲文学传统对马哈弗兹的影响是直观的,他笔下的开罗就像狄更斯的伦敦或左拉的巴黎。他本人不认同这种评价,而倾向把自己的创作置于更大的传统中,这个传统包括托尔斯泰、契诃夫、莎士比亚和纪德。

桑戈尔《鬣狗和兔子的美丽故事》,塞内加尔新非洲出版社
从历史走向现实的“文化混血儿”
撒哈拉以南国家拥有数量众多的语言,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并不顺畅,流通最广的是外来统治者推广的语言,或外来者的语言。如果一个作家选择本土语言来表达,那么他的作品只能传达给很少的受众。选择英语或法语写作的非洲作家,反而相对能接触到国内外的更大读者群,作家的声音可以被带到更远的远方和更多人中间。在20世纪上半叶,为了唤起非裔的族群认同感,以“非洲共同体”为信念的大量作品,是通过欧洲语言表达的。
当桑戈尔被问“为何以法语写作”时,他回答:“我们是文化混血儿。我们的词语包裹着树和血液的味道,而法语词汇闪耀火光,熊熊火焰照亮我们的黑夜。”桑戈尔以法语写作超现实主义诗歌,他认为这种表达形式所传递的高强度节奏、形象和象征,呈现了非洲人的创造性,把非洲黑人的文化信息传达给外部世界,这是被包装在文雅形式中的抗议。一件欧洲的工具被技艺娴熟的非洲人掌握,这使欧洲社会意识到黑人民族具有同等的人性和尊严?还是进一步陶醉于“非洲精英被欧洲文化同化”?在轰轰烈烈的族群认同运动翻篇后,这个暧昧的争端成为长久嵌在非洲文学机体里的芒刺。
西非法语区的超现实主义诗歌很快被讽刺小说取代。1950年代,非洲国家接连独立,人们变得自信,在变化的时代氛围中,非洲法语作家不再对历史作浪漫化的描述,宣称非洲的村庄比欧洲的城市具有更高尚的道德。在塞内加尔作家乌斯曼·塞姆班的很多短篇小说中,非洲人不比欧洲人坏,可也好不到哪里,人性的局限和荒唐是相似的。
西非英语区作家们的态度要谨慎些,他们避免把欧洲人到来前的历史美化成黄金时代,但仍试图为非洲的过去树立有尊严的形象。被公认是诺贝尔文学奖“遗珠之憾”的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是最有影响力的非洲英语作家,他指出,为过去辩护的最好办法是树立“真实可靠的形象”,而非“很美很扭曲的理想”,作家的责任是把过去被剥夺的尊严重新找回来。西非的英语小说家大多书写文化冲突的伤心故事:西方入侵者把曾经井然有序的非洲社群变得四分五裂,个体成为“两个世界的人”,遭受心灵痛苦。阿契贝的《神箭》就是渲染着非洲传统文化和欧洲文明对抗造成的悲剧氛围:“没有一个思维正常的非洲人能摆脱灵魂深处的伤痛。我的小说告诉读者,他们的过去并不是野蛮的漫漫长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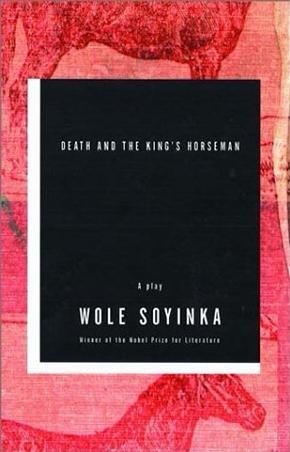
索因卡《死亡与国王的侍从》,W.W.Norton出版社
这条文学路径很快也到头了。1960年代,非洲社会内部矛盾取代了种族矛盾,民众梦想的新世界没有降临,于是他们捣毁了先前拥护的政府,子弹取代选票,紧接着军阀派系冲突升级成全面内战。现实的大环境迫使有责任感的作家关注群体内部的困境,而不是虚妄地重建非洲的历史和尊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剧作家索因卡擅长运用非洲口头文学传统,在剧作中大量借用约鲁巴神话来建构戏剧情境,但恰恰是他说出:“如果非洲作家想成为所属社会的道德记录者、所属时代思想的发声者,就迫切需要从对过去的迷恋中解脱出来。”法农的反思更具刺痛感,他写道:“在欠发达国家,传统的根基是不稳定的,并且因人心涣散而屡遭破坏。知识分子们急于创造文化作品时,没有意识到,自己使用的修辞来自本民族眼中的陌生人,是索然无味的异国情调。”他指出,作家要去的地方是民众深陷的领域,任何民族的真理首先是该民族的现实。读者会发现,1970年代以后,即便围绕着语言的分歧并未缓和,但无论用本土语种还是欧洲语种,比如提昂戈和索因卡,这些最优秀的非洲作家走向自省意识的文学,观察非洲本土的极端事例,应对现实中痛苦不堪的各种变迁。
索因卡写道:“我的非洲世界是复杂的,包括了精密机械、石油钻塔、水利电气、打字机、火车和机关枪。”这位87岁高龄、在疫情期间完成了新的长篇小说的老人,数十年一以贯之地强调,这个时代非洲不能逃避的严峻现实是反抗“与黑暗和偏执共谋的语言”,而探究、知识和思想交流的信条应被视作永恒的真理。
作者:柳青
策划:邢晓芳
编辑:周敏娴
责任编辑:邢晓芳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