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人类学学者对全职妈妈社群四五年持续参与、观察、记录和思考的纪实作品,也是社会学及人类学笔记,真实呈现全职妈妈的境遇,思索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困境,反思和探索女性价值多元的可能性。这本书给出的答案是:女性可以身处更加包容的社会,可以拥有更多可能的选择,并不需要被某种命运绑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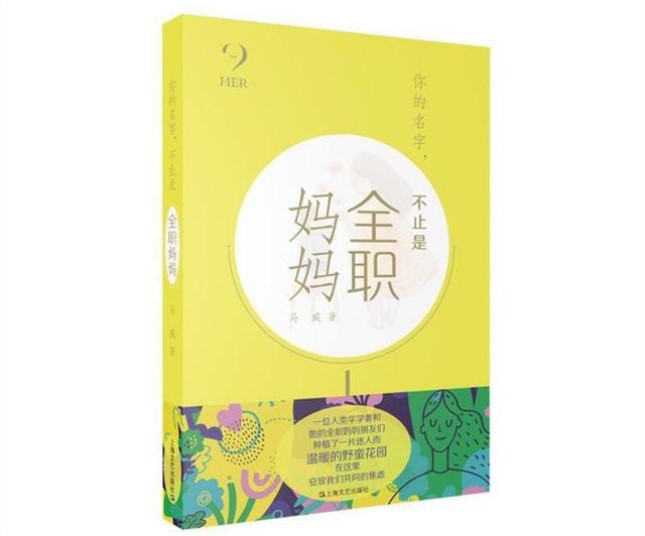
《你的名字,不止是全职妈妈》
马 威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书摘:
碰撞:那些现实的坚硬与柔软
四年来,我陆陆续续与自称为“全职妈妈”的女性群体对聊,在其中,我听到过“孤独”“无助”“烦恼”,我应对过“难过”“绝望”“挣扎”,她们讲述生活过往,即使再平和的状态也仅仅是“知足”而非幸福。这些女性生活基本富足,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们的情绪也许在很多人听来都是无病呻吟,但是她们却时常感受到来自与虚空碰撞而产生的坚硬痛楚。
“这些疼痛那么真实,但是为什么我就没办法把它讲出来。”
“我每时每刻都觉得自己被消耗,但是消耗我的是什么,我却不知道。”
“我的生活里没有什么好事,也没有什么坏事,但是我为什么总是感到绝望。”
在整理这些访谈资料的时候,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出疑问:
“她们为什么都有着或浓或淡的忧愁?”
“她们明明知足为什么却并不开心?”
“为什么没有一位女人被幸福充盈?”
“难道只因为她们是女人吗?”
还是,另有原因?

法国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男女两性的人生有着精辟的概括:
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我们非常不情愿地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只按照性别就粗暴地分为两类,“男人”和“女人”,但是,触手可及的经验却屡屡将人推至两条道路。男人被赋予了重任,不管这个重任是什么,总之,他们必然要走出去,在社会的捶打中历练价值,实现自我。而女性呢,因为她与人类新生命的诞生有着绝对联系,她就注定要为“诞生”生命做好准备,她注定要寻找一方安稳,一处庇护,一个能守护孕育、安放幼雏的安乐窝。比起男性奋力拼搏,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不同,女性则总被鼓励学会等待,接受追求,克制住所有可能带给她挑战的欲望。男人要驯服的是全世界,女人要驯服的是她自己,她只要找到那个愿意提供“窝”的另一半就足够了。这就是女人被教导要滑下去的快乐,而一旦顺从“什么也不必做”,那么一切所谓的获得也都无法属于女人自己。她可能会突然在某一时间发现,意气风发的丈夫总是行色匆匆,豆蔻年华的孩子们也急不可待地找寻自己的世界,年轻时诱惑过她的幻想逐渐黯淡了颜色,闪闪发光的美好画面也失去了清晰的轮廓,从憧憬中惊醒的她,面对的可能是一处毫无生机的沼泽,她捕捉不到成就,把握不住收获。她不仅是丈夫的观众,孩子们的过客,甚至她也与自己无关!
我们整个社会,无论是代际历史的纵向,还是国外对比的横向,都普遍缺乏对全职妈妈的认识和支持,社会舆论没有形成对全职妈妈存在的共识,全职妈妈的家庭成就被视为“理所应当”,全职妈妈的烦恼被认为“无病呻吟”,缺少被社会接纳和理解的公共舆论平台。家庭中的另一半也大多认为,“女人在家中,那么家里的一切都可以交给她了”。而如果家里发生任何事情,都会引起全职妈妈的深刻自责。
各种影视作品、书籍乃至自媒体,凡是聚焦于全职妈妈这一群体则有意无意放大着她们的这种焦灼与无助,伴随着全职妈妈群体越来越庞大,她们的公众面貌却趋于呆板。这些媒体似乎赋予“全职妈妈”声音,而这些声音传达出来的却是单调到无聊的“焦虑”“焦虑”和“焦虑”。

“其实,并不是这样。”在我访谈全职妈妈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每个人故事里都有着不同的精彩和落寞,也都有着与你我一样的轻松驾驭与拼命应对,有着不同的人生桥段,也有着相似的爱与哀愁。
每个人都会在某一个时刻对加之于全职妈妈的种种刻板舆论予以一个不同的展开:
“确实有的时候很失落,但也不是全部。”
“有的时候真的丧,不知道该咋办,但是……”
“(我的)状态也是起起伏伏。以前觉得很郁闷,但是……”
“失落”与“丧”都不出意外,我更愿意倾听的是“但是”之后的故事。
同样作为女性,同样作为母亲,同样作为妻子,我不想将脸谱化的模式套用到她们身上,我愿意去倾听,我相信只要她们讲述,故事必将精彩。
全职妈妈需要被聚焦,聚焦于她们每一刻不同状态的样貌;全职妈妈需要被倾听,听她们讲述一个纵贯女孩到女人完整线索的生命经历。
我接受过系统的人类学训练,也一直用人类学的视角去看待世界。人类学的使命就是拒绝刻板,拒绝对整个群体的单一想象,拒绝审视,人类学鼓励多声部,鼓励让更多的人参与述说,鼓励以尊重为前提的凝视。
人们普遍认为狩猎采集时代,远足狩猎工作由男人承担,人类学家发现位于菲律宾吕宋岛的埃塔人(Agta)女性才是优秀的猎人,她们不仅训练了猎狗,还能够结伴狩猎到大型猎物。
人们普遍认为婚姻能够为孩子提供合法性庇护,家庭亘古而永恒,伴随人类历史流传到今。人类学家则通过对母系氏族社会的研究发现男女婚配不过只是人类家庭制度设计的一种,摩梭人的非婚姻母系氏族家庭同样为孩子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支持与庇护。
人们认为部落社会人人都是挣扎着勉强求生,女性个人生命全部耗费在生育和哺乳。人类学家则亲身参与到部落生活,聆听她们动人的情感史,呈现出她们泼辣的生命张力。
被人类学家的眼睛观照过的世界,不一定能形成通俗易懂的浅显道理,也一定不会有警示效果的宏大叙事,但是,人类学的叙述一定会让你觉得,“哦,原来她们不止如此。”人类学总是将人从康庄大路上引入一处幽径,通往深处的一定是摇曳多姿的野蛮花园。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女性人类学者开始呼吁和倡导女性民族志写作。阿布卢格特(Lila AbuLughod)在她的女性主义民族志中写道:“由女性写就并且为女性而写的民族志可以看作是一种去发现独特的民族志研究和撰写方式的努力。”1986年,她出版了第一部关于非洲北部贝都因人妇女的民族志——《面纱下的情感》(Veiled Sentiments Honor and Poetry in a Bedouin Society),在书的前半部分,阿布对贝都因awlad村寨进行了总体描述,这是一个由父权来主宰的社会,男性的地位永远高于女性,年轻人一定要服从长者,女性主要的活动空间就在家内,她们既没有公共空间可去,也没有任何公共权利可以使用。但是在后半部分,阿布则将她所搜集和记录的“诗歌”梳理并展示出来,很多诗歌是由女性即兴创作,她们按照韵律将它们诵读出来,并代代传承。在诗歌中,女性刻画出另外一种现实,一种情感的现实,也呈现了一种游离于现实,沉醉于美感的状态,擅长诗歌的女性得到荣耀,补偿了她们在父权社会被边缘化的处境。
我陆续翻检以全职妈妈为主题的系列作品,女性身处的时代感、可能性、韧劲与丰富性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呈现,《坡道上的家》《妻子们的思秋期》呈现的故事太过压抑,《82年生的金智英》则没有探索全职妈妈所拥有的韧性潜质,《醒来的女性》刻印着典型美国郊区“绝望主妇”的印记,《女性的奥秘》《第二性》选择与哲学家、心理学家进行对话,这是来自女性知识精英的思考,普通女性无从置喙。
我则想以文字为载体,记述中国二线城市全职妈妈们的多声部。走近她们开启了书写的序章,倾听她们构成书写的主体,与她们共创各种活动则形成了书写的开放式结局。通过书写,我反而获得更多启示,陆陆续续的对聊与倾听促使我不断去探索这些女性的能量场,她们应对问题的韧劲与经营生活的力量,她们总是能够将岁月赋予生机,将琐事升华为艺术,她们总在似乎意义尽止的状态里探索出价值,总在情感干涸的困境里激活了自我,再次腾挪出一汪清泉。
当整个社会还没有觉醒到要为全职妈妈进行制度支持的时候,全职妈妈们自己在有限的空间与关系网络中编织起托载精神与自我的庇护所,每个人也许经历过“金智英”,她们的家也曾经在“坡道”上蹒跚,但是,她们仍然前行,将自己带离出金智英的精神窘迫,在更广阔的平原安放好自己的“家”。
这些静静地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女性,承载着古老的使命,成为新兴的阶层。她们开始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自我表述,或喜悦或无奈,她们所发出的个体吟唱还未能形成和声,外界对于“全职妈妈”群体感到好奇,却不能明了她们的状态到底如何。“记录下她们的声音”这一想法推动我开始对她们进行访谈,倾听女性们述说,呈现她们在家庭中承受过的“不可承受之轻”,以及她们跌跌撞撞却能量满满的探寻之旅。
作者:马 威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