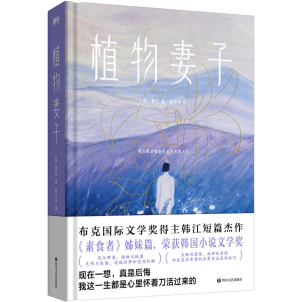
《植物妻子》
[韩]韩江 著
崔有学 译
磨铁图书 | 四川文艺出版社
水与火,柔软与尖锐,春天与冬天,植物与铁器……亚洲首位布克国际文学奖得主韩江在这些冲突中洞悉瞬间的感觉和印象,用美妙而生动的语言刻画命运的表情,在刺探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阴暗面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本书由八部中篇和短篇小说构成。短篇集关注“底层”人群,每个主人公都像在“没有希望的世界里像孤儿一样”流浪。他们从偏僻小镇的旅馆房间、考试院走廊尽头的房间、黑暗的地下室或多户型住宅和高层公寓的走廊尽头走出来,经过黑暗的楼梯和没有路灯的胡同,走进纷繁的令人疲倦的城市大街之中。
>>内文选读
脱身或向往植物的憧憬
现在,我是个危险的禽兽,
若我的手触碰了你,
你讲会化作黑暗,未知而遥远。
——金春洙《为一朵花作序》
有个诗人写下了歌颂花的诗篇。他在诗中告白:人们想接近被命名为花的这种存在,这种欲望无穷无尽,但是越靠近你,你就会变成越大的黑暗而消逝。我对你的欲望永无止境,于是将手伸向你,结果却把你淹没在无名的黑暗之中,我是只危险的禽兽。在“摇晃的树枝上”悄然绽放又凋谢,默默地接受消亡与黑暗命运的花,它对诗人来讲是令人悲伤的自画像,同时又是从忧郁的时代和令人羞愧的欲望中得到解脱的自由的存在。面对像“遮住脸的新娘”一样从不露出面貌的神秘存在,诗人把自己变成危险的禽兽去靠近它。而作家韩江也是内心充满了对花的热烈欲望而苦苦追求的一只禽兽。但是她似乎不那么危险,反而感觉那般病弱和忧郁。与其说是探索花的秘密的禽兽,不如说是梦想成为花的一只悲伤的禽兽。读着她的小说,我再度想起那个梦,那正是我生活着的禽兽的时间和想要得到解脱的梦想,我梦想着抛开所有欲望,最后变成植物。
中篇小说《植物妻子》里的女主人公不愿像她母亲那样出生在海边贫困村又死在那里,因此她远离了故乡。她打算向公司提出辞呈后离开这个国家到世界的尽头去,却因为爱上了一个男人 ,跟他结婚后定居了下来。她相信这爱情也可以到世界的尽头。但问题是爱情不会长久。她和丈夫之间的爱情渐渐消失,对话也越来越少(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语言”曾经是连接两个人的媒介。丈夫曾表白第一次见到她时被她的嗓音给迷住。但是她逐渐变得沉默寡言,最后丈夫连她的嗓音和呻吟声都听不懂。作品的结尾处我们听到妻子的独白,却无法传达到丈夫那里)。丈夫国外出差从“远处”回来时,妻子却站在阳台梦想着逃到“远处”。对妻子来讲,已经无处可逃了。铁制大门和阳台的铁栏杆所象征的“看不见的锁链和死沉的铁球”拘束着妻子的腿脚,使她动弹不得。所以当妻子说的“去远处”的一句话被埋没,她逃脱的欲望受撞时,她干脆失去了双腿。牙齿掉落,找不到一丝“两腿直立动物”的痕迹,就这样她逐渐变成了植物。
妈妈,我总是做同样的梦。梦里我的个子长成三角叶杨那么高。穿过阳台的天花板经过上层房屋的阳台,穿过十五层、十六层,穿过钢筋混凝土一直伸到楼顶。啊,在生长的最高处星星点点开出了像白色幼虫的花。膨胀的水管内吸满了清澈的水,使劲张开所有的树枝,用胸脯拼命将天空向上顶。就这样离开这个家。妈妈,我每天晚上都做这个梦。(《植物妻子》)
在痛苦和创伤的尽头见到的这一植物的世界,是抛开欲望的、绝对顺应的、被动的世界,韩江作品中人物反而在那里向自由飞翔。花终于穿过束缚着她的阳台天花板,又穿过屋顶的钢筋混凝土一直伸到楼顶向天空伸展。花不是静止的、软弱而被动的存在,而是以无比强大的力量向天空伸展的生命的实体。为此作者描写花的时候,用了动物性的比喻,说花“像白色幼虫”一样。现在这花能够自我梦想,自我行动,自我生存。因此在韩江的小说中被欲望、愤怒与仇恨所左右且自相矛盾的刀与火的世界或禽兽的世界和从欲望中得到解脱的花的世界尽管相互对立 ,却相互碰撞出生命的能量。例如,母亲自杀的铁道被记忆成河(《跟铁道赛跑的问》),加油站的老式电子公告牌上打着“火!火!注意防火”的字样,就像“金鱼的嘴一样”不停地开合,当主人公看见挂在电线上的雨珠时他的人生发生了转变(《在某一天》)。韩江的作品中花和水战胜了铁和火,我们通过它们的相撞看到了生命的世界。

▲韩江(网络资料图片),1970年生,毕业于延世大学国文系,现任韩国艺术大学文艺创作系教授,当代韩国文坛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曾先后荣获《首尔新闻报》年度春季文学奖、韩国小说文学奖、今日青年艺术家奖、东里文学奖、李箱文学奖、万海文学奖等。
或许,对忙于日常琐事的我们来讲,韩江所梦想的脱俗、脱身的境界多多少少有些抽象也离现实远了一些。尤其在《红花丛中》里这种印象更加强烈,《红花丛中》作品对生与死的根源提出疑问,并探究如何从欲望、暴力与创伤中得到解脱。如果说我们的生活像荼毗式中所看到的水与火展开的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役,那么,韩江要把生的冤孽通过“活着断了俗缘,死后肉身要经火化撒散到山中”的脱俗、脱身过程展现给大家的创作显得格外凝重而艰难。我甚至觉得,作为一名作家的韩红似乎想从“活”的欲望中得到一点解脱和自由。脱离禽兽的时间后想要进入花的世界的这个过程,有时也表现在从散文的世界走向诗的世界甚至禅的世界的过程中,因此显得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远了一些。与无穷的欲望中得到解脱,燃烧自身走向花的世界的人物相比,反而是《白花飘》中即便想要呕吐却还吞着饭的人物更让人觉得亲近,这是为什么呢?也许这对作者来讲是件残忍的事情,但我还是希望韩江再受一点“危险禽兽”的命运的捉弄。
本文节选自“解说——禽兽的时间,编织梦想的植物”,文/黄桃庆(韩国评论家)
作者:黄桃庆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