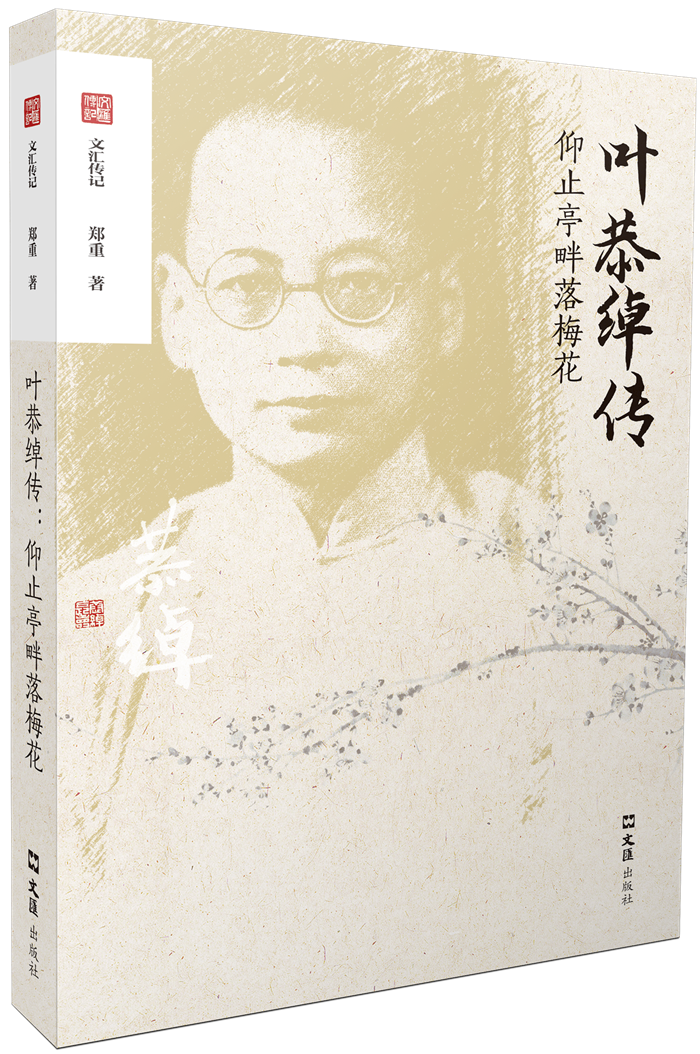
《叶恭绰传:仰止亭畔落梅花》
郑 重 著
文汇出版社出版
20年前,我在写《海上收藏世家》时,其中有一篇写了叶恭绰,那时只是把他当作一位大收藏家,所记的也仅是他的收藏生涯,没有能反映出他收藏高潮所处的那个北洋时代。在遗憾中却留下了“叶恭绰与北洋时代”这样一个题目,想了多年,真可谓“有此心,没有此胆”,一直不敢动笔。
所谓“北洋时代”,即是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奕钚、奕劻、翁同龢、李鸿章联名专折,奏议委任袁世凯训练新军,即小站练兵开始,中经1916年袁世凯称帝去世后的军阀混战、国家分裂,到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结束了国家分裂的局面,北洋军阀也寿终正寝。
光绪三十二年(1906),叶恭绰入邮传部,几经沉浮,1925年辞去段祺瑞执政府交通总长的职务,结束在北洋时代将近20年的宦海生涯。我想通过叶恭绰宦海沉浮的经历,应该能够看到北洋时代之一斑。
北洋时代是一个动乱时代,军阀割据,各方势力都想独霸中国,国家分裂,在“文统”和“武统”争论不休的情况下,发生了军阀混战。在中国历史上,北洋时代是最黑暗的年代,这似乎已成定论。但我认为,中国历史从鸦片战争开始转型,北洋时代是这一历史转型期最激越、社会变化最迅速的年代。新文化运动思潮、国粹保守主义思潮、改良派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风起云涌;民间团体党派组织此起彼伏,又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类学人从书斋走向社会,从幼发走向成熟。这样,诸多因素构成了北洋时代的特色:启蒙、思考、争鸣和觉醒。
在写作的生涯中,我比较欢喜写人物传记。因为人物传记是具体的,不只是他们的史料具体,而且他们的情感以及他们对那个时代的感受也是具体的,从人物的身上可以捕捉到历史细节。通过对几位人物的描绘,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历史画卷。处在北洋这样一个时代,可以说是与北洋时代相始终的叶恭绰,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冒鹤亭曾说:“叶某的脑子大概像一个货仓,把各种货物分类地存储,要用时一样样地取出。”叶恭绰的个性和思想是矛盾而相容的,他自己也说:“我一方面在讨论工业上技术问题,同时却可以谈谈宗教、哲学;一方面研究一个公司要怎样组织,同时又会想到音乐、书画上的问题。”又说:“对于一切的事情来到面前,从来没有忽略过丝毫,但从来没有执滞过丝毫。只是尽心竭力去做,到不得已的时候,我却会全盘割舍抛弃,一无留恋。”(《四十年求知的经过》)叶恭绰的学生、铁路桥梁专家茅以升,对他知之甚深,对他的评论是:“他不肯超越旧道德的范围来谋他个人的权位,他不肯轻试新潮流的武器来造他个人的势力。”(《遐庵汇稿·序》)这些都表明了从官僚到士绅,叶恭绰始终都是一位知识丰富、半新半旧的人物。叶恭绰有不少朋友劝他作自传,但由于他过于慎重与矜持,也有着正所谓“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故而未作。他个人认为:“我个人的历史虽说复杂,还不及我的思想复杂得厉害,思想是说不尽的。”(《四十年求知的经过》)
20世纪40年代末,叶恭绰的学生俞诚之等编著《叶遐庵先生年谱》,又经过叶氏亲自审读,虽有为尊者讳,但它是一部材料翔实而可信的著作,后来虽有几种叶恭绰年谱、叶恭绰研究等著作,有详有略,但都是以俞氏所著为依据。我在写此传记时,对叶氏的复杂经历删繁就简,避开了许多事件枝节的叙述,而是从叶氏的札记闲文及叶氏朋友尺牍中,寻找他的思想。《上海图书馆藏叶恭绰友朋尺牍》甚全,在该馆梁颖先生的相助之下,我对馆藏尺牍粗略地浏览了一遍;此后该馆编的《历史文献》又将其尺牍陆续刊载,为我提供了许多研读的机会。这些尺牍不只是叶恭绰,而是那一代人的情感、思想记录,我从中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可以作近代思想史而读之。所以,在撰写《叶恭绰传》时就想有别于其他作者所写的传记,而是以叶恭绰与朋友往来信札为主干,组成了本书的结构。
从立功来说,叶恭绰政事学术文章彪显,功德甚多,其中最为重大者则以交通建设为上。中国近代交通肇始于清末而发展于民国之初,叶恭绰于此时期经历邮传部书记员及交通部次长、总长,又掌管交通建设,运思极精,所经历大事及艰辛更难以计数,特别是收复铁路主权、提出铁路之独立,不属任何一家军阀所独有。正是因为交通之便利使军阀割据的局面很快结束。叶恭绰自言他并不懂铁路建设,何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这些只有从他与同僚、下属的通信中,才可看到他的“树人之不可缓、求才若渴、举贤如恐不及”的精神。古来的人立功多而不易立言,甚至功大的又多以文牍立言,言虽立而不传。叶恭绰与朋友往来的尺牍,使我们看到他在立功的同时又立言,这恐怕是在他的公事文牍中看不到的。就如同走进森林,不但看到主干,而且看到枝叶,避免了在人物传记写作时容易犯的“一叶障目”的错误。
风云激荡,叶恭绰时而在朝,时而在野,无论在朝或在野,他都是古代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勘察大同石窟、拦截敦煌经卷、支持西北科学考察、对流沙坠简的保护与研究,似乎都和新文化运动的潮流有些相抵触,从他的文章诗词中也看不出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叶恭绰和新文化运动的推手蔡元培,相识于南北和谈时期,他们又都带着很深的传统文化烙印走向共和。从通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在许多事情上共同合作,一脉相通。从整个文化发展史来看,张扬新文化和守护传统文化并不矛盾,两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叶恭绰说他的经历复杂,远不如他的思想复杂。他所说的经历复杂也就是他在朝为官的那个阶段,时而在职,时而被免职;时而复职,时而又被免职,需要他四面周旋,八方应酬,复杂得的确令人眼花缭乱。但他始终以传统道德与操守为底线,合则留,不合则去,进退自如,毫不留恋官位。经历虽然复杂,思想不甚复杂。但是对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与取向、宗教哲学信仰之探索、经济困境中的艰辛,以致到生命垂危之际以后事相托于朋友,经历比为官时要简单,但思想经历比为官时要复杂。对这个探索生命真谛的复杂心理,也只有从他与众多朋友往来的信札中读得出来。探索叶恭绰对生命的态度及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正是我为他立传的目的,企盼与其他作家写的传记有所不同。
叶恭绰是一位收藏家,如果说他的生活以收藏为轴,他的生命就是以这根轴为中心而转动。可以这样说,如果他不是从事文化保护及收藏,他就仅仅是北洋时代的官僚,最多只是过眼烟云的历史人物。
但是,从一开始他就不以收藏为自娱自乐,而是以守护传承者的责任在肩,开展学术研究。这是有别于其他收藏家的。他对一些藏品的研究,可以持续多年,逐步深入地揭示藏品的内涵。从众多的题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思想认识的复杂性。以《凤池精舍图》卷而论,他把自己在苏州的居所名之曰“凤池精舍”,在请吴湖帆作图时,此园已荒芜。在吴湖帆作此图前三年的时间里,他曾数次致信吴湖帆作此图,图成后他不只是自己题跋,而且请众多好友题跋。他尤感不足,仍然念念不忘地作题。从题跋中,谈形与神、名与实之哲学。我们能从中感受到他对故园的恋情,并看到他由此图拓展开去的对吴中文化的研究。
北宋燕文贵的《山水卷》本是傅增湘的收藏,叶恭绰于1925年得之于傅增湘或颜世清,是他的早期收藏之一。叶恭绰由此旁及燕文贵的《溪山楼观图》《武夷山色图卷》等作品及几幅宋画,并对它们进行了研究。这使我想到书画鉴定大家谢稚柳研究燕文贵仅存的四幅图及李成的《茂林远岫图》所进行的研究,并编著了《李成燕文贵合集》。
叶恭绰的研究和一般鉴定专家的研究有些不同。叶恭绰的藏品中有多幅佛像画,他把收藏和研究、信仰、人生融合在一起。叶恭绰收藏了不少僧人的作品及佛像,但他不信佛,不是佛门弟子,而是从佛学中寻找另一种精神世界。尘世给他带来许多烦恼,他想从佛学所提倡的精神世界求得寄托。
1968年8月6日,叶恭绰病逝,享年88岁。他爱交友,一生都在与朋友交游,即使是宦游生活19年,也没有远离朋友,而多是文化界的布衣之交。
正是因为他的交游之广,所以才能留下数以千计的友朋信札。披览读之,感到其中闪烁着“和为贵”的精神。“和为贵”是中华文化之内核,历史早已证明即使是国家的政治生活也是以和为贵。斗则伤,斗则乱,斗则败,何况朋友之间?叶恭绰与朋友交游,洁身自持,求同存异,与许多人终生为友,不背不弃。叶恭绰从青年到暮年都以白莲自喻。1934年去仪征顾园,开凿旧池,亲手种下白莲;1958年吴湖帆又画白莲为他78岁寿日祝祈,对花写照。从《五彩结同心》到《见心莲》,可以看到叶恭绰对民族、对社会、对朋友都是以肝胆相照。
整理旧稿,书香少年、北洋官僚、收藏家,叶恭绰的一个个绅士的背影总是浮现在眼前。
作者:郑 重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