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因为习惯披挂“乐观派”的外衣, 我成了他人眼中“最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年岁渐增,朝不继夕的事情亦随之而来,某一个时刻忽然觉得写散文已经无法让我在纸上一吐为快,于是变得更为焦虑而敏感。忖度再三,我决定尝试在创作上有所突破。
每当我经过长久斟酌之后开始动笔,我与我笔下的人物默然相视,静静地感知彼此,我能从他们身上获得我继续努力下去的力量和勇气。每当我关起门来独自面对这个世界,我也在书写的过程中开始学会理解世界并让自己释然。文学即人学,我必须慢慢学会如何能在审时度势的同时变得更加宽容,坦然接受“宿命的安排”。
有人说,写小说实在太难,而写散文、写诗歌或者写其他文体,则相对简单,对此我不敢苟同。于我而言,想要写好每一篇文章都不容易,前提是你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正所谓“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故而我觉得这种比较实质上毫无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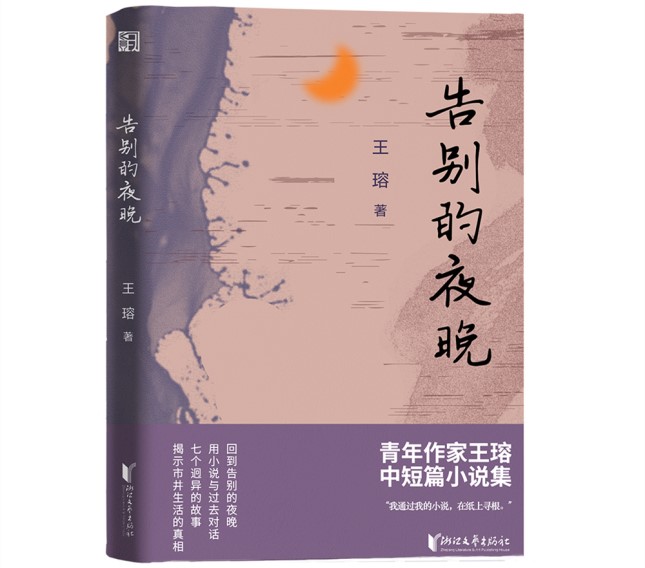
《告别的夜晚》
王 瑢 著
KEY-可以文化 |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目前这七篇小说,是在2021年之前完成的。而在此之前的近十年时间里,我写诗,写散文,也写一点纪实文学。我笔下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物与场景的构思设计,皆从我本人的人生经验中提炼锻造而来。我力求自己的文风独具个性,这便注定要与我的“故乡”休戚与共,血脉相连。
我的小说一如我的散文,都直通我的内心,而我的心事与我的精神血肉相连。唯有细节能够印证故事的合理性,而紧密独特的细节使得故事的真实性无可比拟,这让我的小说具有“个人特质”,但它绝非是个人情感的宣泄。我的这部中短篇小说集,实则为“每一次的回眸都于心不忍,却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沉迷于伤怀……”它们无声无息,却带给我在面容模糊的汹涌人潮中安身立命的力量。过客经此,纵然我早已经习惯了南去北来,一刻不停地途经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
2015年中秋,我的父亲仙逝,转眼已逾八载。这些年我在文字里频频回望,然而父亲能留给我的回忆实在不多。因此,这种复杂而沉重的情感由童年一直纠缠至今。它悄无声息却如影随形,成为长久以来压在我心头沉甸甸的石块。要感谢文学,唯有文字可以带来“精神意义上的激励或缅怀”。当我目睹父亲在我面前慢慢闭上眼,咽下最后一口气,我终于明白,那扇牵扯父爱的大门就此彻底关上了。那是一种茫茫然,手足无措的感伤。

父亲去世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夜不能眠,恐惧黑暗,不愿见人,屋子里的灯通宵亮着。我让电视机从早到晚开着,却二十四小时戴耳机借以阻挡外来声音的干扰。我无论睁眼,闭眼都能看见父亲就站在我的床前,他寂然而立,一如在世时缄舌闭口。父亲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我与他面面相觑,心照不宣。我突然觉得自己必须找到一个让积累已久的情感得以宣泄、释放的渠道,并借此让自己的生活尽快重回正轨。于是, 我想到把自己有限的生命中跟父亲的牵绊写成一篇小说。一开始也没想究竟要写多少字,就只是埋头写下去,当最后一个字敲完时发现是一个近三万字的中篇。其时,恰逢“中融杯全国原创文学大赛”正在征稿,我未及多想便将这篇小说发去参赛,最后获得大赛二等奖。这对于头一次尝试写小说的我来说,算是意外之喜,也就从那时起,我正式开始写一些中短篇小说。
世上诸多事,知易行难。当真正开始写小说以后,我发现自己变得更加焦虑,乐观豁达的我甚至变得自卑,因为我发现我笔下的故事跟人物总是无法让自己满意。有那么几个夜晚,我半梦半醒之间不断地与父亲邂逅,我在混沌迷离中惊醒,醒来时三星在天,我走到阳台往外看,霓虹璀璨,午夜的魔都如同巨大的蜥蜴静伏眼底。父亲的死让我头一次近距离感知“消失”的恐惧,纵使胸中有万语千言,顷刻之间都灰飞烟灭,而我身上的故事连同我的肉身,终有那么一天亦将成为虚妄。我突然按捺不住地想要把它们记录下来,这样即使未来这些小说孑然留存于世,对于现在的我而言,无疑是生命的全部意义。我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沉迷于文学,渴望在孤独而凄然的艰难书写中渐渐赋其于形。而也就是这一时刻我方才恍然,正是我的谨慎与诚实,才使得小说里的他们鲜明立体、情感充沛。
关于这部小说集,有的小说已经刊发,有的尚未发表。其中,《告别的夜晚》刊发于 2019年第三期《山花》杂志(发表时名为《黑白往事》);《室内地道》刊发于 2017年12月号《上海文学》杂志;《乌金墨玉》刊发于2021年第五期《西部》杂志。这些小说书写了我,也映照着我,无论过往、现在、将来,文学永不可能站在现实生活的对立面,而我之所以会选择这个“孤独而艰辛”的行当,并以此为生,其实是对自己已经逝去的三十几年人生的无言挑战。

现代都市的生活日益繁华,将喧嚣白热化,然而花钱也难买到“回乡”之感。“故乡”于是只能一次又一次跃然于纸上。或许忙于赶场的你,某一天忽然间吃到某一道菜,久违的滋味告诉你,这是一道家乡菜;抑或是你去看了一场年底贺岁大片,然后在摇曳不定、模糊堆叠的镜头中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弹指间已逾不惑之年,离开故乡许多年的我,早已经习惯行走于路上。南来北往,脚步难歇,然而何时能“回乡”?我是指真真正正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小住一段。转念一想,又不禁踌躇难安起来——哪个才是我要回的家乡呢? 是我成长生活过的太原,还是学习工作过的北京,抑或是久居于此的上海?
或许有那么一天,我会在某地遇见来世的自己,那时的我不再有今生今世的记忆。日月轮回,斗转星移,我将目睹已然安葬的自己重新复活过来,她静静蹲伏着,自身后一跃而起,趁我不备将我踹醒……
我通过我的小说在纸上“寻根”。 因此故事中随处可见颇具北方况味的描写,风土人情、民俗文化,我永远愿意相信,一定有更美好的人与景在向我招手,静静等待着我将他们尽快付诸纸上。这样想来,“故乡”回不回得去又有什么关系呢?“故乡”在我的笔下得以永生,她的鲜活与苍然都将活灵活现,重现于每一个小说人物,而最令我愉悦的是,他们永远跟别人所说所写所唱,所以为的截然迥异。
感谢文学。人与物质世界的绵密交感,其实始终在延续,而不同时代的变更与交替,具体到我个人而言,一些简单的词语、镜头,频繁出现在梦里的父亲,会自然融入我的童年、青少年时期的记忆碎片中。又是一年将尽时,我不断地借用小说与过去对话,企图重现父亲尚且在世时未及问出口的话,问他为什么至死也不给母亲一个交代,为什么不喜欢家里唯一一个女孩的我……而为小说不断地反复编排的过程,慢慢让我懂得并且接受,即便再如何拓展、深入,作为个人,永远只能徘徊于“独自情感与视野”中。个体与众人的关系,隔代的触碰与纠缠,好像是一旦看清了某些细节,周遭便愈加混沌迷茫……
(本文为《告别的夜晚》一书自序)
作者:王 瑢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