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龄修先生给历史所带来的学术清誉,要远过于历史所给他的名与利。
何先生这一代人,是从强调集体主义的时代过来的,常常会认为,一个像社科院历史所这样的单位,必须有些集体项目,才能显示出这个单位存在的必要。他在《中国史稿》第七册《后记》中说,“一个学术机构只是人自为战的局面恐怕也不行,组织集体力量写出有价值的有系统的大部头著作,实在是这类机构的生命线”。在高校工作的学者,也常有类似的要求或期许。
何龄修先生欣开九秩,世愉先生主持的《清史论丛》拟出专号以示庆祝。他知道我自来所后,常常听何先生讲掌故,也知道何先生对我多有关照,所以特地嘱我写文。2013年,清史室主办了隆重的庆祝会,不少受过何先生教泽的学人都赶来庆贺,如张玉兴先生就是从东北远道而来的。姚念慈先生特意精心准备了发言稿,详细谈了何先生的学术研究的特点和贡献。他觉得自己发言时间长了,中间曾两三次中断,问大家是不是自己发言时间太长;如果太长,他可即刻停止。大家都表示没有关系,他才又继续发言。中午一起聚餐,大家兴致都极高。这是我来所以后,极少遇到的为老先生庆寿的学术活动。
转年,《清史论丛》“何龄修先生八十华诞纪念专集”印了出来。我的小文在刊发前,呈何先生过目,他纠正了我若干记忆有误之处。所以,我说他身体虽时有小恙,但并无大碍。此后他还参加过所里组织的一些学术活动。然后,又转年的秋天,我的小书出版后,赴何府拜谒呈正时,老人已受阿兹海默症的折磨,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前一句还是清醒的话,下一句就离题万里,口里喃喃自语。其间,他还喊师母:“给小孟准备行军床啊,不然,他晚上怎么睡呢。”师母连声应道:“好好好,我给他准备。你不要着急。”看着他,真是心里说不出的难受。现在,他已经走了,我觉得对他而言,是一种解脱。我想他也一定希望得到解脱。
何先生对清史研究史非常关注,他曾写过好几篇文章,谈清史学科的成立和发展。他认为孟森先生是清史学科的奠基人,他的学生商鸿逵先生曾花了很大的精力,整理出版孟森的著作,这就是为大陆学界广为使用的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明清史讲义》《明清史论著集刊》及《续编》。但直到商先生仙逝,孟森最为重要的未完成的著作《明元清系通纪》也未能以完帙面世。何先生认为学术界对孟森的表彰是不够的,于是接受了三联书店孙晓林先生的委托,编辑《孟心史学记》。承何先生不弃,命我帮他做些杂事。他常常跟我念叨,这件事,是他们这辈学人的责任;他们不做,了解孟先生生平的人越来越少,将来更难得有人做。为稿件的事,常陪他到三联。负责该书编辑、出版事宜的孙晓林、曾诚两位先生每次都会请我们在附近吃饭;在饭桌上,我们就总能津津有味地听何先生谈往事。于是,我们就一再撺掇他写出来。他动了心,就陆陆续续,一条条、一点点写,渐渐成了一本回忆录的规模(这本《五库斋忆旧》,经刘小磊兄编辑,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印行)。也许是受此事的激发,在这前后,他写了一篇比较详尽的《自述》。
他1933年11月出生于湖乡县,祖上据说是咸丰年间从江西迁来的客家。光绪年间,左宗棠在湘乡招兵,他的曾祖父投入行伍,随左氏西征。后来左宗棠内调,他的祖父也回乡成家,开设酒席馆;因自小学习烹调,技艺精湛,成为县中有影响的厨师,擅长燕窝烧猪、生炒肚丝、汤泡肚尖、蛋糕杂烩等名菜。他祖父生二子,他是长子所生,但出生即过继给他叔父。他的叔父即养父继承了他祖父的厨艺,并且能出蓝跨灶。有次,听他讲起往事,说过去的厨师都有些窍门或绝活。比如,某道菜,需要先将整只鸡过水煮一下;但这一煮,往往会使鸡皮发紧,不好嚼。他祖父就有一招,把水里先放点什么(他告诉我,我忘了),就可以使鸡皮不会变紧。2002年,我随侍何先生前往广州暨南大学参加纪念陈乐素先生诞辰百年的会议。那时,他已患帕金森病,但症状并不太明显,只是在夹菜时往往手抖得比平常更为厉害。他也不无自嘲地说,这病,就是不能紧张;平常在家也没事,越是场面就越抖。所以我总坐他旁边,帮他把菜夹到他小盘子里。一次餐会后,他笑着对我说,“你小子,不会吃”。我说,您怎么知道。他说,“会吃的,不是你那种吃法”。我忙叩问所以。他继续笑着说:“每道菜上来,只吃一点,是为品尝。像你那样,三下五除二,菜还没上完,你就先吃饱了,还怎么品尝呢?你那是为吃饱。”我出生在北方农村,一出生就是“文革”十年,哪里能想到“品尝”呢。他又说:“品尝,不难,就是要多见世面。这跟读文章一样,读得多,自然知道高下好坏。”说完,又笑呵呵加一句,“你就是没机会吃好的。”他虽然深得祖父的疼爱,但大家庭的种种纷争,特别是他养母的被迫离异,还是让他体会到了人情冷暖,也增强了生活的自理能力。
1944年6月湘乡县沦陷时,他已在县城读完初小(三年级)。光复后,他进湘涟中心小学读高小。1947年秋入湘乡中学读中学。这期间,湘乡解放。1952年秋,湘乡中学高中部最高的两个班与湖南省立第十五中学 (改名涟源第一中学)相应班合并,他转至涟源。1953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成为全国第一届历史系五年制的学生。他在《自述》中称:
我们有幸受到许多名师的系统教育,其中有中国史的翦伯赞、向达、邓广铭、商鸿逵、吴晗、张政烺、汪篯、许大龄、陈庆华,世界史杨人楩、齐思和、周一良、胡钟达、张芝联,考古学夏鼐、苏秉琦,哲学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潘梓年、李光灿等先生,都是当时学术界、教育界的精英、优秀代表。我们在世界观形成、品质修养、史学方法训练、历史基础知识积累等多方面,得到他们的言传身教。汪先生课上课下常给我们讲自己读马恩著作的体会,结合专业讲尤觉亲切易懂,听完后总感觉恍然有悟。邓先生强调学好理论,也要掌握四把钥匙(年代、地理、职官、目录学),特别深入人心。在袁良义先生指导下,我学习明清史,阅读了一些明清史籍,特别是方志、别集。我的毕业论文题为《明代的山陕商人》,也在袁先生指导下顺利进行。这是我自选的课题。我学习傅衣凌先生,搜集了若干山陕商人的资料。结果我只写成大半,没有完篇。我感到不甚满足,认为傅先生用传统方法排比资料,没有进一步应用经济学的方法做分析。我试着绘制了山陕商人资金流动示意图,但知识菲薄,思想幼稚,所做“分析”,非驴非马,而且几句几行之后,再也无话可说,真可谓自不量力。
1958年秋天,大学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组。
他把自己的研究经历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以前,是第一阶段。这个时期,主要是参加集团项目。“在大学时,我受政治运动的影响,逐渐形成大集体的想法,认为始终在集体中则毕生一路平安,确定只做集体工作,不搞个人项目的原则。这就需要把个人融合在集体之中,不搞 ‘地下工厂’,不争个人名誉、地位,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必要时能把个人求得的学术成果、找到的好史料贡献出来,全心全意工作。”这个阶段参加的学术工作主要有《太平天国运动史》《中国史稿》(第七册)《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的编写。后两种书,都是八十年代才陆续出版的。
第二个阶段,是从1978至1993年退休(研究室返聘至1996年)。这个阶段,除协助杨向奎先生办《清史论丛》和受命组稿编辑《清史资料》,帮助清史室年轻学人选定研究方向等庶务外,主要的工作,一是《中国史稿》第七册的扫尾、出版(作为这一册的召集人,他称这是“最繁重、最累人”的工作),使这部由历史所牵头的“郭氏通史”终成完帙(其实在郭逝世后编写的诸册,为文责自负,即不再署郭氏为主编)。二是参与《清代全史》的工作,特别是组织编撰《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即清前期),花费了他大量的精力。他说,“我对全部稿件200余篇做了加工(其中有些满族人物传记,是约请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同行写的,我只最后审读,并做技术加工),统一体例,修改文字,调整内容,纠正错谬,增补史料,甚至完全改写”。何先生逝世后,远在日本工作的郝泽宗先生托朋友致送赙礼千元;这位朋友托我转致。我问所以,才知郝先生就是当年在何先生的指导下,撰写了《汪懋麟传》,并被收入《清代人物传稿》中。他自称“对于室里的工作,我真是全力以赴,不惜时间,不吝精力”,乃实事求是之言,毫无夸张。
也就在这个时期,他终于敢就自己感兴趣的学术问题,进行“个人”的研究工作了。这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明清之际的反清复明运动和清代艺术史。前一项研究,大致始于他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他说:“捧读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时,看到他史实挖掘之深,竟然揭出清初存在的暗潮汹涌的大规模地下反清运动,以及到处取材,驭重若轻,驾轻就熟的史料学功夫,深感震撼。揭出‘复明运动’,科学意义重大,有助于恢复清初历史的全面性、复杂性、真实性、丰富性。”为此,他于1988年撰写了《〈柳如是别传〉读后》。此后的十年,他研究了江南、浙江、湖广、北方的复明运动和复明大案,集中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发前人所未发,揭开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史事。他不无自豪地说:“其中李之椿、平一统、杨鹍、虞胤、陶尔鼐等案和史可法扬州督师幕府人物,前人所知甚少;魏耕、李长祥、吴祖锡等的活动,从前虽有研究,但多缺漏,失误。这种状况在理论和史实结合的基础上给我留下了广阔的发挥余地。”这些成果,大多结集为《清初复明运动》,遗憾的是编辑有些自以为是,如将作者自称的“我”统改为“笔者”,文气似乎都不顺畅了。这很让人疑心,责编还动过什么手脚。
对后一项研究,他说:“我自我感觉良好的,有明清隔壁戏研究,和说书艺人柳敬亭、昆曲清唱艺人苏昆生(二人即吴伟业所说的‘楚两生’)研究。我研究了隔壁戏起源、发展、消亡的全历史过程,描写其状况,分析其必然性,即探索和概括其运行的规律。”三联书店近已编就他的《民族艺人“楚两生”》一书,应该很快能面世。届时,我们一定能体会到,一位史学家在研究艺术史时,对材料爬梳的功夫、对历史背景的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对艺术史的认识。
他晚年自己最为看重的一项工作,就是1997年开始,参加的由王钟翰先生牵头的“四库禁毁书丛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对这份工作,他直言:“在那里打工,报酬不高,但我不是奔那个去的,我喜爱这份工作。四库禁毁书大部分是善本、孤本书,我几疑工作过程是进入了皇家翰苑,在那里纵情留览外间难得一面之书。”“我作为学术负责人,首先要保证进入丛刊的禁毁书身份的真实性,不是另一作者的同名书、同一作者的另一书、禁毁后的篡改本,以及其它鱼目混珠本,而不折不扣地确为乾隆禁毁的那种书。”“据估算全套400册约共56万页书,一、二审纠正大部分错误。我三审(我看了总册数的略超六分之五)是最后一关,最后印制出书,是否遗留有错,是我的责任。全部排列无误,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稍一走神,就有漏网之鱼。”他对山东省图书馆所藏达六百叶的钞本《新纂乾坤宝典天文》装订错误的纠正,正可看他对书的热爱和对这项工作的高度负责:
二审时,审读的先生发现此书只有前面百余页装订正常,余则混乱错杂,不堪卒读。原来,馆方拆开修裱此书,裱工师傅中途忘了标记书页次序,只好拢到一起,分册订线了事,以致如此。最恼火的是,全书无目录、无页码,缺少分割内容段落、排列顺序的标志;又是孤本,缺少对照清理的参考资料。当问题摆到我面前,我知道这是对我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挑战。我反复翻检全书内容,发现书中有大量小标题是解决问题的惟一可依赖的线索。经过仔细阅看,我感到小标题都讲列星,也有不同,归为两类:嵌有二十八宿星名的一类;其它的一类,多与气象有关联(分别简称为二十八宿类、气象类)。气象类有线装书页略超400页,但其中百余页排序正确,只有200多页需要我们排出来。小标题多,是绝大帮助,200多页中,只有四个小标题下文字超10页(《中宫紫微垣经星占》38页、《太微垣星占》19页为最多,共占80页),其余为每题数页,以1、2、3、4页者居多。于是我根据小标题与内容的关系、小标题之间的联系、文字的衔接等多方面因素,很快就把气象类书页次序排出来了。经过查书,我了解到从汉到清二十八宿排序无变化,决定利用二十八宿小标题分割这一类书页排定次序。如果不是找到这一分割标志,174页书就成为混沌一片,排序难度就大得多了。分割以后,每一星宿小标题平均只领有6页多一点,找齐就比较容易,排序的问题也得到圆满解决。似乎比较困难的问题,顺利地得到解决,看起来我选择的路子是对的。
读到这里,我们都不禁为何先生感到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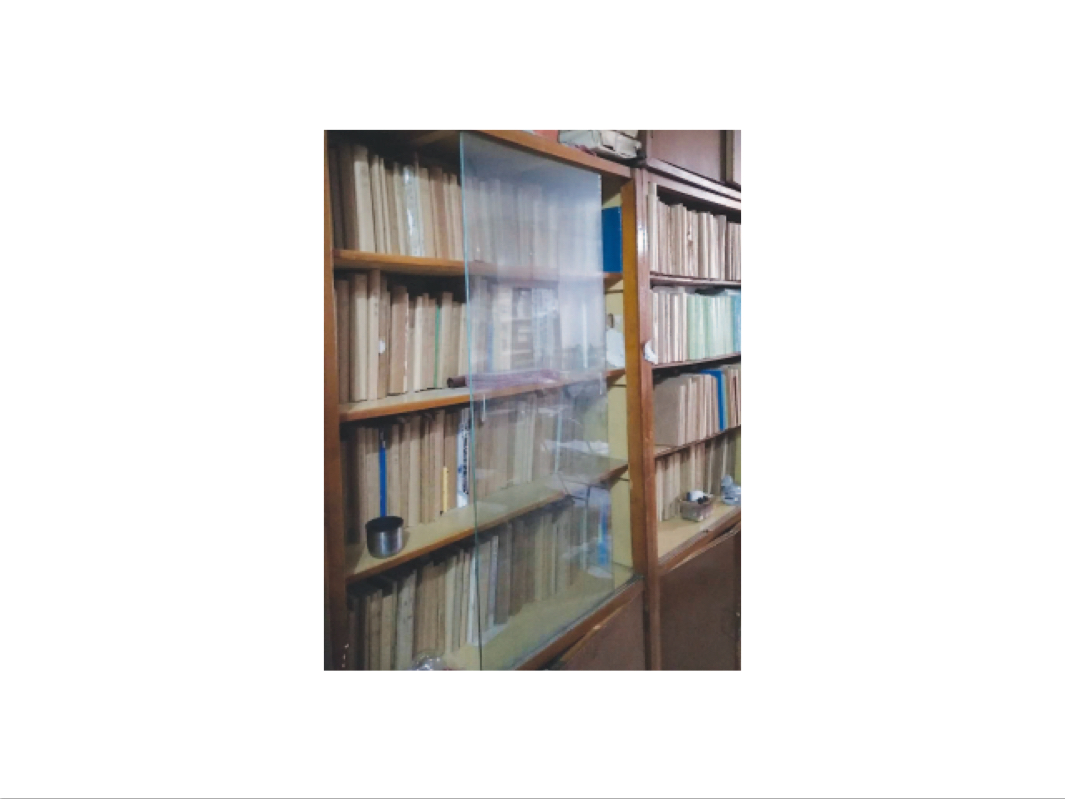
▲何龄修先生朴素的书架
何先生这一代人,是从强调集体主义的时代过来的,常常会认为,一个像社科院历史所这样的单位,必须有些集体项目,才能显示出这个单位存在的必要。他在《中国史稿》第七册《后记》中说,“一个学术机构只是人自为战的局面恐怕也不行,组织集体力量写出有价值的有系统的大部头著作,实在是这类机构的生命线”。在高校工作的学者,也常有类似的要求或期许。其实,在我看来,办研究所跟办博物馆、纪念馆有点类似。有钱,大可以多办几所;没钱,也可以少办乃至不办,毕竟这不牵扯国计民生。多办或少办,也都跟它们应该如何工作、如何运作,没有太大关系。就古代史研究而言,除了必须合作方能完成的具有基础性或工具性的工作之外(如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如点校二十四史,等等),大量的或常态的研究工作,都是要研究者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取长舍短,进行研究。动辙设立课题、上马工程,还要有梯队、有带头,对古代史研究来说,这实在没有必要;研究毕竟不等于编书。
何先生的一生基本是在历史所度过的。他对这个单位的心情,我想是比较复杂的吧。2008年,他75岁年,我们以所青年史学沙龙的名义,为他举办了“从事学术研究五十周年”的活动,老人讲的题目是《太子慈烺和北南两太子案——纪念孟森先生庭生一百四十周年、逝世七十周年》。我在5月16日的日记中称“何先生讲了一小时,精神颇好”。这大概是令他感到一丝欣慰的事。倘若用我的市侩的眼光看,何先生给历史所带来的学术清誉,要远过于历史所给他的名与利。
何先生论著,除结集为《五库斋清史丛稿》《清初复明运动》以及很快面世的《五库斋忆旧》《民族艺人“楚两生”》之外,还有些零散论文。很希望将来有机会编辑出版“五库斋清史丛稿拾遗”,以纪念这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纯粹的学者。
二○一八年四月廿六日于新都槐荫室
作者:孟彦弘(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编辑:范菁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