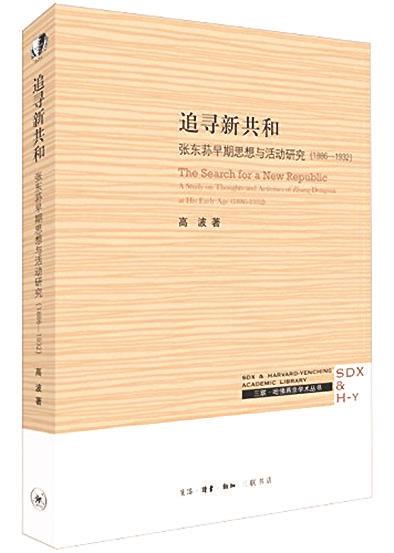
面对传统士人阶层已经堕落坍塌的事实,张东荪认为士人的历史使命应当从“辅治政治”转向“辅治社会”,在社会和文化层面成为大众的导师;士人阶层非但不应当恐惧大众,反而应当与大众打成一片,并最终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新生”。
为政治性知识分子作思想传记,是一条相对独特的史学路径。这类知识分子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既不是纯粹文人,也不是纯粹政治人物。他们自己会生产出一些关于政治的理论,这些理论不仅能够用来解释同时代人的政治处境,还可以用来批判或者嘲讽他们自己的政治实践(因为往往是失败的)。他们不仅是所处时代的阐释者,同时也是自身命运的解说人。历史学家书写他们的思想轨迹,无异于是与传主进行一场对话。高波的《追寻新共和:张东荪早期思想与活动研究(1886—1932)》(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就是这样一本对话式作品。
以善变著称的张东荪并不是一位理想的“对话者”。少年时,他被清廷公派到日本,回国即被授予七品官职,然而辛亥革命的枪声一响,他就南下加入了临时政府。待到南北妥协,政府北迁,他觉得“周围的人都不像是在做事情的”,于是转入报界。在智识上他是新派,却对传统心怀眷念,主张“不骂不破坏”,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中与《新青年》派吵得不可开交。他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之一,但与中国共产党的组建擦肩而过,并掀起一场社会主义大论战,与陈独秀等早期中共党员分道扬镳。他信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可是这个主义的正宗代表罗素却偏偏认为,俄国道路更适合中国。他多次表示厌恶政治,不愿意“干政治”,只愿意“评政治”,但他不仅担任过参议院秘书长,还和张君劢一起组建了国家社会党,积极参与民主同盟的活动。为了抵制国民党召开的伪国大,他又不惜与一生的好友张君劢绝交。他成了中共最信任的盟友,不仅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立了“第一功”,还在新政协参与了建国大业,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但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又旋即卷入一起间谍案,自此政治生命彻底结束。这样的人生,仿佛落叶在风中兜了无数圈,令人唏嘘。
当然善变不是张东荪的专利。人总是会变,穿梭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而且在许多时候,的确是“形势比人强”,政治性知识分子不得不改变甚至“改造”自己的想法。严复在晚年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就转而成为西方文明的批判者:“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31页)但是我们又不能把政治性知识分子的每一次思想和立场波折,都解释成是对某个具体历史情势的条件反射,仿佛他们只是提线木偶,表演着自己无法掌控的命运。政治性知识分子大都超越了书斋,积极“入世”,主动参与现实政治。至于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适应政治生活,则取决于性格、眼界以及机运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一些熟悉张东荪的朋友和研究者就指出,这是一位痴迷政治但又过于自负的书生,往往会高估自己在政治领域的作用与能力;即便在一些重大政治抉择中栽了跟头,吃了大亏,他还是会固执己见,绝不轻易低头(参见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7-89页)。
这也就意味着,所谓张东荪的“善变”只是表象,在他的内心或者思想深处,依然会坚持一些“不变”的东西。
《追寻新共和》这本书的努力,在我看来,就是穿透张东荪的“善变”表象,去抓住其思想中某种“不变”的连续性。因此高波不打算按照历史时序,来简单罗列张东荪一生的思想碎片。如果是这样,那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很可能是一团千头万绪的毛线。而高波想要做的,是“找到隐藏在这一堆杂乱材料后的某个‘一’”,“将张东荪的一生收拢为一个整体”,“以看清张东荪的全貌”。作者的具体做法,是用两条宏大的历史脉络来概括张东荪的所处时代:其一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欧洲兴起的大众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其二是从同时期开始中国迎来的政教“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趋于同步。于是民主在近现代中国的展开,被“设置”为张东荪一生都走不出的生活背景,同时也是他无法绕开的思想议题。如果张东荪的思想碎片真的能够被编制为一个“整体”,那么民主就是高波手中最主要的理论线索。
从结构上看,除了一头一尾的导论和结语,全书十一章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至四章,介绍张东荪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活动以及观点;第二部分是第五至七章,讨论张东荪在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中的态度和立场,并引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道路问题;第三部分是全书的核心部分,即第八至十一章,介绍张东荪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矛盾态度以及转变过程。如果说第一部分针对的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共和”,那么第三部分则通向新中国即将建立的“社会主义”;第二部分夹在中间,是一个过渡。实际上,《追寻新共和》由高波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来,而这篇论文的题目正是 “共和与社会主义”。我们可以把博士论文标题中的“社会主义”,理解成这本书标题所谓的“新共和”;或者,把“共和”和“社会主义”理解为两种不同的“民主”形态。但不管怎样理解,这两个标题都寓意着,在作者设定的时间段之内,即1886年至1932年之间,张东荪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
在第一部分,也即张东荪的第一个思想阶段,他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走向共和。其实在辛亥时,他对革命的理解非常简单,“就只知道要革清朝的命”。和当时许多人一样,他把“民主共和”与推翻帝制笼统地画上等号。而且由于革命进程颇为意外的“顺利”,他也乐观地相信共和能够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经过民国初年一连串政治动荡与分裂,张东荪不得不开始反思共和何以失败。只不过,此时他更愿意从道德角度寻找答案。他认为民初政治的失败,在于政治精英,无论是革命派还是北洋派,都缺乏政治精英应当具备的政治伦理;他们既不能自我约束,也不能彼此共容。就整个“国民性”而言,中国人也缺乏西方人的那种共和精神。所以他认为要想重建共和,就必须重塑国民道德。只不过,他又主张优先教育“中等社会”,让学生、士绅和商人等社会精英成为新道德的主要载体。进而他提出的贤人政治理论,也是主张由少数道德优越的“贤俊之士”来执掌国政。在他看来,由多数人构成的大众的共和道德,就是对贤人统治的“虔服”。所以高波犀利地评价说,张东荪这时设想的共和,不过是“披着人民主权外衣的士绅共和国”罢了。
第二部分有些零碎,三个章节分别介绍了张东荪在传统文化、社会改造以及组党等问题上的观点与行动,前后联系并不紧密。但从总体看,这些问题都是在回应新的历史形势。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西方文明内在的矛盾与缺陷,促使一部分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十月革命的爆发,则为对民初共和彻底失望的人们提供了新的制度方案,即社会主义。当本书行进到第七章末尾时,社会主义已经取代共和成为作者讨论的核心问题。其实早在1913年,张东荪就已经谈论过社会主义,当时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的中国,社会主义“无发生之余地”。但是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他再一次走在了潮流前列,成了引人关注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民国初年的情况类似,此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和当初对共和的理解一样多元化。张东荪倡导的是“浑朴的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而且他认为必须首先进行“精神上的革命”,然后才是“物质上的具体制度的改造”(左玉河:《张东荪传》,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第80-81页)。这显然是他前几年道德理论的另一种表述。虽然他在许多方面都认同布尔什维主义,但终归算不上同路人。
第三部分始于1920年,张东荪陪同罗素访问湖南。初次深入内地让张东荪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究竟有多么贫弱。在罗素的影响下,他又重新拾起自己在1913年表达过的观点,主张发展实业优先,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主义则都应当缓行。这无疑给当时的社会主义热潮泼了一盆冷水,特别是在不久前,他还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最主要的鼓吹者之一。很快他就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群起而攻之的对象,并由此掀开一场社会主义大论辩的序幕。
颇具戏剧性的是,罗素在离开中国前突然改变了想法,认为中国缺乏自己支持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土壤,所以还不如走俄国道路。这一变化让张东荪非常尴尬,但他并没有退却,反而越战越勇,在辩论过程中更加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理由: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阶段,中国没有“拒绝资本主义的能力”,因此必须长期忍耐它带来的罪恶后果;而且“忍耐”的对象是本国资本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抵御国外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压榨;中国并没有“阶级对立”,效仿俄国只会导致一场实为暴民动乱的“伪劳农革命”;国家社会主义会让政治吞噬社会,也即让国家包揽一切……在辩论中,他明确提出基尔特社会主义优于布尔什维主义,因为前者注重实业,只是要求对资本主义加以限制,并且对政权也没有太大的野心,不打算搞激烈的政治对抗和阶级斗争。但事实上,张东荪又不得不承认罗素的判断,即基尔特社会主义更适合西方发达国家;在中国,按照张东荪自己的逻辑,它与布尔什维主义一样都不具有可行性。所以高波也忍不住评论说,张东荪只是个“勉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
论战结束之后,布尔什维主义在现实政治中的发展肯定超出了张东荪的想象。而他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则只能长期停留在象牙塔之中。他似乎已经跟不上形势,或者不愿意去紧跟这样的形势。面对风起云涌的五卅运动、国民大革命和北伐战争,张东荪竟不置一词。1927年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时,张东荪还作为“学阀”被通缉,不得不避入租界。
但随着时间进入1930年代,张东荪的思想轨迹再次出现转折。而这次转折,同样以国际国内的重大政治格局变化为背景。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和民族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救亡图存再次成为最为紧迫的时代主题。张东荪也就不再坚持“政治/社会”二元分离的信念,开始明确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现在他认为,要想实现民主,必须得有一个统一且强大的国家。而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功范例,让张东荪看到布尔什维主义同样可以发展实业,因而需要放弃资本主义是强国必经阶段的错误看法。种种这些变化,都促使张东荪与布尔什维主义和解,并且与中国共产党走得越来越近。
在1949年后,张东荪回顾了自己民主思想历程:第一期是在抗日战争之前,他“抱着旧民主的梦想”,“既反对国民党,又反对共产党”;第二期是抗日战争到1947年,此时他“想与共产党合作,而不是受共产党领导”;第三期是1947年到新中国成立,他接受共产党领导,但还是“希望在新民主之内仍可以保留一些旧民主式的自由”。《追寻新共和》的副标题把时间限定在1932年之前;也就是说,张东荪的民主思想刚刚转入他自述的第二期,这本思想传记就落下帷幕了。但是高波的思考与论述,显然溢出了自己设定的这一时间段。特别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也即第十一章,从表面上看是在介绍张东荪如何完成第二期的转变,但实际上却是为张东荪整个的人生命运作出总结陈辞。
高波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张东荪在本质上还是一个深受传统熏陶的士人,始终不忘政治与教化的双重使命。因此他所追寻的“共和”,无论展现出怎样的理论形态,骨子里都是基于他对自身传统的“乡愁”。他从头至尾都不是大众民主的真正支持者;在他看来,工农只是统治与教化的对象,而不可能独立具备实施善治的能力。面对传统士人阶层已经堕落坍塌的事实,张东荪认为士人的历史使命应当从“辅治政治”转向“辅治社会”,在社会和文化层面成为大众的导师;士人阶层非但不应当恐惧大众,反而应当与大众打成一片,并最终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新生”。张东荪后来选择支持共产党,其根本动机并不是为了改造政治,而是为了改造社会;只要社会改造好了,政治回归“正道”也就指日可待。
作者:岳林 上海大学法学院讲师
编辑:周俊超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