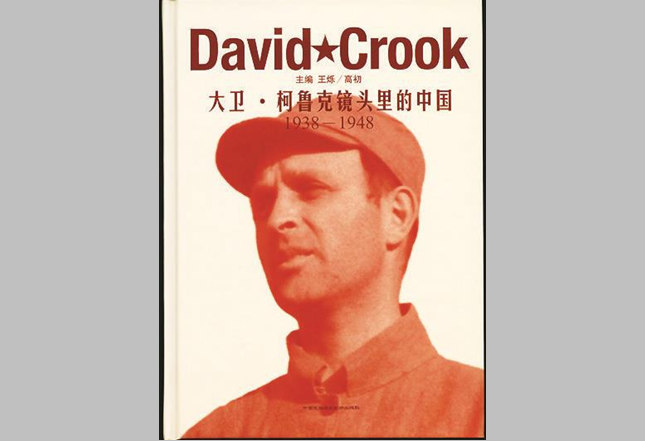
当时,我父亲在一次晋冀鲁豫后代集会上结识了柯鲁克家长子,说起我在做的事,他说他家有很多这类资料,就邀请我们去他家里看看。土改题材汇集了我自己所无法处理的最困难的那些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我一听到这个题目就很兴奋。在胶片比较匮乏的时候,一个共产党摄影师所拍的土改最多几十张,他不会像柯鲁克夫妇一样,花八个月时间去拍一千多张东西。所以这一批资料在题材上和在我自己要面对的学术问题上,都是我所期待的一个题目。

2011年,每周二和每周四,上午 10点半到 11点半,伊莎白精神好的时候,我和王烁就一起来到她的家里。伊莎白是一位很好的学者,又是一个对于中国革命有非常深入了解和同情心的人,她所在的处境和学术训练,以及她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耐心,站在不同的背景立场和岁数中的争论,其实对于我们有非常好的影响。她是在世的最重要的一位国际友人,但她拒绝接受更好的物质条件,住在北外一间非常俭朴的宿舍里,每次从她家里走到楼下的时候,我们两个都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如果说在很多事情之中,我们碰到非常多的困难,资料的繁琐、出版的受阻、自己研究和同行的隔膜等等,但是从她那里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在她那个年代她所面对的情况,可能比我们还要艰难。和她在一起,虽然看起来我们只是完成了一个项目,但这是让我们不断有力量讨论学术问题的两年。
我去柯鲁克夫妇当年待过的村子里断断续续地住了几个月。过去对于土改的论述一般是由上而下的一个讲述,对于伊莎白而言,是带有社会人类学训练的外国人的见证,对我而言还要找到一种自下而上的理解。革命这个词在村民那里毫无意义,他们怎么理解突然间来的这些人,理解他们所做的事,理解一种不一样的观念;甚至他们自己不理解的时候,他们的后代是否能突然间对于已经发生的变动,有一个追认的理解。这些是我所关心的问题。(李佳怿)
作者:高初
编辑:范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