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阿姆斯特丹,约1958年
记得曾经看过一句话,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comfort zone”,中文或可译为“舒适区”。这种舒适,是因为你安逸地呆在自己熟悉的文化与环境中。很多时候,人们都不愿意走出舒适区,因为这意味着挑战,意味着你将要面对一个未知的世界,意味着极大的勇气。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显然是少数的例外。
在学界,安德森的赫赫大名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本《想象的共同体》,被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奉为圭臬。我第一次阅读这本书,大致是在十年前,记得当时曾被作者的开阔视野与旁征博引所震撼,对里面的核心观点——“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更是印象深刻。从此,便对这位作者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是怎样的人生经历与学术训练,才能让一位学者能够自如地在古今之间穿梭,在欧美大陆与东南亚新兴殖民地之间游走,随意采撷官方与民间的各种材料,构建出如此具有挑战性却又发人深省的论述?
感谢这本《椰壳碗外的人生》,终于为我的困惑揭开了谜底。
正如戴锦华教授在“写在前面”中说的:“捧读它的,也许是那些长久以来热爱着《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的几个代际的学者们,也许是更多的渴望穿过历史的罅隙与裂谷,望向以生命贯穿‘二战’前后的人生与精神理路的同代人、后来者。”最早阅读这本自传,纯粹是因为对安德森人生经历的好奇,但在读完之后,我发现,这并不是一本纯粹意义上的自传,它既是对时代的记录与缩影,亦是对学术研究真诚而深刻的思索。
全书的叙述,大致是按照时间脉络进行的。在前面三章“移动的青春”、“区域研究”、“田野工作”中,安德森讲述了他儿时的回忆、成长的历程、在康奈尔求学时的故事,以及他在印尼、泰国、越南等地的田野研究。第四章“比较的框架”与第五章“跨学科”,记录了他对学术本身的思考。第六章“退休与解放”,多了几分闲适的意味。最后的“跋”,则可被视为全书的总结与升华。
成长与求学:穿越新旧时代
“从地理上讲,我是在为一种四海为家的、比较性的人生观做(无意识的)准备。行将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我的生活足迹已经遍及中国云南、美国加利福利亚和科罗拉多,并在爱尔兰和英格兰独立生活过。我是被爱尔兰父亲、英格兰母亲和越南保姆养育长大的。法语是一种(秘密的)家庭语言;我喜欢拉丁语;我父母图书室里的书籍作者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法国人、俄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和德国人。”
这是安德森对自己童年生活的概括。他将自己称为“边缘人”,说自己过着一种无根的、缺少稳定身份的生活。在很多人看来,这可能是并不美好的回忆,但安德森却赋予了它正面的意义,因为这为他带来了多重依恋,并使他后来能够迅速爱上东南亚的国家与文化。
从成长经历来看,安德森可被视为穿越新旧时代的人。在爱尔兰,他被送进了一所贵格会小学,并在母亲的建议下学习了拉丁语;此后,在英国著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他又接受了良好的古典学训练。安德森写道:“我是在一个旧世界行将终结的时代长大成人的。我把自己享受到的优质旧式教育视为当然,浑然不知我差不多属于最后从中受益的那帮人。”安德森早年所受的教育,使他带有一种浓厚的怀旧情怀,也使他后来始终以一种冷静的眼光看待新时代。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曾把民族主义与“古典的共同体”之间进行对比,认为后者以语言的神圣性为中心,而正是这种神圣性的式微,才为世俗的民族主义提供了机会。这种极富创造力的思考,或也与他早期的古典学与拉丁文训练脱离不了干系。
1958年,在安德森22岁的时候,他来到了美国。这个时候,世界正在二战尚未散去的硝烟中重组,传统的欧洲强国开始衰落,美国则作为新的霸主登上了历史舞台。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化,也影响到了象牙塔中的学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便是“区域研究(area study)”,尤其是东南亚研究在美国的出现。
在安德森看来,这种研究的兴起有两方面原因:首先,传统古典学的地位迅速衰退,关于当代政治和经济的实用研究受到政府的青睐,政府为之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其次,随着冷战大幕的开启,“世界共产主义”的幽灵总是让美国高层感到威胁。对于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整个地区,此前的各个欧洲帝国一直满足于进行内部瓜分,因此,他们仅仅各自关注于自己的殖民地,而美国,则带着支配整个这片区域的野心,将其视为了一个整体。就这样,“东南亚”一词开始稳定而普遍地被使用,安德森就读的康奈尔大学,则成为了从体制上推进东南亚研究的先驱。学生们试图运用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各种学科的范式与方法,再加上必要的语言训练,探索这片未知的世界。
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第一次田野工作的经历是决定性的,一个人再也不会感受到完全相同的震惊、陌生与激动。1961年12月到1964年4月,安德森在印度尼西亚待了两年半的时间。这是他的第一次田野,他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博士论文,也成为了他此后很多思索的起点。从最初的文化震撼与语言上的困难,到游刃有余地展开调查与访谈,再到使自己创造的词汇成为了印尼语的一部分,安德森笔下叙述的田野,是幽默的、生动的,让人忍俊不禁又心向神往的。遗憾的是,他对当地政治的介入,却使他被后来的苏哈托政权驱逐,并整整持续了27年。此后,他不得不将研究兴趣转向泰国(他更偏向于使用它的古名“暹罗”)、菲律宾等地,跨国的研究,迫使他开始思考不同国家的民族主义传统,这些思考,后来也反映在了《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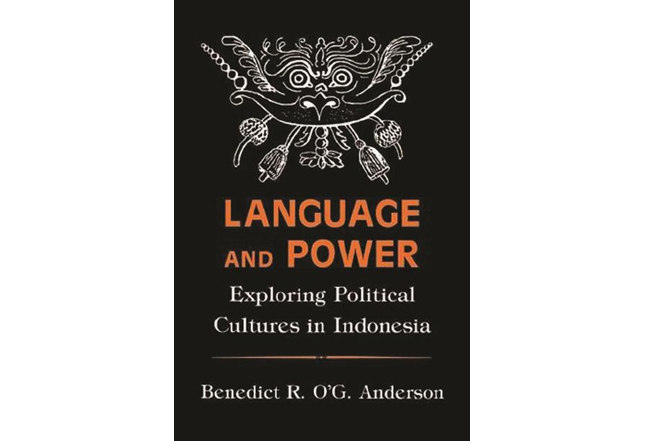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语言与权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0)
比较研究:反思与挑战
田野的经历,无疑带给了安德森巨大的影响。它不仅为他提供了写作的素材,更使他养成了敏锐的洞察与比较的习惯。安德森写道:
“我开始意识到关于田野工作的一些基本的东西:仅仅专注于‘研究项目’是无用的。你必须对一切保持无限好奇,擦亮你的眼睛,锐化你的耳朵,凡事做笔记。这是此类工作的最大恩赐。陌生的经历让你的一切感官比平素敏感得多,你对比较的喜爱变得更深。这就是当你回归日常时,田野工作也非常有用的原因。你已经培养出观察和比较的习惯,它们鼓励或者迫使你开始注意你自己的文化同样是陌生的——倘如你仔细地观察,不停地比较,保持人类学的距离。就我而言,我第一次开始对美国——日常的美国感兴趣。”
对于一名好的人类学家而言,人生无处不是田野。虽然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35年间,安德森一直任教于康奈尔大学,并逐渐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名声,然而,他却从来没有沉浸在声望与名誉之中,而是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审视着周围的环境。
他写道:
“长期以来,美国民族主义的核心神话之一是‘例外论’——认为美国历史、文化和政治生活显然是无可比拟的。美国不像欧洲,不像拉丁美洲,亦绝对不像亚洲。毋庸讳言,这种想象是荒谬的。依据与某些国家的某个时段的相关性,美国完全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比较的,尤其是与欧洲、南美、日本和大英帝国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等)。这一观点的另一原因是其根深蒂固的排外主义。因此,出现了针对在比较政治之内涵括美国政治这一符合逻辑之事的强烈抵制。”
这段话,无疑是尖锐的,也是一针见血的。长期以来,随着美国在世界上霸权地位的奠定,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为之喝彩,为之欢歌,但很少有人敢于质疑它。安德森,算是敢于挑战“皇帝新衣”的极少数人之一。正如他在书中所言,早在印尼做田野的时候,他便开始认识到,看起来疯狂的爪哇人,事实上与西方人一样理性。他们有着一种不同的权力观念,印尼,也有一种与西方人不同,但并不是不可比较的民族主义。
从这个时候开始,比较的念头便始终萦绕在安德森的脑海,而挑战美国乃至西方的“特殊论”,也成为了他立志完成的任务。由此,在让他声名鹊起又饱受批评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他便将那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国家扯在了一起:沙俄与英属印度、匈牙利与泰国和日本、印度尼西亚与瑞士、美国与西班牙……等等。先不论论据如何,单是这些国名并置本身,便已足以激怒高傲的西方人。安德森坦言,在他退休之后,他开始意识到,《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比较过于强调民族主义的单一性,而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在全球思潮中被串联起来的,也会受到庞大的宗教网络、经济与技术力量的影响。这种反思,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比较的视野,只是在比较的过程中,考虑到了更多的要素。在2005年出版的《三面旗帜下:无政府主义和反殖民想象》一书中,他仍旧带领读者在那不勒斯、东京、马尼拉、巴塞罗那、巴黎、里约热内卢、布鲁塞尔、圣彼得堡、伦敦之间来回跳动。这种纵横古今、跨越大洋的纵横捭阖,或是安德森带给学界最大的刺激。
正如安德森自己所言,比较,不是一种方法,或者一种学术技巧,更确切地讲,它是一种话语策略。它要挑战的,恰好是我们平时最习以为常的那些框架与范式。没有人会对日本与中国的比较吃惊,但如果我们把日本与奥地利或者墨西哥放在一起,则可能会让读者猝不及防。再次,对于一个国家内部的长时段纵向比较,也可能会带给我们很多意想之外的故事。例如,想要坚信自己被英格兰人长期压迫的苏格兰人并不想被人提醒,在17世纪的大半时间内,伦敦曾经被苏格兰王朝统治;同样,很多日本人也并不愿意接受他们国家最早的“天皇”可能有部分朝鲜血统这种说法。无论是跨文化的比较,还是纵向的对比,为的都是逼迫人们反思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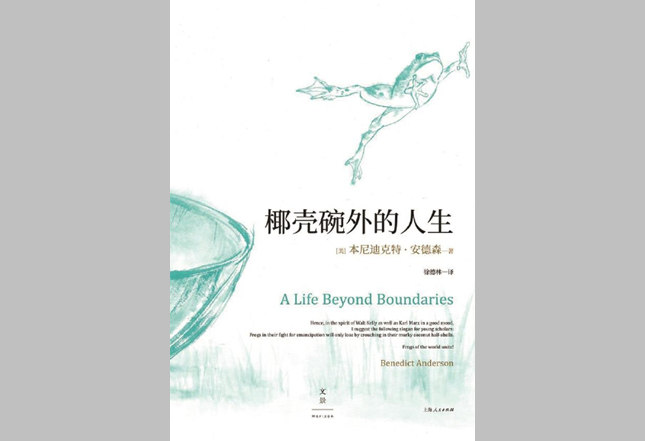
跨越边界:责任与勇气
在反思自己学术生涯的时候,安德森写道,他是一个“好运连连”之人。他出生的时间与地点、他的父母与祖先、他的语言、他的教育、他移民美国,以及他在东南亚的经历,都不是一般的人所能拥有的。然而,如果单纯用“运气”来解释他的成就,显然是不够的。在前文的叙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既像一个天真的孩童,对一切新的事物都带有强烈的好奇心;又是一个严谨的学者,愿意在他感兴趣的事上投注所有的精力。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勇气,这种勇气,既是身体上的,又是智识上的。正如他自己写道:
“运气经常是以意想不到的机会的形式来到我们身边的,当这样的机会一闪而过的时候,你必须非常勇敢或者莽撞地抓住它。对真正具有生产力的学术生命而言,这样的冒险精神在我看来是至关重要的。在印度尼西亚,当有人问你要去哪里而你要么不想告诉他们要么尚未决定的时候,你回答说:‘lagitjajiangin’,意思是‘我在等风’,好像你是一艘帆船,正在驶出港口冲向浩瀚的大海……学者们倘若对自己在一门学科、一个系或者一所大学中的地位感到舒服自在,就会设法既不驶出港口,也不等风。但值得珍视的是等风的准备,以及当风朝你的方向吹来的时候去追风的勇气。”
在这里,回到了笔者在文章最初提到的那个问题:学术领域中,每个学者其实都有自己的“舒适区”,这种舒适区很多时候是由学科划分设定的。安德森回顾了大学里学科布局的形成过程,在他看来,学科的设立与专业化是工业化以后的事情,这种专业化带来了培养的便利,但也造成了许多问题。学生变得对其他专业的知识毫不感兴趣,而他们的训练,也是“职业的”,目的只是为了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能够在被称为“学术工作市场”的地方具有竞争力。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在被教育,只是在被训练,也很难真正从现实出发进行思考。
在安德森看来,区域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专业化的学科设置构成了抗衡。区域研究有很强的现实导向,这就迫使研究者学习多个学科的知识,寻求跨学科的合作。到了20世纪80年代,跨学科研究的观念开始广泛流行,原因也正是在于保守的体制权力无法再满足现实的需要。安德森写道:“以学科为基础的各系往往对维持现状有既定兴趣,但学术研究领域却可能不适应现有系所的边界,因为它们很可能改变其轮廓,以回应发展中的历史形势、社会需求或者研究人员的学术兴趣。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迅速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变化随处可见。于是失配出现,而且不断增强。”事实上,这才正是学术研究应有的路数。任何一个有趣的、有价值的研究,不应当是从学科所设定的理论问题出发,而是应当从现实中不知道答案的问题出发,然后,再从各个学科中寻找可以解释问题的智识工具,最后,用时间来使自己的想法连贯和发展。
显而易见,这样的研究,也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不能再安适地呆在学科为他划定好的藩篱之中,而是要不断突破自己,不断尝试新的东西。甚至,他还可以挑战同行与读者的“舒适区”,用一般学者不会用到的方式进行写作。安德森写到,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他便被善意的老师告知,不要把逸闻趣事和笑话放进正文,要将严肃的学术产品呈现给读者,然而,这并不是他想要的方式。在获得了终身教职之后,安德森终于可以用他自己喜爱的方式进行写作,于是,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我们便看到了他使用文学、诗歌、报纸等不那么“严肃”的材料,也看到了他时而正经时而挖苦的写作风格。显然,这些都没有冲淡这本书的严肃性与价值。
跨越边界,不仅需要相当的勇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名研究者应当承担的责任。在今天这个日新月异变化莫测的时代,任何一项具有现实关怀的社会科学研究,都不可能再仅仅局限于一门学科的界限之中。抛弃自己的“舒适区”,大胆地尝试与跨越,才可能生产出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学术作品。
* * *
事实上,这是一本可读性极强的自传,字里行间,时常流露出安德森的睿智与幽默。究其一生,他始终保有一颗孩童般的心灵,到了退休后,还重拾起了童年与青春期时代的梦想——将文学融入创作,追踪电影制作,写作文学性的政治传记。正是这种从未消逝的好奇,带领他在学术海洋中探索,也使他的作品既有深邃的思考,亦有令人忍俊不禁的顽皮。安德森的一生,是在漂泊中不断思索的一生。
在《学术与政治》一书中,韦伯曾经写道,学术生涯就是一场鲁莽的赌博,只有当一个学者把学术视为天职的时候,才能抵抗所有外界的干扰,享受到其中的快乐。我想,安德森真实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当他在全书最后,号召所有的年轻学者们摆脱束缚,投身于学术之中的时候,也是真诚而鼓舞人心的。也请允许我以此作为结尾:
青蛙们只要不蜷缩在自己阴暗的椰壳碗里,它们的解放之战就不会输。
全世界青蛙联合起来!
作者:刘琪(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文汇理评部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