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讲者杨炼以回顾其作品《谒草堂》的写作背景开始,讲述全球化危机下的诗歌精神。
本版摄影 周文强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曾经也是一名诗人,在对话环节中,他与杨炼共同探讨人类的精神家园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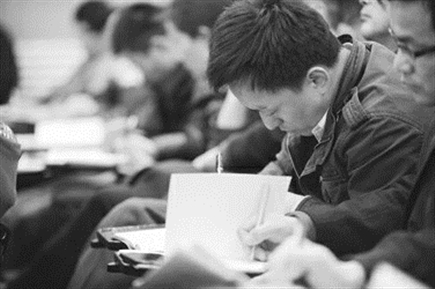
现场认真做笔记的观众。
刚才听了《谒草堂》的朗诵,让我很感动。两年前,我漫步在成都草堂,想着30年间自己的漂泊和杜甫诗歌之间的关系,感觉不只是把自己写进了中国传统,实际通过漂泊经验流进了中国传统。
全球化下共同的新世界、新困境
这个题目让我感觉自己仿佛一个怪圈、一个诗歌的鬼魂,30年间,我在世界上漂泊,而世界也仿佛一个鬼魂,在我和诗之内漂泊。30年来,世界发生了剧变。2012年,我在柏林写了篇题为《新世界》文章,说的就是世界的语境被彻底更新了。但到底“新”在哪里?随着全球化,中国已成了世界的有机部分。与冷战时期相比,世界某种意义上变得更自私、更血腥、更玩世不恭。冷战后曾有过粉红色的梦,梦醒后又碎了,比如“9·11”后,更严酷的现实又在逼近,这实际上是生而复死。今天我们似乎完全被统一,都被商业化、利益化了,这到底是在进化还是退化?还是其实根本原地没动,只不过在不停深化原有的处境呢?
今日世界的共同困境
在2011年伦敦国际诗歌节上,阿拉伯大诗人阿多尼斯和我共同参与了一次诗歌朗诵。他的朗诵题目是《公元前2001年9·11协奏曲》。这一个“公元前”把我们以为只有一次的9·11事件,超越了四千年,推进、深化成为一种人类永远的、不变的处境。
同样,去年我去南非参加国际诗歌节,从开普敦机场到会场的路上,是一望无际的贫民窟。但此时报纸上刊登的却是今日代替了白人种族主义者的黑人政权的腐败。两年前,我去亚美尼亚,参加“为什么阅读和怎么读”的活动。其他的诗人们说“为愉悦而读”、“为知识而读”,我的回答恰恰相反:今天阅读的东西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但是我们没有思想,我们被泡沫化的信息和消息代替了思考的能力。我告诉亚美尼亚的孩子们,一个人一生其实只需要读五本书就够了,关键是有没有能力选出这五本书。更可怕的是,无论南非还是亚美尼亚,可怜的孩子们的一辈子已经过完了,因为他们的头脑里除了未来的工作和工资,并没有别的人生意义。
几年前,挪威有个白人青年提枪扫射其他同龄人。挪威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国家,但那一次的血腥令人震惊。德国媒体在不停地回收冷战的意识形态口号,却没有真正接触到今天人类的真正处境。而美国则一直在奉行着“双重标准”。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今天世界上有一种可怕的词和意义的分裂:我们差不多什么都能说,但是什么都不意味着,这标志着我们这个世界的精神危机,它的危险性远胜于经济危机。因为如果没有思想的能力,那么世界是没有希望和存在的意义的。
共同新世界的新问题
今天的世界确实是新的,也面临着一大串“是什么”的问题。民主是什么?是多数派的游戏吗?历史是什么?是进化的空话和怪圈的现实吗?政治或者政党是什么?是一种公司或经营者,与同一个利益的竞争者吗?文化是什么?等于商业吗?文学艺术是什么?只是这种空洞世界的无聊装饰品吗?自我是什么?难道就是一个空盒子等着装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浪费一生吗?对我来说,新世界其实是一个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空前贫乏的世界。我们知道我们在向哪里去吗?当年艾略特站在伦敦窗前看着暮色说,“没有出路,永远没有”,这不是诗人简单的感叹,我今天也有这个感觉。
个人体验中的诗歌漂流和世界共性
1988年我出国之前,在《还乡》的最后一行写道“所有无人回不去时/回到故乡”。困境实际上是对诗歌本质的一种印证。我的26年漂泊带着一部中国思想的辞典,它对我非常重要。因为就我个人经历来说,每一步的困境实际上都带来灵感,让我反思今天中国的、世界的真正的精神乡愁。在不停加深的困境中,不停获得自己思想的资源。如果说这部辞典有一个源头,那就是屈原和《天问》。
中国思想字典里的逾越和诗意的激情
自有独立诗人的名字开始,中文诗歌有2300多年的历史,第一个有名字者就是屈原。我的这部辞典的源头就是屈原经常用的一个词——流亡。想像一下流和亡,是流向死亡?还是流意味着死亡?还是我自己更喜欢的解释——从死亡开始流动?这就是诗歌。这个词一举奠定了一个诗人的形象,诗人永远是一种逾越内心之墙的越墙者,永远寻找自己的局限性,挑战它、刺激它、逾越它。如果说这个辞典里还有一个语法的话,我要提出“诗意的激情”这个词,这是一种自我追问,它并不简单地面对别人,更多则是挑战自己。这部辞典的地平线是一个不断推远的方向,一直指向追求思想和语言的深度。
反思:我们经验的根基
我们把1980年代称为有精神乡愁的时代,为什么?因为文革的疼痛让我们不仅反省表面的现实,而且反省历史、传统、语言、文化。作为一个诗人,我通过对历史痛苦和当下命运的思考,返回到对汉字的思考,返回到对“五四”以来产生的文化虚无主义的思考,最终它返回到一个词——自觉。汉字动词的非时态性,好像让我们抓住了某种启示,不是去追逐一种表面的时间性,而是追求一种删去了表面时间的幻象以后,对处境的深度认识。我希望抓住的就是剥开了时间幻象之后,使一件作品能够成为经典的那样一种超越时间的性质。经典性,其实是一种思想追求。我在世界上的漂泊,实际上也在印证这种经典性。
经历他国:弥补中国文化的弱项
我在国外写的小组诗《黑暗说》里有一句“另一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我感到中国外国、自我他人其实真的是一个同心圆,真的是在层层加深,层层扩大。我在国外的经历,某种意义上弥补了中国文化最大的弱项——中国文化在过去两千多年里缺少应对真正外来挑战的经验和能力。而欧洲文化在应对外来文化挑战上却有更强的弹性。
应对:独立思考为“体”,古今中外为“用”
在国外的生活每天都是文化挑战和文化应对的经验。这让我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其实这也有关中国人思索了一个世纪的“体用之争”话题。我的结论非常清晰——独立思考为体,古今中外为用。手机和汽车都不是古代留下来的,今天的生活本来就是“古今中外”。关键就在于,如何通过自己的思想能力,把“古今中外”建成一个有建设性的精神存在?同时我们都是一种“诗意的他者”,它强调的不只是一种美感,更是一种主动性,是你主动把自己创造成他者,包括昨天的你的自我,你也仍然是一个他者。
而这正印证了: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有了独立思考为体,古今中外为用,作为“诗意的他者”,诗歌让我们所有人在那儿相遇。
中阿:超越语言的共契
在我遇到阿多尼斯之前,读到的阿拉伯文化作品都是经过欧美翻译的。但是在约旦与阿多尼斯面对面讨论时,我才发现我们的共同处境、共同感受太相似了。其特征就是:内部文化转型的复杂性,被外部世界用意识形态或宗教冲突简单化了。更让人感动的是,他和我有着一种完全不约而同的应对方式——独立思考。每首诗对阿多尼斯和对我都一样,是一种创造性转型。所以在他的《我的孤独是一部花园》中文译本出版时,他请我写序言。我起了《什么是诗歌精神》的题目,看起来虽大,对我们俩来说却是具体无比,因为在我们看来,诗歌正是“从不可能开始”!
中德:共同的现实深度
我现在住在柏林,我与德国诗人之间也有许多交流。我曾与德国诗人萨托留斯坐下来为他《历史》一诗讨论三个小时,我们将它推回母语的真正背景,然后推入中国文化反思和德国战后反思,难道我们只是受害者吗,或我们每个人其实也是迫害者?那首诗写的简直就是我自己的经验,我们都在诗歌中追求现实,因为现实的诗意最有深度。
中英:诗歌互译增加全球化的文化深度
旅居德国之前,有15年我都住在伦敦。对我来说,中英文之间,不单是两个语种之间的比较。如果说汉字通过持续三千年文化转型,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时间象征的话,英语则覆盖面积最广,通过不同文化背景和语境,呈现出丰富的空间性,因而象征了空间。中、英对话也是时、空对话。伦敦生活甫一开始,我就一直在推动中英诗人之间的互译,《大海的第三岸》做了一种精选的呈现。此书出自本雅明所说的“翻译是第三种语言”。还有一种说法说,全球化世界最大的语种就是翻译,尽管这个语种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难免被商业化,但是诗人间的翻译让这个语种增加了深度的向度。如果全球化是大海,文化是一条船,那么诗歌就是船上的压舱石。没有诗歌这一深刻的、专业的“深度”内涵,这条船将是随波逐流的。
中日:近邻的同与不同
我曾以为日本近在咫尺,就必然与我们有许多相似性。但两三年前,当我和日本著名诗人高桥睦郎进行题为“开掘每个人自己的智慧之井”的深度对话时,我才发现地理上的近掩盖了本质性的语言和文化上的远。比如,日语里包有三重因素:汉字、本土的平假名和直接复制西方语言发音的片假名,如同一个拼盘。但汉语如同一只炒锅,把原料放进去,必须炒熟了才能成为中文,但是炒熟了也回不去了。比如电脑也被翻译成计算机,这个词却不能用来写诗。而“电脑”就形象多了。汉语炒锅有自己的深度,但也有封闭性。而日语拼盘有它的敞开,但却缺乏韵律。这也导致了中日的文化命运之异。不过中日诗人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法是相同的:每个文化整体自觉,从思想到创作形式综合古今。
中印:共同的内心之伤
2012年我得到诺尼诺文学奖,而评奖委员会主席是有印度背景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奈保尔,他有一本书《印度:一个受伤的文明》,这本书对印度文化自身的批判、反省及挖掘不亚于鲁迅,我感觉每个中国作家、甚至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给自己写一部《中国:受伤的文明》,只有你懂了伤在哪儿,你才能开始疗伤。
诗意的全球化:国际诗人联合
我认为演讲题目中间的“寻找”这个词是一个永远的共识性的动词。“诗”这个字来自我们血肉和生命的原创之点。它引领学术,因为它是提问者,而学术一直在试图归纳已有的知识来回答这些提问。世界性的漂泊,使我们相遇于诗歌,也通过诗歌找到了人的精神支点。如果用大家都习惯的话来说,就是“全世界提问者,联合起来”。
构建诗歌同心圆:人生-作品-人生
在今天,多元文化已不再是空话,真正现实的情况下,什么是我们的判断标准?还有没有一种判断标准?我认为是有的。回到题目——漂泊的诗歌。我们无须在诗歌的外面再寻找一个精神家园,正如没有哪一辆火车是停在那样一个理想的车站上面。因为诗歌自己就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流亡,这个题目不是一个负面的话题,是绝对正面的话题。
寻找标准的三个层次
寻找标准的过程,对我来说包含三个层次。
第一,全球性的深度对话。全球化使得在中国和在伦敦使用电脑的年轻人没多少区别,实际上这个共同的现实,让我们面对着共同的精神危机。“诗意的激情”是对自身的提问,并不只针对第三世界的人们,西方人也同样如此,因为对他们来说双重标准带来的自相矛盾可能感受更为强烈。而独立思考为主,古今内外为用的这种思维公式也是通用的。
第二,建立判断标准。《天问》是我的源头,但光提到屈原是不够的,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天问”。我的每本诗集,我都称之为思想艺术项目,它必须拥有一种全方位有效的意义。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未必是成正比的。当我读到一部作品,我会在中文语境之内考察它是否有独创性。但同时我也会观察其在世界性的语境中有无不可替代的深度。最终我希望读到的,是在这个全球化的语境中一部具有不可替代的思想和艺术深度的作品,它具有一种个人美学反抗性。
其实我经常提到,如果回顾一战前的历史,可以发现当时一大批精彩的个人,包括哲学、美学、历史、政治等各个领域。他们都是个性化的反抗者,但也是20世纪人类文化最精彩的部分。因此这种深刻的孤独和寂寞,更是深刻的能量的一种证明。
第三,寻找当代杰作。深度的标准对我们来说,首先针对的就是自己。如果自己不能瞄准这样一个标准去思考,那么其实所谓写作很可能是一句空话。30多年的写作,让我学会了一句话——先锋好当,后锋难做。后锋的意思就是后劲、耐力,深度、发展自身的能力。中国诗人很聪明,但是缺少足够的深度和耐力,发展自己的诗人太少了。
每部作品是一个问中之问
对当代杰作的认识,首先必须落实到自己的创作上。
我的《同心圆三部曲》长诗,最后一部题为《叙事诗》。它和前两部长诗构成了一个正反合。它的思想主题,可以概括成两句话:大历史如何纠缠个人生活;个人内心如何构成历史的深度。在语言和形式上,这也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它是一部新古典主义的作品,每个结构和形式都是精心设计的,甚至该直接称作形式主义!我认为,任何文学传统,本质上都是形式主义的传统。这三部长诗花去了我14年的生命,我认为很值。中国抒情诗传统非常伟大,但也有很大的遗憾,因为自从伟大的屈原之后,作为极端思想形式的长诗传统几乎是断绝了。我的长诗,就是想重建这个极端,来构成对散碎、肤浅抒情表达的反思。我当然也写抒情诗,可是我认为仅仅那些还不够,现在这样的生命使用方法是值得的。
回到最根本的意思,在我看来真正的同心圆其实是人生-作品-人生,不停向深处递增和轮回。人生经验通过深刻的反思和艰难的创作,成为作品。作品的结构和形式其实也体现着人生的结构和形式,再派生出新的人生阶段和层次。我过去的30年就是这样一个不停地推进。我的每一部作品开始于我对自己的一个提问,或者说一个问中之问。这就是:我还能给自己提出更深的问题吗?通过这样一个以问号结束的思维方式,在中国思想辞典的每一页上标出页码。这辞词典在手,我确实走遍了世界,没有碰到任何障碍。
最后,我想回答“漂泊的诗歌寻找人类精神家园”这个话题。我突然想起一个托马斯·曼的故事。二战期间,他在过美国海关时海关人员跟他说:“曼先生,您一定很怀念德国文化。”他回答说:“不,我就是德国文化。”而现在,我想说:诗歌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哪儿就是精神家园。
嘉宾对话
在不确定的时代里,漂泊既是寻找也是家园,追问为了成为精神上的强健者
刘擎:我觉得杨炼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诗人,他是一个时代的思考者和知识分子。刚才演讲中对人类的精神状况提问,每过两三分钟所涉及的话题,都是一大群哲学和政治学领域的学者们的研究课题,虽未详细展开,但都触及到了,体现了诗人的高度敏感性。
从1980年代过来的人,对杨炼刚才用的“梦醒时分的状态”一定很有共鸣。本来我们觉得世界应有未来的明确目标,中国不够现代化,我们就赶超“四个现代化”,当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后发现,物质好转了,精神层面却空虚了。西方近代思想史上也有同样的疑惑。前现代的生活中,基督教有上帝这样的权威,中国人有传统的权威;但进入现代社会,尼采提出“上帝死了”,权威受到追问;对中国来说,西方船坚炮利带来的是它文明中的理性追问,一问之后,我们就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所以杨炼触及到的是一个大的时代问题。
杨炼不光有屈原式的追问,还有一些回答。我们需要一个重建生命根基的家园,什么才算家园?杨炼说,在路上就是在家园。如果把精神和理想的家园幻想成一个永久不变的庭院,把根基变成水泥一样,那生活实际上是终结了。杨炼的生命宇宙观里有一个很强的存在主义的生存论观念——人的生命是一个过程,人的本质是不断的生存和显现的,所以寻找本身就是求解,就是一个答案。而漂泊既是寻找又是家园。换句话说,正是由于我们有这样一种对家园的传统想像,我们才会遇到精神危机。杨炼实际上是暗示了这样一种精神,就是不断地成为自己,不断地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强健者,去发问去寻找。
杨炼:我在伦敦发起了私人国际诗歌节,题目就叫《水手之家》。6个语种的诗人同题写成10首诗,然后翻成英文。水手是没有家的,在他寻找之中,让自己变得真正经风历浪。结果非常成功,完全享受到了诗人内部深度的交流。广义而言,每个人都是一个水手,都在寻找一个家。人性何尝不是一直在路上呢?我们老怕失去一种保护,一种支点,一种固定的结论。但事实上人生其实是没有一种固定结论的。刘擎:康德谈启蒙时说,公开大胆的应用的理性,我想这是一种人类未成熟状态;在今天看来,你永远大胆面对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这才是人类的成熟。
诗人对于公共生活的贡献体现在,其诗意的激情包含了对生活的所有层次的追问
刘擎:是。在西方哲学史上,苏格拉底时代就遇到诗歌和哲学的冲突。诗人在个人世界里冒险、寻求,但是对于公共生活、政治生活,诗人经常的作用是“问题化”,把他认为凝固的天经地义的事情打开。比如说发展商业,诗人告诉你,商业使我们变成犬儒主义者,变成利益计算者,变成精神上的爬虫,越来越失去了高贵的精神,所以不应该搞商业。在公共生活中,往往有两种价值:精神世界的价值和政治价值,后者的原则具有强制性,一旦达成,对所有的人都适用。请教杨炼,诗人对于现代的政治共识或者公共生活中缺乏价值的共识,能有什么贡献或看法?
杨炼:很好的问题,因为诗人很容易被理解成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家伙,有时差不多是对的。但是“独立”和“自私”不一样。我认为“独立思考”是诗人参与这个世界的一种根基性的东西,也是我刚才说诗意的激情,自我追问,它包括我们社会生活在内的所有层次。
比如八十年代的精神乡愁,从“伤痕文学”到“寻根文学”,是要深入到对语言的思考,对精神潜意识状况的思考;德国人写的诗作《历史》,不仅追问自己是受害者,也追问自己同是迫害者。对自我追问加深时,也是对自我价值的尊重,实际上是自我开始长大。
这样的追问,内含着政治的价值观,通过创作所体会的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观。比如说社会的不公问题。当我在英国的工人们中间朗诵、演讲时,就会问,为什么中国的劳动力如此廉价,难道仅仅是中国人多吗?
前年我被聘为北京文艺网总监,从2012年开始到2013年7月,和西川、翟永明等一起发起了第一届国际华文诗歌奖。一年内八万多首诗投稿,至少10%以上写得相当精彩,过了所谓诗歌的史前期,就是我们写朦胧诗的那个阶段。其中最重要奖项之一——第一部诗集奖,至少需要写40首,获奖诗人是一位真正的农民工,曾在富士康工作过。他诗歌的主题《纸上还乡》,写被派去安装造楼的安全网时摔了下来的小伙子,他的骨灰被送回家去时的那种安全,毫无空洞、宣泄的语言,极为美好、甚至举重若轻。里面交织着和当代中国深刻的血缘关系。其实在社会的商业化表象下,有一个看不见的诗歌大海,农民工等无声的群体在这个网站发出了声音。据说有2300万农民工在写诗,受到了鼓舞,我们设计了鹿特丹北京文艺网的国际同步诗歌节,三个小时内,现场的点击率达到670万,午夜后点击率上升到了1400万,10天之后则是2500万。
这就是诗歌参与社会的方式。得奖的农民工笔名叫钻石先生,现在开始扬名德国、英国、荷兰,被不断采访,虽然他一家四口仍住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月薪1500元,欠债十万元。这正说明任何人都可以主动参与到诗歌创作之中。
对我而言,所有我作品后面那首真正大诗就是中国,某种意义上也是世界。真正的原版是那个变化中的史诗性的中国,而我的作品只是那个大史诗的一个小小的分支。
在全球化时代,民族也在与外部的遭遇中不断生成自己、辨识自己、发展自己,无法拒绝他者
刘擎:诗歌不仅要发问,在对待公共生活、社会生活当中,诗人会和其他人联合起来一起来做这些事。谈到中国我也很有体会,刚才杨炼的演讲中谈到他的流亡精神,每个人在这个意义上都是流亡者,在现在的世界上。
大家在这个时代里,面对着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一方面要守住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又觉得应该拥抱世界的开放性。杨炼虽然没有完全展开,但暗示的一种态度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似乎没有觉得外部世界对我用汉语写作的人有冲击,反而是给我开放出一个新天地。
杨炼:一个人的精神的存在质量,是随着给自身提问的深度和丰富性而增加的。这是我不期而然获得的东西,我父母都是英语教授,但我在国内拒绝学英语。在海外写作时,没有感到语言上的转折,只有深化和印证,因为中国这部“思想辞典”真的是有质量的。刘擎:“中国的思想辞典”,这个说法特别打动我。实际上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力量对待外部的文明的民族,但在近代以后收缩成封闭、防范和抵御的状态。在我看来,中国所谓文明的复兴是重新能够和世界相容。
杨炼:今天,西方、中国已无法截然分开了。在混淆之中,实际上焦虑、困惑不只是对一个他者的困惑,说实在,现在世界面对着一个非常古怪的,可能从来没出现过的荒诞,贫富差距的产生和扩大让人越来越难以理解,这世界是怎么了?反过来中国知识分子也面临这种问题。我认为,其实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都处在一个大洗牌的状态,我们在一个大的没人面对过的处境面前。
刘擎:我赞成您的看法。这个过程,好像是新的,实际上也不是新的。我们个人是在关系当中的,民族也是如此。民族从来是和外部的交往或者遭遇中来生成自己、辨识自己、发展自己,我称之为“文化的遭遇论”。在晚清、民国初年时,西方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应对、消化、吸纳进来的外部,一个绝对的他者,所以我们有了这么长时间现代化的艰辛历程。到今天,在学习当中,外部慢慢转化成内部,内外的边界从来不是固定的,外部的东西变成了中国自身的构成性的部分,还不是一般的部分。所以我们不能带着外部、内部的泾渭分明的视角。
杨炼:当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我们内部的问题时,正是同心圆在诗歌的提问中不停深化,不停扩大建立独立的精神世界之时。诗歌在这里还是有点用处的。
刘擎:有很大的用处,我完全同意。
提问
○诗歌兴旺需要诗人和读者不断互动
○诗歌的追问和怀疑精神让人受益无穷
○翻译是带着美学要求长出另外的树
○公共精神中需要哲学和诗歌的合作
详见文汇网-活动主页或公众微信
本版据现场活动录音整理。音频请登录文汇微电台(喜马拉雅·听·文汇讲堂)
4月6日下午,著名诗人、2012年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获得者杨炼做客第71期文汇讲堂,作了题为《漂泊的诗歌寻找人类精神家园》的主题讲座,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擎应邀担任对话嘉宾,共同探讨了人类面临的文化困惑和思想危机。演讲过程中穿插着杨炼所作《谒草堂》、《还乡》、《蝴蝶——柏林》、《奶奶的船》等诗歌的朗诵。现场浓烈的诗意氛围,令在座的诗歌爱好者们惊喜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