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把“鳳(凤)凰”写成这轮廓相近的两个字,无疑是把凤、凰分别与雄、雌相配之后的产物。“凰”字本来只写作“皇”,为求两字平衡,突显雌雄对等,才给它加了外框。
凤凰的雄雌之分起于何时,尚难于确切考定,《诗经·大雅·卷阿》的“凤皇于飞”自然难以拿作根据。有的人认为甲骨文里高冠美羽、像凤鸟之形的那个字,本来可能就具有“凤凰”二音,因此早期的凤鸟有无性别区分,很难指实。
春秋时,齐国懿仲欲妻陈敬仲,卜问于神灵,占断时借《卷阿》“凤皇于飞”之语略加敷衍,预言妫陈与姜齐联姻之后子孙蕃庶的大好前景。如相信这时的凤凰已经象征男女的话,则可将此观念上推到东周前期。但这也不见得是一条凿得实的证据,《左传》的有些话不一定真出于春秋人口,尤其是预言、占辞这些本质上属于事后诸葛亮的话,更不可当真。
不过至少《尔雅·释鸟》已经明确记载:“鶠,凤。其雌,皇。”“鶠”字用作凤鸟的意思,有学者发现,在上博简《子羔》所记的简狄传说中尚可见到痕迹,它是故事中遗卵的神鸟,应以解作凤鸟为佳。在无父感生的先妣神话中,先民一定是把此“鶠”作雄鸟看待的 (所以也有人把此类传说中的简狄所吞之“卵”视为男性生殖器的隐喻)。无论如何,如允许下一个稍为模糊的判断,我们基本可以相信,最晚在战国时代,凤凰应该已经分出了性别。


▲洛阳出土的新莽时代壁画墓中见到的凤、凰图像雌雄可辨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洛阳火车站附近发掘的一座新莽时代壁画墓中见到的凤、凰图像,雌雄判然可辨(见王绣、霍宏伟著《洛阳两汉彩画》,122-123页),令人印象深刻。据考古工作者判断,这座墓葬的下葬时代,恰是在新莽的地皇元年至四年之间(公元20-23年)。
王莽年号“天凤”“地皇”相对,汉人把凤凰描摹得如此华美,与择取年号时反映出的凤凰祥瑞崇拜,是合拍的——众所周知,在王莽之前的汉昭帝、宣帝时期,已经有元凤、五凤两个年号用过“凤”字,但用“皇”字入年号的,王莽还是第一个。
今可见的新莽时代木简上的年号“地皇”与《汉书》所记一样,一律作“皇”而决不见“凰”字的写法。把雌性凤鸟“皇”写成“凰”,一般以为是东汉以后的事,《隶辨》著录的东汉麒麟凤凰碑及吴国神凤元年(公元252年) 买冢城砖的“凰”字 (毛远明 《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348页),都是可靠的例子。再往上去,“凰”字的身影便无踪可觅了。
谁都不会想到,汉宣帝时下葬的海昏侯刘贺墓,发现了衣镜上的一篇所谓“赋”,一下子把这个“凰”字上推到公元前一世纪。
发掘者称为“赋”的这篇文字(见胡平生《趣味简帛学》1,45页;《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第64页),体式、功用与两汉时代青铜镜铭韵文基本相当,押阳部韵,形式上虽类似骚体,但实际有点类似打油诗。下面的释文略去述及孔子以下的内容:
新就衣镜兮佳以眀,
质直见请(清)兮政(正)以方。幸得承灵兮奉景光,脩容侍侧兮辟非常。猛兽鸷虫兮守户房,
据两蜚(飞)豦(遽)兮□凶殃,傀伟奇物兮除不详(祥)。右白虎兮左仓(苍)龙,
下有玄鸖(鹤)兮上凤凰。西王母兮东王公,
福憙(熹)所归兮淳恶臧,左右尚之兮日益昌。
飞遽为神兽,见于司马相如《上林赋》(此承孙飙君示知),它与下文所描述的四灵——白虎、苍龙、玄鹤、凤凰,以及西王母、东王公,都见于衣镜描绘。一般常识中,四灵与南方位相当者为朱雀,不少人主张朱雀与凤凰本为不同类型的动物,后来在纬书等文献中逐渐合并混同。即使这种意见正确,现在也可以知这一混并不晚于西汉中后期(前举新莽壁画墓的凤鸟凰鸟,亦是南方主夏之灵)。海昏侯墓发掘整理者判定为“朱雀”与西王母、东王公的镜框上方图案(上方为南),但根据赋文可知,位于中间者其实就是凤凰形象,只是没有区分雌雄二者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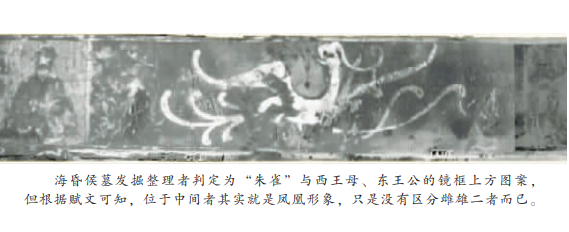
我们所谈的“衣镜赋”的“凰”字,尤可注意者在于,其去掉“皇”的部分,也是“凡”形,与“鳳 (凤)”字的外框亦即声旁“凡”完全相同。最早的“凰”字未尝不可看作从“鳳”形、“皇”声的一个字,现在少了一横的“凰”,反倒应是后来简省的、无理可说的错讹之形。过去的一些字书(如清人铁珊《增广字学举隅》卷二)把“衣镜赋”的这类“凰”字写法判定为非,可谓本末倒置了。
作者:郭永秉 责任编辑:安迪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