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勋
近一个月来,在琼崖森林湖畔的“春明景和”亭前,静读蒋勋先生的美学论著,面对春天的湖光山色,真是一种美的享受。
多年前,浏览朱光潜、宗白华、蔡仪诸公的美学论著,印象似深非深,一知半解。后来读李泽厚那本图文并茂的 《美的历程》,它的照片、图录的可视性,使我得以初窥美学之门。2014年春月客居海南,朋友从江南寄来蒋勋的 《美,看不见的竞争力》《新编传说》《蒋勋说唐诗》三书,读后顿觉耳目一新。蒋勋的美学著作,以其通俗清丽之文,语短意深之笔,为世所称。不尽之意显在浅处,深藏之美彰于俗间,这是蒋勋美论给我的巨大震撼。
美可能是一种信仰
蒋勋说:“美绝对不只是客观的,美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主观。美是主观跟客观的对话。”“常常是因为这个客观的对象,忽然让你感觉你自己主观生命跟它之间有了互动,这时美才发生,美才诞生。”“审美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主观的主体———个人生命,和客观事件之间的复杂对话关系。”(《美,看不见的竞争力》,下简称《美》,第52页)

人们谈美,往往关注达·芬奇的多方面研究和创造。他在500年前就研究声波学、流体力学、解剖学、生理学、医学……研究人类过去不知道未来可能会知道的事情。“人类永远在他要证明的东西和他要相信的东西之间存活。”“我们非常难归类达·芬奇是科学家还是艺术家……美是连接着两者的桥梁。美可能是一种秩序,也可能是一种信仰。”(《美》,第11-13页)
花,是美的象征,古今一贯,中外相通。耶稣传道,见路边开遍百合花,对门徒说它比所罗门王所有宝藏都珍贵。释迦牟尼拈花示众,门徒迦叶微笑,他便把花送给迦叶,说一切道理尽在此中,“心心相印”即典出于此。唐朝处于盛世,崇拜牡丹,以其富贵艳丽,彰显圆满幸福。宋朝受外敌侵扰,专爱冰雪寒天中绽放的梅花,以示顽强不屈。日本的樱花,从盛放到飘落,只短短几天,融欢乐与悲伤于顷刻,是“美和极大悲哀的混合”,成为日本文学乃至民族性格的象征。
人们的潜意识是一个高度压抑的心理现象,需要美来平衡和调节。从生理学角度看,人通过最大努力活出生命极限的部分没有被满足,导致各种精神上的焦虑时时发生。这时美就是一种纾解,在美的世界里,被压抑和限制的潜意识会得到释放。音乐、绘画、戏曲、电影、诗词,会释放人们忍受着的现实压力、痛苦、心酸。“美是现实的互补。它使我们看到我们一生当中没有完成的部分是在美的领域中变成可能完成的。”当然,“你在文学或艺术里喜欢的对象,常常不是你在现实里喜欢的对象”,如生活放荡的卡门,如哀怨多疑的林黛玉,如精神失常的凡·高。(《美》,第60-63页)大概多数人会欣赏他们的艺术形象和作品本身,却难以在现实中喜欢这样的真人,尽管他们值得同情和怜悯。
审美也要有“库存”
人的审美,需要在平常累积很多美的感受经验,是谓“库存”(《美》,第30页)。美也有先天的遗传基因,即天赋。我曾亲眼看到一个不满周岁的幼儿,他打开音乐盒按钮,竟随着悦耳的乐曲节奏,坐在那里晃动身躯,一副欢乐自得的样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家长抚育教诲下,他喜欢唱歌、念诗、写字、绘画、观鱼、看花。看见束发的奶奶,他会让她低头,用小手把束发解开,变成披发。他说,奶奶这样才美,他似乎已经有了自己的审美标准。我以为,这是天赋与现实融合之美。“库存”、基因,人各不同,每个人的审美习惯、判断力、选择力会有差异。而如果判断力、选择力迷乱、失序,美便会消失。蒋勋举例说,一座豪宅装裱客厅,用西班牙牛皮包墙,用意大利水晶灯照明,厚重沙发围着一座苏州园林式的小桥加宝塔,这些东西分开来全是美的好看的,但拼凑在一个客厅里便会不伦不类,不美了。
美不在“多”,“美是你懂得选择。‘少’可能是一个不美的条件限制……‘少’其实在客观上反而有一种协调性和统一性。”江南乡村房舍,自明清以来都是白墙黑瓦,色彩分明,十分漂亮。当你坐车跨过长江行至苏锡常地区,沿途黑白村舍坐落在碧水蓝天之间,心中的震撼与熨帖,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那是一段最美丽最引人注目的旅程。我有几枚闲章,“烟雨江南”、“梦中江南”、“梦里江南云归处”,内中江南乡野的美景,始终驻留在心,挥之不去。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我曾写过不少字幅送给朋友,因为这天地之美无处不在,可能就在你身边,却被人忽略。有美就有丑,也许在身边,也被忽略。上西山看红叶,登长城望边塞,确为一桩美事。但如果是在假日或周末,你看到的只是人山人海,美就会湮没在混乱中,无影无踪。世间时有与美对立的丑,如虚假的编史、拙劣的宣传、空泛的说教……
噪音与躁动夺去宁静稳定,有人便会丧失自我,跟着噪音去躁动。或隐恶溢美,或丑人之美,或美己之丑,不一而足。那时,去看多少画,听多少音乐,看多少美景,其实都不见得有用。
禅宗倡导顿悟,说是人人可以立地成佛,认为每天诵经不如做好眼前的事。近年来,人们在京城,早起必先看天,如果是天蓝云白,风起长林,心会放松,人也舒坦。如果是雾霾肆虐,毒气塞鼻,再好的心情也会被扫得一干二净。长安居大不易,人们于是避往江南;江南霾起,又避往海南。因为那里的空气、阳光和水都好。但是,大家都趋聚海南,人为地过度开发,生态再遭破坏,美就将变为丑,前景实在堪忧。有人说,到那时,人们也许结队往南北极跑,这恐怕不能仅仅当作笑话吧。
盛唐之大美
蒋勋的 《诗像一粒珍珠》,写唐诗与唐文化的渊源,是一篇美文。对初唐、盛唐和晚唐诗界的代表人物,从陈子昂、张若虚、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写到李商隐,以及他们的代表作。全文不足两万字,都是文可醉人,情到迷人。
蒋勋说:“唐代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时代。”陈子昂的这句诗是在说“历史上苍凉时刻里面充满了骄傲,又充满孤独感”(引自 《蒋勋说唐诗》,下简称《唐诗》,第13页)。李白“举杯邀明月……”,连喝酒,都只跟月亮喝,把自己放在一个孤独的巅峰上,跟宇宙对话,更是一种“巨大的自负与巨大的孤独”。蒋勋承续了闻一多、宗白华关于唐诗“宇宙意识”的思想,又有所发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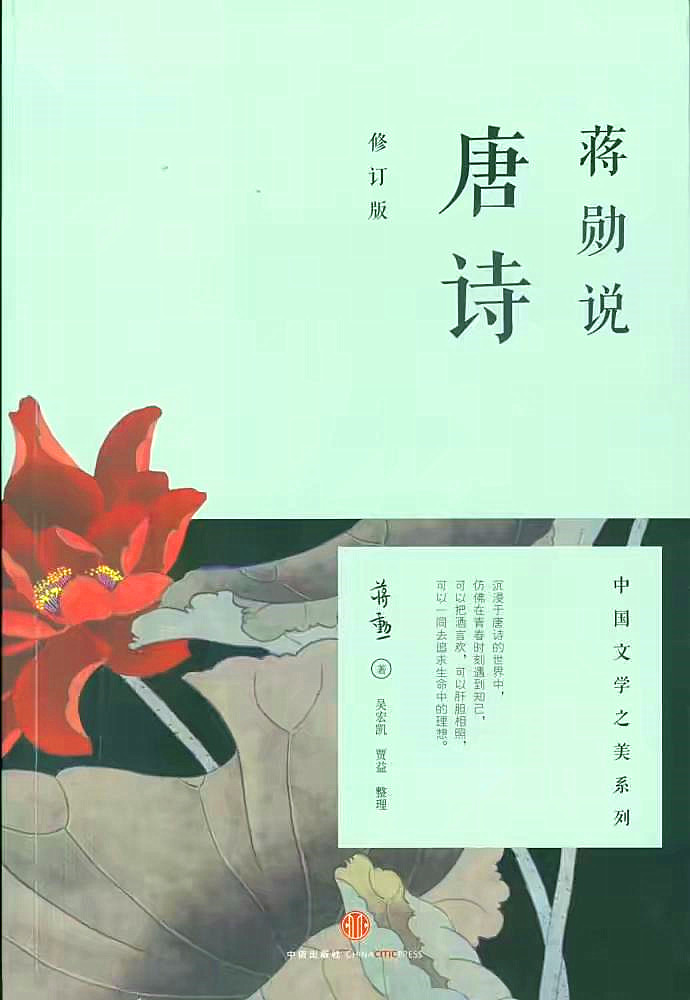
魏晋南北朝后期,“宫体诗”盛行,词藻华丽,不出宫墙,格局萎小。同时又有“田园诗”,如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表达文人逃避现实,梦想回归田园,回到农业社区。那里有温暖,有人情,也有虽然稳定却闭塞的孤独。农业伦理,即儒家伦理,满足于生活简朴、节俭,其道德观视美丽为骚动、不安分,坚守共同性,排斥特殊性。“唐代文学不能与南朝文学一脉相承,而是来自北方。”(《唐诗》第14页)在那里,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只有北方广漠的山川大地,才有如此雄浑阔大的景象。
唐朝皇帝母系来自游牧的鲜卑族,开国时的皇族女性皆非汉族,后来的武则天、杨玉环身体丰腴饱满都是“胡风”。唐都长安是大于今天西安十倍的国际化都市,世界各国人聚居其间,文化混杂交融,“有一种非常特殊的非汉族的美学”(《唐诗》,第17页)。唐代诗歌,从“边塞诗”到“贵游文学”,都属于“浪漫主义文学”,是“因为诗人得到了巨大的解放,不再是活在伦理当中的人,而是活在自然当中的人”。他们“夸耀生命的华美、头上的装饰、身上的丝绸、生命中的一掷千金———‘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这样的句子在农业伦理中不可能出现,这绝对就是‘贵游文学’”。“唐朝是唯一一个觉得可以被大声赞美的时代。”
人们“为唐朝文化的美而震动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其中非常残酷的部分”(《唐诗》,第19页)。李世民跟他哥哥李建成争夺皇位,把建成头颅砍下,提头见父皇李渊逼宫,李渊即刻表示退位做太上皇。武则天也用此法取得皇位。这是“在自然当中跟所有的生命搏斗”,在皇权的争夺上靠的是武力争斗、你死我活的游牧民族的“物竞天择”法则,而非坚守田园耕读、靠本事、善伪装、尚节制、有稳定周期的农业伦理。
蒋勋说:“李白一生当中只希望变成两种生命状态:一个是仙,一个是侠。”先是结交炼丹道士,求仙不成,转而练剑,结交侠士,一掷千金。从四川出来数年间,耗尽30万金。浪迹天涯的生命经验,积变而为宇宙意识,他的诗总是跟日月山川对话。李白被称为“诗仙”,因其“体现了老庄思想的最高完成”;杜甫被颂为“诗圣”,因其“体现了孔孟哲学的最高完成”。两个诗人都达到了那个时代道家、儒家的不同巅峰,分庭抗礼,无分高下。后人对李杜优劣的千年评说,识者斥之为一种“浪费”,似无不可。
从初唐的开拓豪迈,盛唐的灿烂繁华,到“安史之乱”后衰微的晚唐,繁华不再,只剩下对繁华的回忆。晚唐对后来的南唐有直接影响,李商隐与李后主靡丽的诗词,其中的秋日黄花气息,竟是那样相近:“幻灭与眷恋的纠缠”。“盛世将要结束之前的最后挽歌是可以非常华丽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几句诗写的是繁华和幻灭,舍不得是眷恋,舍得是幻灭,人生就是在这两者之间纠缠,如果全部舍了,大概就没有诗了……李商隐就是在唯美的舍得与舍不得之间做着摇摆。”杜甫晚年诗中已有哀伤之感,但那是“对家国的哀伤”,而非李商隐那种“源于个人生命的幻灭”(《唐诗》,第193页)。至于后来南唐李后主的哀伤,则应归于“颓废文学”范畴。
白居易的《长恨歌》同时承载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甜美与悲哀,喜悦与不忍,是历代长诗中美到极致的一首好诗。“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是说生命中有过春风里桃李花盛开时的繁华优裕,也有秋雨中梧桐叶落时的凄苦悲凉。人的生命中曾经繁华过,虽有凄苦也值得,并无遗憾。(参见《美》,第182页)蒋勋用很长的文字解析《长恨歌》,读来叫人心痛。弘一法师临终书写“悲欣交集”四字,悲哀与喜悦交织,其实正是美的混合共同体。有一年春天,我去杭州,在西子湖畔流连忘返,秋天又从京南到西山赏红叶。几年间,有几度这样的优游,于是从脑中迸出这样的短句:
春归何处,碧水江南;秋来何方,红叶香山。
那时,我还没有读到蒋勋的美学论著,今天我在琼崖森林湖畔漫议美学,却碰巧暗合了蒋先生的谠论,这也算是一种心缘吧。
作者:陈铁健
编辑:薛伟平
责任编辑:朱自奋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