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福芸(Dorothea Hosie,1885-1959)
从晚清到民国的大变局,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事件。因此,任何与此相关的描述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谢福芸(Dorothea Hosie,1885-1959)的《名门》(1924)、《中国淑女》(1929)、《崭新中国》(1940)以及《潜龙潭》(1944),正是通过对普通人生活的描写,再现了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感谢沈迦先生组织翻译了这四部书,它们钩沉出了中国近现代史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
作为著名汉学家、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苏慧廉之女的多萝西娅·苏息尔(Dorothea Soothill,1885-1959),她出生于浙江宁波,后随在温州传教的父母在温州长大。谢福芸7岁时回英国读书,后毕业于剑桥大学纽海姆学院。1913年多萝西娅嫁给英国驻华外交官谢立山爵士(1853-1925),后来才有了“谢福芸”这个中文名字。1920年,英国政府重新启用时年已68岁的外交官谢立山,于是他与夫人谢福芸重又开始了在中国的生活。按沈迦的说法,谢福芸写作才华的发现纯属偶然。
1923年,中国大部分地区遭受水灾,谢福芸以外交官夫人的身份动员居住在中国的欧洲人为此次受灾的民众募捐。尽管她精心制作了幻灯片并到处发表演讲,但收效甚微。谢立山最了解妻子的强项,建议她给在中国的英文报纸写文章。出乎意料的是,仅凭借一篇文章,她就募到30英镑的捐赠——这在当时绝对是大数目。其后,作为作家的谢福芸便一发不可收,创作了大量与中国相关的作品。
正如苏慧廉所指出,谢福芸是在“他们之中长大的”,所以她讲述的根本不是别人的故事,而是自己的经历。更何况她在书中“寄托着对中国人深厚的爱与尊重”。她以博大的胸襟和丰富的知识,尽力冲破时空和文化的阻隔,来理解中国人。这是一种同情的理解。

▲谢福芸女士的四部专著:《名门》(左如科译)、《中国淑女》(龚燕灵译)、《崭新中国》(程锦译)和《潜龙潭》(房莹译),东方出版社2018年出版。
中国人是与西方人一样有着同样感情的人
这套书向西方传递的基本观念是:中国人是与西方人一样有着同样感情的人。
此前很多有关中国的书籍,将中国文化描写成一种神秘文化:中国是一切规则的例外(罗素)——中国人的生活完全游离于现代文明之外。但从谢福芸的描写中可以知道,中国并不特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谢福芸列举了一些事例,来说明中国人的一些美德与欧洲人并无区别。在有关节俭方面,她认为中国有很好的美德。除了节俭,中国人善良和纯朴的美德也在谢福芸笔下得以再现。她用一幅老农的照片来诠释何谓“真正的中国”。老人站在长江轮船的甲板上,身穿宽袖、对襟棉袄,双手握在一起放在前面,头戴瓜皮帽,留着山羊胡子,神态放松地微笑着。中国普通人的善良、乐观,给谢福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尽管中国下层民众的特性是敦厚淳朴,但在忍受诸如饥饿等极端状态下,他们也会变得极端。面对很多西方人认为完全不可理喻的“暴徒”行为,谢福芸也给出了理性的解释。
正因为有同情有理解,在展示“当代”中国时,谢福芸给读者描绘的并非只有中国贫穷的一面,也包括当时已取得的成就。在《中国淑女》中,她选取“夜幕下的上海南京路”,给人以摩登时代夜景的感觉。与《名门》所描写的晚清“名门”的传统生活不同,在这本书中,谢福芸希望通过能讲流利英语的上海少妇宋太太,展现一个现代的中国。
谢福芸既不赞成对中国的一味贬低,也反对吹嘘美化中国的做法。谢福芸对中国的“同情理解”,源于她与中国的关系以及情谊。她出生在中国,周围到处是中国朋友。后来她嫁给驻华外交官,同样一直与中国人打交道。书中处处流露出她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在《中国淑女》中,谈到要给中国一家报纸写公开信时,谢福芸写道:“这封公开信就叫作‘致中国,我的养母’。”中国已不是她的研究对象,他们俨然超越了主客体的关系,发展成了具有感情基础的“亲戚”关系。
由于亲历了晚清到民国的变化,谢福芸有着与一般西方人不同的对中国的理解:
“中国”这个词就像“英联邦”一样,包含了众多民族,从北方的蒙古族、满族到南方靠近印度支那的广州人,还有纯正的中国人——他们称自己为 “汉人”。
(《名门》,第31页)
我认为,谢福芸的这个比喻非常形象、恰当。大部分英语读者也会因为这样一个说明,对中国产生更加合理的理解。她同时也跟其他外国人一样惊讶于中国人居然会有共同的身份认同,尽管他们来自众多不同的民族:
不管面对怎样的压力,中国始终是中国,是一个同源同祖的整体,这时常会使外国人觉得这是一个奇迹。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个国家始终立足于两大根基:一个是任劳任怨的广大民众,另一个就是个人服从家族的从属关系。
传统与现代的断裂
在谢福芸看来,传统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其审美。1911年辛亥革命后,她最担心的是传统审美的丧失。因此在她的书中,很多照片显示了传统中国之美。一幅静谧的江南住宅图:一位绅士家中漂亮的花格墙,正对着运河对面普通民居的空白墙面。(《名门》第53页)除了住宅建筑,还有中国园林:在花园的茶室中享受下午的美好时光。夏季,桥下池塘里的荷花和莲花竞相开放。南方的老宅子:依山傍水而建,因为相信山、水能为居住的人带来好运气。
从字里行间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谢福芸所担心的是这些中国文化的独有之处——审美、雍容大雅的生活方式等会不复存在。
苏慧廉是著名汉学家,曾将《妙法莲华经》译成英文,并与何乐益共同编写了《中国佛教术语词典》,其中国佛学造诣极深。耳濡目染之下,谢福芸同样谙熟中国佛教典故。她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的重要遗产,可惜被今天的中国人遗忘了,从而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断裂。
谢福芸的理想曾是“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我倒是愿意把剑桥给搬到中国,让它在那里开枝散叶……如果慈禧太后能对科学真理和现代历史有哪怕一点点最肤浅的认识,她还会支持义和团掀起暴动吗?”对于中国来讲,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断裂需要通过教育来予以克服。而“五四运动”所倡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得以扎根于中国大地。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东部地区造成了严重创伤,所有建设成果几近惨遭毁灭。1936年7月谢福芸到达香港时,她如是写道:“我的心跳开始加速:十年未曾踏上中国土地了。三年前父亲离世,三年来我唯一做的就是平复心境,适应未知的新生活。当然,中国漫长的苦难也终于结束了!”实际上这只是战争来临前的暂时平静,中国的新苦难,马上又要开始。尽管《崭新中国》第一版于1938年就已出版,但在1940年修订版出版时,谢福芸在很多篇章结尾处增添了最新的内容。她在书的献词中写道:“满怀挚爱与崇敬,将此书献给今日勇敢的中国”以及“1940年,此书得成,实因感佩中国为争取自由而战斗不辍之精神,并对其最终胜利抱有无比坚定之信心”。这两句平实的文字,显示了谢福芸对中国的深情厚谊以及中国必胜的信心。
重要的历史事件还包括对西安事变的描写。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时,谢福芸正在从宜昌到武汉的船上。她的英国房东告诉了她这个“坏消息”。
“天啊,可怜的中国!”我呻吟起来,彻底惊呆了,不得不靠在扶手上,“中国才刚刚站起来呀!”我知道这条消息将带给中国什么样的灾难,将带给那些艰苦奋斗逐渐把国家团结在一起并最终取得胜利的人什么样的灾难。从广州到北京,从山东到四川,中国人也将问自己,伺机等待的仇敌会不会利用这个群龙无首的机会发起侵略?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在中国的普通英国人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这是与当时整个国际社会对待这一事变的态度是一致的。
一部关于20世纪中国大变局的非虚构杰作
以前曾有人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如果一个人在某个地方待过几天,可以写一本书;如果一个人在某个地方待上几个月,能写一篇文章;如果一个人在某个地方待上几年,就只能写几行字了。在《中国淑女》的“作者前言”中,当“励诚”鼓励谢福芸在写完《名门》后再写一本有关中国的书时,谢福芸答道:“岂敢呀!我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所知道的那一点点东西早已经写进上一本书里了。”谢福芸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如果中国人、印度人、美国人或日本人只是来欧洲转一圈,然后写一本关于炖肉汤的书!这样的出版物简直粗鲁无知、毫无人性,显然不足以全面展示我们的文明、文明的男人和女人。”这也是为什么谢福芸这四部著作特别值得一读的原因。
作为女性作家,谢福芸以史诗般的语言,将20世纪中国大变局呈现在读者面前。这四部有关中国的作品,尽管做了一些必要的改动:“比如姓名、地名和官阶,并非和实际生活中完全一致。”但这四部书都属于“非虚构写作”,通过这样的处理,可能更加真实地展现这些人物的“精神史”。
阅读这四部著作,我们能感受到谢福芸与中国社会的真正互动。诸如谢福芸一样在中国生活过多年的英国作家,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他们将西方近代以来的知识、信仰传到中国,谢福芸本人建学校,在父亲的医院帮忙,参与中英庚款委员会的工作等等;另一方面他们也将中国文化的传统介绍到西方世界。这四部作品中除了介绍一些中国历史、文化知识,还有大量的中国式审美,这些如果没有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经验以及与当时一定社会阶层的广泛接触,是不可能洞悉的。
谢福芸的四部书中,三部所涉及的是文献式的摄影照片,最主要的是风景照片和人物照片。她舍弃了那些所谓异国情调的照片或猎奇式的“人种摄影”,它们自19世纪末以来由于商业原因而在西方大为流行,正是这些照片造成了欧洲人对中国的轻蔑态度。谢福芸书中的照片,仅有为数极少的几种类型化样式照片,其中大部分人像所显示的是非常有特点的单独的人或人群。她自己拍摄的照片中,有一些是非常成功的,显示出一流的艺术品质。这些照片同时也传递了作者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热爱。她在其中所寻求的,是她熟悉的且与自己相关的事物。在谢福芸那里,陌生性不是通过煽情式地强调中国与欧洲近代文明的不同,而是通过常态与共同性表现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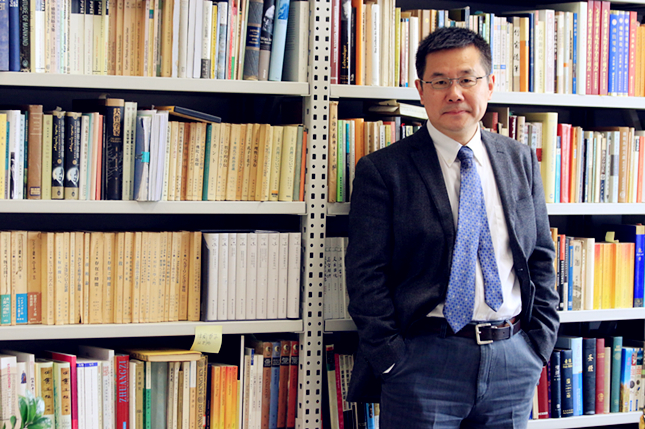
▲本文作者李雪涛近影
作者:李雪涛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薛伟平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