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拉玛依的艾青雕像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艾青离世已经23年了,但35年前我与他谈诗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我崇拜上了艾青
虽然同样是“五四”以来的著名诗人,但在我们的青少年时代,可以读到郭沫若的诗,却读不到艾青的诗。当然,郭沫若的《女神》确曾使我激情燃烧,热血澎湃,由衷喜欢。后来我听说艾青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难以读到他的作品,觉得很遗憾,便四处寻找。即使只在一些陈旧的刊物上找到只言片语,我也如获至宝,抄录下来。
时值动乱的岁月,虽然焚烧了很多书,但也有不少书从封存的图书馆里流散出来,有时也会莫名其妙地流传到我们这些初中生手中。分明记得,1967年初,我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本《艾青诗选》,青绿色封面,内封后页还有他的肖像照和《自序》。我一下就被这本书里面的诗吸引住了,犹如醍醐灌顶,《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透明的夜》《手推车》《北方》《乞丐》《向太阳》《我爱这土地》《他死在第二次》等诗,都深深打动了我,令我爱不释手。有一次在理发店排队时我也聚精会神地在读他的诗,直到理发师大声叫我,才回过神来。
从此,我崇拜上了艾青。我一边读他的诗,一边抄录,一边介绍给别人。
后来,我从报纸上得知艾青获得了平反,出版了诗集《归来的歌》,很为他感到高兴。当时我正撰写《现代诗四十家风格论》,其中也包括艾青的诗,很想有机会去北京时能拜访他,谈谈我对他的诗的看法。
1984年10月,我去北京出差,住在崇文门东交民巷的中国社科院招待所,而艾青家就住在北京站附近的丰收胡同,离得很近。于是我便在一个下午去拜访他,但他恰巧不在,从他儿子口中得知,复出后的艾青很忙,活动也很多。隔了两天,我再次登门拜访,一进四合院的大门,只见艾青正从院中走过,我忍不住一个大招手,高喊:“艾青同志!”他一怔,止步回头一看,是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我赶紧上前说明身份和来意(也许家人已告诉了他),他才释然,与我握手,引我进入客厅。
那年艾青74岁,与我想象中的模样差不多,大脑袋,大脸庞,大眼睛,很有气派,身板硬朗,穿一身藏青色中山装,朴素大方。客厅中央挂着一幅楹联,是王维的诗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想这可能是他所喜欢的。字很大,也很有气势,不知何人所写。楹联前面放着一大桌,两边放着椅子,我们就分坐在桌边闲聊起来。
我当时根本就顾不得什么寒暄,见了艾青就想把自己多年的感想倾诉出来,也非常坦率地说出了对他诗的喜欢,随后话锋一转,说:“由于您书赠给一位诗友的八个字是‘朴素、单纯、集中、明快’,因而有些人用这八个字来概括您整个诗歌创作的风格和特点,这恐怕是欠妥的,至少我是不大同意的。”
“噢?”艾青前面一直在安静地听,这时却发出了声音,看看我,鼓励道:“你说说看。”
“好吧。”我直截了当地说,“这八个字,可以说是您经过多年的创作实践的心得体会,在晚年对诗所得出的一个基本要求。如用这八个字概括您晚年的诗作《花样滑冰》等,是对的,确实显示了这些特色。但如要包括您早期的诗作,则不确切。您早年的诗歌朴素和单纯是有的,集中和明快则谈不上,非但不明快,而且可以说是非常阴暗,节奏缓慢。”好在我对他的诗比较熟悉,便一边背诵一边作为例子说明:“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像这样的句子怎么能说明快呢?可以说,您早年写的《手推车》《北方》《乞丐》等一系列诗,甚至包括《向太阳》等,节奏都是缓慢的。只有到您复出以后所写的《平衡木》等,才称得上是集中、明快……”
我只顾把心中的看法说出来,根本就没注意到艾青的想法和表情。没想到等我一气说完,他立刻说:“对!你说得很有道理。”
能得到他的认同,我高兴极了,连声说:“谢谢艾青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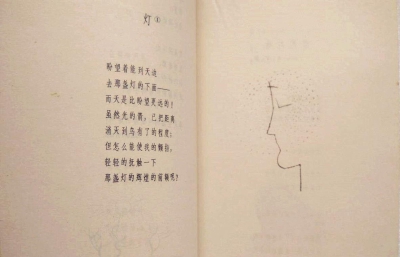
听艾青盛赞戴望舒
艾青的妻子高瑛很热情,为我们倒茶,有时也会坐在旁边听一会儿,有时则起身去做其它事,尽量不打扰我们的谈话。不过,艾青与卞之琳、冯至等人一样,似乎都不太习惯谈论自己的作品,但当我们谈起戴望舒,他的话明显多了起来。
“你看,戴望舒的诗写得多好哇!”他用手比划着,“他写过《灾难的岁月》《我的记忆》《狱中题壁》,很爱国,特别是他的《我用残损的手掌》……”他伸出手掌一边比划,一边背诵起诗里的句子:“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他继续向我比划着,偶尔作一点讲解,主要还是赞美:“你看,这些句子写得多好!还有‘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
我没想到他对戴望舒的诗竟如此熟悉,便说:“你们都到法国去留学或旅学过,都受过法国象征派诗的影响,诗中都有象征性。只是所受影响的诗人不一样,戴望舒先受到魏尔伦后受到耶麦的影响,而您则主要是受阿波里奈尔的影响。”
艾青并没有回应我的话,只是继续赞美戴望舒的诗,仿佛沉浸其中,最后又说:“所以,从他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这些诗来看,这才是大手笔!大诗人!”
后来我读到一本《望舒的诗》,内选戴望舒的诗数十首,编选者正是艾青。怪不得他对戴望舒的诗这样熟悉!老话说:“同行是冤家。”艾青却不是。同样写诗,译诗,学法国象征诗,艾青却盛赞戴望舒,从中正可以看出他的胸襟。
随后,我问艾青他的近况,也跟他谈起了他近些年来的新作。他说:“他们让我看电影,有各种各样的专题和镜头。”他又用手比划起来:“有蛇,有山水,还有其他内容,希望我能产生灵感,再写一些诗。”
这时高瑛又进来了,我看看手表,已足足谈了两个多小时,便起身告辞。高瑛忙解释:“我不是来催你的,你再坐坐,我看你们谈得挺好的。”我说:“不行,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你们也该休息一下了。”艾青见我执意要走,便叫高瑛去取一本书来。不一会儿,高瑛拿来了一本《艾青短诗选》,艾青在扉页写上我的名字,赠送给了我。
客厅里挂着一幅诗人合影照,我起身时稍稍看了一下,说里面有些人曾见过。高瑛指着其中的卞之琳说:“这个人好。”又指着另一位说:“这个人不好。”我望了下艾青,他也在看,却不吭声。
走出客厅时,我忽然对艾青说:“舒婷的诗现在影响很大,很多人都喜欢。”他站住了:“你说的是那个小女孩吗?”我点点头,说:“是的。和我差不多大。”他似乎想起来了:“你说的是她呀,写爱情诗的!她到我家来过,叫我艾伯伯,就在这个院子里。”他指着自己的四合院。我认真地说:“她不仅写爱情诗,也写其他诗,有些诗很深刻,很有分量。”“哦”他将信将疑地望着我:“是吗?”
我再次点点头,并请他留步,与他握手告别,高瑛则一直送我到大门口。我已走出20多米了,没想到背后忽然传来高瑛的声音:“下次再来玩啊!”原来她一直在目送我。我赶紧回转身,对站在门口的她一个大招手,大声说:“一定来!”
直到1992年初秋,我才再次去艾青家,那时他已搬到东四的一个四合院。没想到他不在家,孙辈说人民大会堂正要开他的研讨会,忙得很。我不便打扰,便匆匆离去。
四年后,艾青去世,终年86岁。

2003年,纪念冯雪峰100周年诞辰之际,我在参观冯雪峰故居的同时,也顺道参观了陈望道、吴晗和艾青的故居。其中艾青的故居规模最大,高大的白色围墙内,旧宅、院落、草木、石凳一应俱全,院内人丁兴旺,不禁使我想起了他在《我的父亲》一诗中的有些描写。故居附近还有大堰河的墓和碑,这又使我想起他所写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于是我在墓碑前拍了张照。
30多年以后,有一次与《诗刊》社的老编辑朱先树谈起拜访艾青的事,他说:“艾青平时不太爱说话,能与你谈两个多小时,已经很不错啦!”又说:“别看艾青平时不吭声,有时一发话挺厉害的,有的人还真受不了。”
我也曾听辛笛、雁翼、周良沛等人谈起过与艾青接触与交往的印象,各人的感受都不相同。而作为后辈,我对艾青始终是崇敬和景仰的,写下这些文字,也是对他的一种真诚怀念,献上自己的一瓣心香。
作者:孙琴安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周怡倩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