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是在上个世纪的某一天,在华东师大科学会堂,李欧梵开讲座,有关新著《上海摩登》的话题,学子云集的景象就像一部大片。昨天(16日)上午,这位思想史研究、现代文学研究、上海研究大家在上海师范大学再次引发现象级关注。在这场“与20世纪同行:现代文学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的上午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李欧梵以半小时视频访谈方式“出席”:清瘦干练,谈笑风生,幽默睿智。现场的同龄老友批评家李陀、当代文学研究专家洪子诚,上半年在香港中文大学驻校的作家王安忆都感慨:李欧梵依然当年。作家、学者毛尖则评价虽是里程碑学者,却无架子,十分“可爱”。记者和在场的四五百位学子一同聆听了李欧梵接受弟子、同事张历君的学术访谈,谈及在哈佛如何走上研究鲁迅之路,缘何和曹聚仁交流,既披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往事,也谈及了他一贯坚持的治学,与主题中的“同行”意蕴呼应,李欧梵及弟子研究20世纪的治学方向——“跨文化现代性”,即致力强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考的复杂性,以及中国现代性的跨文化和混杂特质,依然是当下中国学术界所需。

哈佛大学东亚系、香港中文大学冼为坚中国文化讲座教授李欧梵以视频方式讲述《世纪经验、生命体验与思想机缘——我和“20世纪的中国文学”》
费正清同意我去剑桥找灵感写徐志摩研究
1961年,从台大外语系毕业后,李欧梵先在芝加哥大学修国际关系,1969年进入哈佛东亚语言系跟随费正清攻读中国思想史,著名汉学家史华慈正式指导他的博士论文。如何从思想史研究扩展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则是史华慈的“放养”,二则遇到特殊机缘。
李欧梵披露,当时,大家在费正清中心学习,但他对历史学家费正清重要的课比如《清史》《外交史》都不太有兴趣,所以没有选。中心主任费正清指导学生:每个人要选一个人,去做他的传记。在台大学习时李欧梵就和同学白先勇等创办过《现代文学》杂志,推动台湾文坛潮流。李欧梵当时非常膜拜徐志摩,就决定研究这位诗人、作家。有一天,李欧梵和费正清进行了交流。“我觉得做一位现代作家研究太单一,我要做6到7人,反应一代文人”。费正清同意了;他又说,“我想去剑桥,去找找徐志摩留学的灵感。”费正清也表示支持。
1970年代,英美的传记都做得非常规矩,侧重写传主很有人格魅力的一面。一天,李欧梵在哈佛燕京的图书馆看到民国时出版的书籍《文坛登龙术》,翻了几页觉得非常有趣,其中的信息来源非常广泛。视频中,李欧梵指出,“它传递了一种新的文学概念。我开始搜集民国的报纸,即便是小报也不在乎,上面的信息和主流的说法一起就构成文化角度。”接受访谈中,李欧梵告诉现场学子:任何历史题目都要有其背景,而跨界研究又会带来新的视角。他喜欢跨界。这样的寻找过程让他顿悟:原来,历史就是文化史,要在历史的长镜中追寻细节。

视频访谈者、香港中文大学学者张历君
做传记时,并没有理论先行的概念
就这样,他做了徐志摩的研究,又扩展到郁达夫,此后又聚焦鲁迅,并写了《<鲁迅内传>的商榷和探讨》和《铁屋中的呐喊》。四十年过去,再看当时的研究方法,有着相当超前的新理论支撑。张历君提及,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曹聚仁谈鲁迅的研究方法时,曾提到三位传记王:路德维希、莫洛亚、伍尔夫圈子里的斯特拉奇,他们提倡写“新传记”,即传记作者和传主平起平坐。其实这是1920年代英美文学圈就一直提倡的。问及是否受此影响,李欧梵回忆,自己写《鲁迅内传》时,只知道莫洛亚和伍尔夫。在视频中,李欧梵笑着说,《鲁迅内传》现在看来,也的确符合这些理论。但他声明:自己做研究,一贯不受理论影响。他年轻时就非常喜欢理论,但反对理论挂帅。在其他场合的演讲中,李欧梵曾介绍过自己在1960年代接受的理论熏陶:非常喜爱乔治·斯坦纳的《语言与沉默》,耶鲁的韦勒克和哈佛的哈里·列文,哥伦比亚大学的莱昂内尔·特里林和雅克·巴赞,当然还有稍后的苏珊·桑塔格,普林斯顿的埃德蒙·威尔逊,虽然对著作内容一知半解,他非常欣赏将批评和理论合二为一。李欧梵认为,好的理论本身就值得细读,像一本文学名著一样;坏的理论往往是二手的演绎;随意套用理论,反而对理论不够尊敬。视频中他说,“我当时并没有刻意去寻找一种时髦的理论,不像也斯等香港作家那样自觉。”李欧梵在访谈尾声强调,“研究著作和文学作品一样,一旦问世,应该和作者区分开来独立评价。”
回顾自己的研究方法,李欧梵总结受了几个传统的影响,一是后期浪漫主义,有点象征意味,二是早期现代主义,三是停留在两者之间的现实主义。李欧梵鼓励后学:“要冲破传统旧路,力求文化史和历史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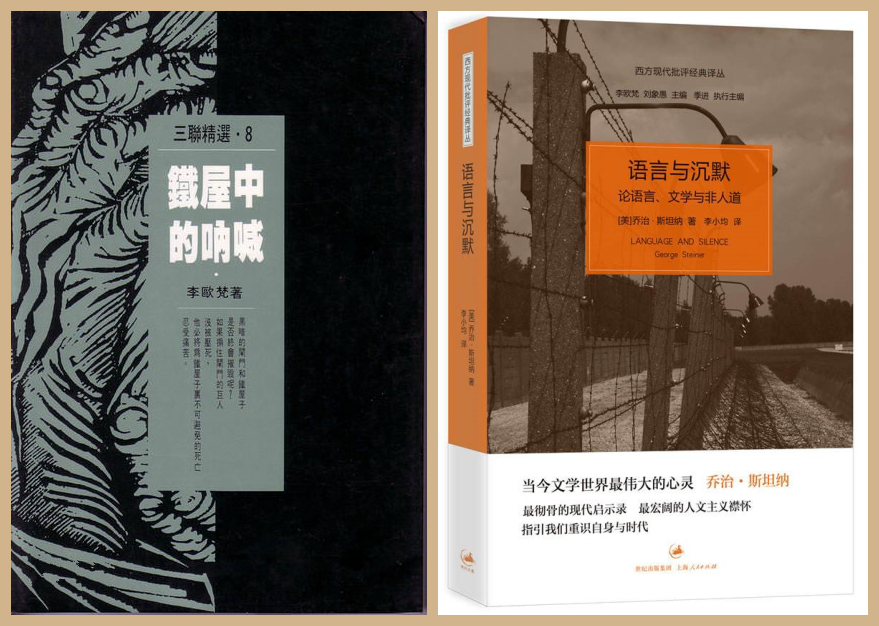
李欧梵著作《铁屋中呐喊》及乔治·斯坦纳的《语言与沉默》
2004年,李欧梵从哈佛提前退休,遂扎根香港中文大学。从研究生开始即受其亲炙、留校一同治学的张历君向记者介绍,灵活运用多种不同学科领域知识,进行跨学科的人文研究是当前他们的方向,他们尝试解拆“左/右,本土/全球,文学书写/哲学思考,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等主流的二元对立思维,这种“跨文化现代性”方法也挑战既有的学科领域划分的专业分工模式。
在哈佛,受埃里克森鼓励研究现代文学大师鲁迅
《铁屋中的呐喊》确立了李欧梵鲁迅研究的地位。如何从徐志摩、郁达夫转到鲁迅?李欧梵披露了一段值得怀念的往事。
1969年,哈佛医学院来了位著名的新精神分析派代表人物埃里克森(E.H.Eriskson,1902-1994),他担任了人类发展学教授,讲授“人类生命周期”课程,全校研究生都可以选。埃里克森师从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但是,他不同意将所有原因归结为童年,所以,改良了弗洛伊德的方法,将心理研究的焦点放在人生发展不同阶段所产生的“认同危机”问题上,并著有《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中央编译局出版,2015年)一书。同时,埃里克森也写了两本传记《青年路德》和《甘地的真理》。李欧梵回忆,当时,杜维明和自己都选了他的课,埃里克森要求选课者在课上分享研究心得,杜维明博士论文做王阳明研究,他就讲青年王阳明(后来成书为《青年王阳明》)。李欧梵想讲郁达夫,埃里克森不知道郁达夫,但他知道鲁迅,就建议李欧梵和自己研究奠基性人物一样,要讲鲁迅这位中国现代文学之父。李欧梵在台湾时,并未读过鲁迅,到了芝加哥才开始接触。在哈佛,他从埃里克森的甘地研究中得到启发,借他的心理研究方法解读鲁迅的《父亲的病》。由此正式走上了研究鲁迅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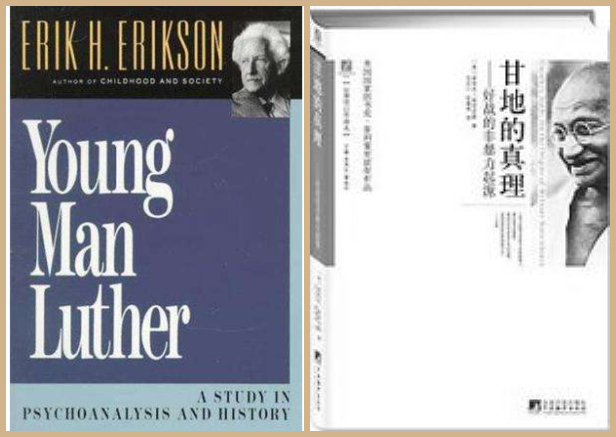
埃里克森也两本传记《青年路德》和《甘地的真理》
和香港、日本同行切磋,找到自己的“鲁迅传”风格
1970年,李欧梵去香港访学,在《明报月刊》上发表《<鲁迅内传>的商榷和探讨》,风格受了埃里克森的影响,面目一新,编辑非常喜欢,分3-4篇全部发完。于是,就迎来了和曹聚仁的见面。作为记者和学者的曹聚仁在1950年代写了《鲁迅评传》引发轰动,他以平视的目光写了同时代人鲁迅,成为鲁迅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1970年,曹聚仁在香港和大陆两地工作。“与曹聚仁见面是偶然,罗孚请客,一桌人吃饭,酒过三巡,曹聚仁问我,你知道鲁迅写过另类的诗歌给许广平吗?”
李欧梵在香港看了更多的传记资料,周作人的资料最有用。“香港‘华洋混杂’,是各类思想聚集地,自己如鱼得水,也觉得非常幸运。”
除了香港受到的思想碰撞外,李欧梵兼收并蓄。夏济安是李欧梵在台湾大学外语系的老师,写了《黑暗的闸门》。李欧梵和他一样喜欢《野草》,对鲁迅的研究直接受他影响,夏济安剖析了鲁迅文艺上的黑暗面,李欧梵则勾勒鲁迅心理的暗面。回到哈佛,李欧梵写了一篇长文《鲁迅和他的遗产》。当时,美国有个学者已经做了十多年的鲁迅研究,李欧梵称“自己不好意思占领他的研究领域,因此以发文章的形式呈现。”
1981年,李欧梵在美国组织了同名的鲁迅研究会议,请了世界各地研究鲁迅的学者参加,从日本学者丸山昇那里知道了日本的鲁迅研究现状,并第一次听到了竹内好这个名字。吸收了各家之长,李欧梵在视频里告诉大家,自己最初想用埃里克森的精神分析法写《鲁迅内传》,但后来发现这种方法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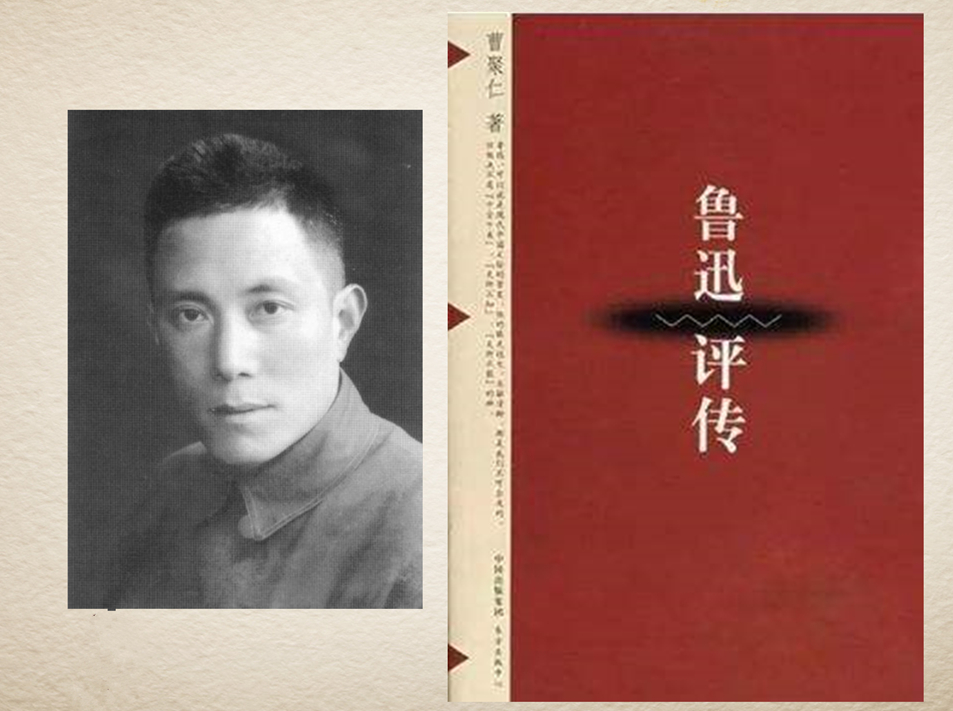
曹聚仁在1950年代写了《鲁迅评传》引发轰动
近年来回到晚清和现代文学的研究
在披露往事后,李欧梵又回答张历君提问,向学子们介绍了自己的现代主义阅读兴趣。
他在台湾大学读书时就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兴趣,譬如福克纳、海明威和卡夫卡,罗曼·罗兰作品,在中学时已经阅读,茨威格是近年来才关注,因为发现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是对茨威格的致敬。在台大的同学王文兴经常会看一些现代主义的作品,自己也迷迷糊糊跟着他看。他自己对德、奥、匈等国文化的关注,都受卡尔·休斯克这位学者的影响,休斯克写了《世纪末的维也纳》。
谈及当下的研究,李欧梵称近年来自己又回到晚清和现代文学这两个领域。其实,李欧梵很早就研究过林琴南,但没有成书。最早研究梁启超的文学观时,他发现光是一种文学观是不够的,所以,就开始看晚清时期的翻译作品,发现都是维多利亚的通俗文学,其中类型小说较多。视频最后,李欧梵哈哈一笑,“但是,我可能无法完成如此巨大的工作了。因为,我已经到了当年曹聚仁的年龄——老了。”

由上海市高峰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主办的“与20世纪同行:现代文学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上午场邀请了众多名家,从左至右为王安忆、洪子诚、李陀、陈思和、蔡翔
现场因为时间关系,视频并没有放完,张历君事后向记者补充,在他访谈末尾,“他(李欧梵)声明自己不是大师。”(完)
作者:李念
现场拍摄:李念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李念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