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童世骏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本报记者 杨逸淇摄
【编者按】
如果说,面对疫情,积极乐观的情绪、健康向上的心态、理性平衡的心理,是一种强大的免疫力,那么,良好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心态,更是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的稳压器。
当下,如何加强社会心理疏导,做好人文关怀,及时平复不良情绪,培育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是社会心理重建的重要内容。为此,本报记者把“话筒”递给了一批人文学者,请他们面向大众,普及知识,分享观点,从不同的学科视野,探究当前社会怎么走出“压力迷失”“矛盾迷失”,用思想的力量照亮未来,用理性的阳光驱散阴影,共同把社会心理建设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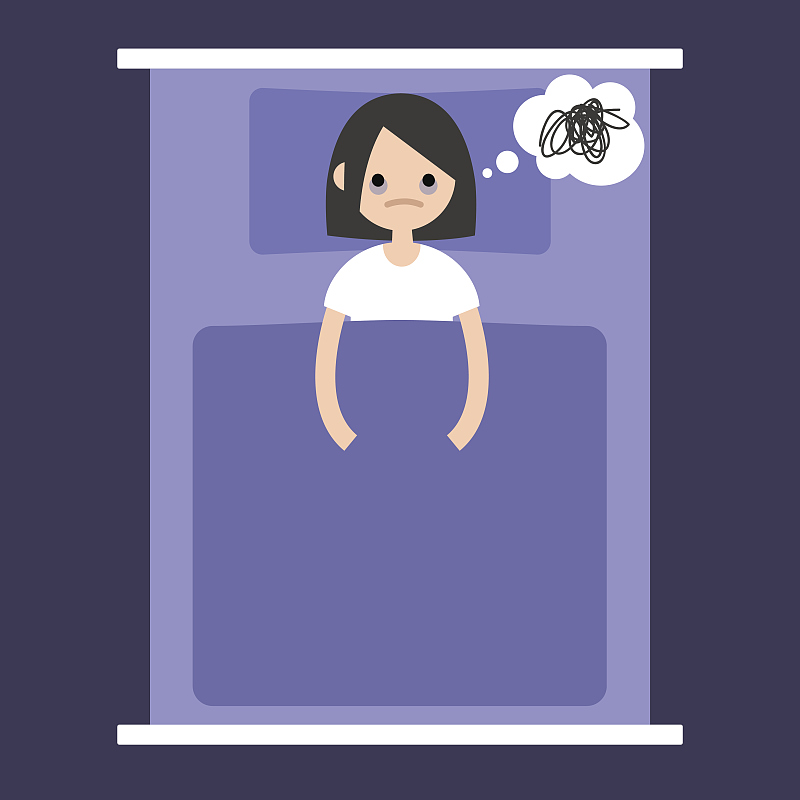
图源:视觉中国
疫情之下,如何认识焦虑和学会正确地焦虑?
关键是如何看待焦虑
疫情中,许多人都很焦虑,那么多人焦虑,这本身也会引起焦虑,但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关键是怎么看待焦虑。这次疫情以一种特殊方式让我们意识到,日常生活中哪些是“必要的”,哪些不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说,应对新冠疫情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正确理解新冠疫情引起的焦虑,通过对焦虑的理解不仅可以避免焦虑造成“次生灾害”,而且可以让焦虑助我们有所学习、有所成长
文汇报:疫情下,“焦虑”这个词总是在我们的视野里跳动着,有人正在经历它,有人奋力抵抗它,甚至还有人在贩卖它。就业、升学、订单、输入病例……不管我们承不承认或者赞不赞同,焦虑的因子几乎围绕着我们每一个人。对此您怎么看?
童世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来具有焦虑的基因,心理学认为,焦虑的情绪本就来源于人类居安思危的生存本能。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在《焦虑的意义》中指出,如果我们能穿透政治、经济、商业、专业或家庭危机的表层,深入地发掘它们的心理原因,或者试图去了解当代艺术、诗歌、哲学与宗教的话,我们在每个角落几乎都会碰到焦虑的问题。
焦虑无处不在,而疫情则放大了焦虑,并使之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特点。事实上,纵观焦虑的发生原由,其本身就有人类的共性在其中推波助澜——人会对自己的存在状况有反思,同时人是所有动物中最不具有确定性的,海德格尔说得就非常形象生动——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的,萨特异曲同工——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其实都是在描述人的存在的不确定性,而焦虑的根源就是不确定性。比如当下,人们的焦虑正是自然的不确定性叠加社会的不确定性的结果。
文汇报:听说您在疫情期间专门读了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1958年出版的《人类境况》一书。这本书能为我们应对疫情,包括应对疫情引起的焦虑,提供哪些启发呢?
童世骏:本次疫情中,许多人都很焦虑,那么多人焦虑,这本身也会引起焦虑,但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几十年都习惯于高速度发展甚至加速度发展的人们一下子碰到那么大范围、那么长时间的停工停学、封村封小区,不焦虑倒反而不正常了。关键是怎么看待焦虑。我之所以想起阿伦特的《人类境况》一书,是因为这本书可以说就是她应对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所激起的焦虑的结果。她说她是要“从我们最新的经验和最近的恐惧出发来思考人类境况”。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再次表达了人类要飞离地球的古老愿望,由这件事阿伦特联想到人类不仅正在一步步走向用科学技术手段创造生命,而且已经在科学研究中用上了远离日常语言的人工语言——因此,肉身存在、日常语言以及地上生活这样一些“人类境况”,恰恰在可能失去的时候,提醒我们看到它们的重要意义。这次的全球新冠疫情也是以一种特殊方式让我们意识到,日常生活中哪些是“必要的”,哪些不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说,应对新冠疫情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正确理解新冠疫情引起的焦虑,通过对焦虑的理解不仅可以避免焦虑造成“次生灾害”,而且可以让焦虑助我们有所学习、有所成长。
文汇报:“焦虑”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从什么时候进入学者的著述当中的?
童世骏:大约是19世纪。最早比较深入而系统研究焦虑现象的是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他们以不同方式把焦虑看作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最基本状况。中文“焦虑”一词对应于德语的Angst,而后者之所以在海德格尔著作的译本中被译作“畏”,是因为孔子所说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中的“畏”字,与“忧”“惑”“惧”“怨”“尤”“虑”“患”等词相比,更接近于存在主义哲学传统中的“Angst”的含义。这里的“畏”不同于害怕,它没有具体所畏的对象,体现的是人对不知何故被抛到世上,在世上又无法确认对象,感到孤立无援而产生的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心态——海德格尔将其视作人存在的方式之一。
文汇报:哲学家将焦虑看作是一种人的基本存在状态,那有没有提出与之共处之道?
童世骏:克尔凯郭尔是这么说的:学会认识焦虑,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一次历险。如果他不想,或是因为对焦虑无知,或是因为被焦虑淹没,而走向毁灭的话。因此,一个人如果学会正确地焦虑,他就学会了最重要的事情。

图源:视觉中国
如何把注意力集中到自我努力与奋斗上?
疫情之后的基础教育
家长和老师要努力保持和优化孩子们在这几个月中学到的良好学习技能和生活习惯,要引导甚至矫正他们在这几个月中出现的不良倾向,但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孩子们在这段经历——对许多孩子来说这意味着痛苦和创伤——的基础上,写好他们今后的人生篇章;多少年后,评价我们的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角度,就是看家长和老师们如何用好这场静悄悄全球战“疫”所提供的特殊教材
文汇报:正如您所言,当下人们的焦虑与“不确定性”有关。另一方面,以“确定性”有效对冲“不确定性”,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及复工复产复市,很多行业把业务从线下搬到线上,新产业新业态竞相迸发;以产业链为中心,建链补链延链强链,应对产业变局不确定性;“两新一重”建设以“增量”补“减量”;再看看我们长期形成的显著制度优势、完备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这些都是“已知”和“确定”。您怎么看这种“确定性”的积累?
童世骏:这说明我们的经济社会正在恢复正常状态。对个人而言,这也是放下焦虑,保持乐观的理由。
如果你把乐观仅仅看作是一种触景而生、有感而发的心情,那乐观是不需要理由的。但乐观不仅是一种心情,而且是一种判断。当我们问有没有理由乐观的时候,我们是在问,我们对自己的现状或未来的乐观判断有没有理由,我们之所以要做这样或那样的判断,是因为我们总要有所行动,总要有所选择。在我看来,在所有的选择当中,最为合理的,就是让今天比昨天更好,使明天比今天更好。人的肉体生命有自然周期,也有不测风云,但人的精神生命则可以作不懈追求、有不断成长。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约翰·杜威说,成长是硬道理。发展和成长是硬道理,乐观也就成了硬道理。在这个意义上,乐观不仅是一种态度,而且是一种责任。
文汇报:您能否跟我们分享下作为一名哲学家保持乐观的方法?
童世骏:要做到乐观,我的第一条建议是看到“‘成人’比‘成事’更加重要”。我建议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话之后再加上“成事在天,成人在己”。成就事业需要天时地利,而成就人格则首先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如果有心向善,出污泥也可以不染;我们如果无意戒恶,近朱者也可能变黑。
从这个角度来看,《论语》当中别人对孔子的那句评价,“知其不可而为之者”,看似指责,实为赞誉。从“成事”的角度来看,挟泰山以超北海,潜水底而捞明月,极不理性。但是,从“成人”的角度来看,夸父追日,愚公移山,则含有深意。
文汇报:可是焦虑之所以成为很多人的 “肤色”,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对标在了别人的眼里。如何把注意力集中到自我的努力与奋斗上呢?
童世骏:多想想“未来不仅仅取决于过去”,这是我的第二条建议。在与他人的比较中产生焦虑,或者说,在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时产生焦虑,往往是因为在处理自己的过去与未来的关系时出了偏差。我们之所以不仅“应该”乐观,而且“可以”乐观,是因为哪怕已经发生的遗憾之事,甚至灾难事件,它们在我们个人经历和集体历史当中的意义,也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以往的人生阶段作为事实是无法改变的,但这些事实的意义,却是可以在未来人生中得到诠释、展开、更新和升华的。
有人问我对疫情之后的基础教育有什么看法,我的回答是:家长和老师要努力保持和优化孩子们在这几个月中学到的良好学习技能和生活习惯,要引导甚至矫正他们在这几个月中出现的不良倾向,但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孩子们在这段经历——对许多孩子来说这意味着痛苦和创伤——的基础上,写好他们今后的人生篇章;多少年后,评价我们的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角度,就是看家长和老师们如何用好这场静悄悄全球战 “疫”所提供的特殊教材。

图源:视觉中国
如何在教育过程中用好焦虑这种“精神资源”?
适当的教育焦虑有积极意义
教育焦虑是与“人之所将是”有关的特定焦虑,介于“生存论焦虑”和“生活面焦虑”两者之间。教育焦虑的意义不完全是消极的,也有可能是积极的。“孟母三迁”和“断杼教子”也反映了一种教育焦虑,而现代人之所以还能从这些古代的故事中得到启发和激励,表明适当的教育焦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关键要看到,不仅“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而且“成事在天,成人在己”
文汇报: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除了医疗救助之外,教育问题因事关千家万户同样备受瞩目。网课如何保证学习效果?“神兽”出笼如何适应课堂教育?中考高考是否会受影响……由来已久的“教育焦虑”在疫情面前似有加重的趋势。您在教育领域耕耘多年,又曾对“焦虑”做过深度哲学分析,可否以“教育焦虑”为案例给我们做一个剖析?
童世骏:分析“焦虑”,首先要把“正常焦虑”与“病理焦虑”(焦虑症)区别开来,之后可以进一步把“焦虑”分成“生存论焦虑”(与“人之所是”有关的一般焦虑)和“生活面焦虑”(与“人之所做”有关的特殊焦虑、与“人之所有”有关的特殊焦虑)。我特别关注教育焦虑的问题,因为教育焦虑是与“人之所将是”有关的特定焦虑,介于“生存论焦虑”和“生活面焦虑”两者之间。
文汇报:您的意思是,这种焦虑之所以会形成是因为教育是一种“人成为人”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童世骏:是的。人是自然和文化的结合体;刚出生时,人身上的“自然”成分大大超过其身上的“文化”成分,而教育就是要完成自然(天)向文化(人)的升华过程。对这种意义上的“天人关系”而言,“亲子关系”特别重要,因为父母的使命就是要让孩子成功地实现这种转化。亲子关系是哲学家们所说的“主体间关系”的一种,但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主体间关系。对于父母来说,孩子既是自己的派生,也是独立的他者。因为孩子是自己的派生,父母会认为为孩子就是为自己;因为孩子是独立的他者,所以父母普遍有那种“可以委屈大人,但不可以委屈孩子”的牺牲精神;但毕竟孩子又是自己的派生,所以,对孩子哪怕打骂强迫,也具有某种道德正当性,所谓“棒头底下出孝子”。
亲子关系的这种复杂性,造成了父母对子女的责任的复杂性,这也是造成父母焦虑的重要根源。“责任”就是“应当”,而根据康德的著名命题“应当蕴含可能”,不可能之事不是义务,往往一个人能力越强,他的责任也就越大。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抽象的“应当”越来越因为具有实现的可能,而成为实际的责任。发展水平所造成的“可能性”,与社会状况的“不确定性”加在一起,往往会让父母处在一个不知道自己为孩子的未来做多少努力才算尽了义务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家长们往往会选择为孩子的未来不遗余力;而“不遗余力”的极端形式,是“道德献血”,甚至“道德捐肾”:不顾一切地为孩子争取机会,哪怕搞特殊、破规矩甚至坏名声,哪怕被原以为可能是“门”的“墙”撞得头破血流,会被认为是具有道德正当性甚至道德崇高感的,就像必要时为孩子献血、捐肾一样。这样的父母虽然精神可嘉,但往往劳而无功——父母的过分焦虑不仅会加重他们自己的个人付出,而且会妨碍孩子的健康成长。
文汇报:那如何走出这种状况呢?您在方法论上有什么建议?
童世骏:首先要看到,教育焦虑的意义不完全是消极的,也有可能是积极的。“孟母三迁”和“断杼教子”也反映了一种教育焦虑,而现代人之所以还能从这些古代的故事中得到启发和激励,表明适当的教育焦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文汇报:这与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的一个观点不谋而合:适切的焦虑能激发人的活力,与创造性成就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如何在教育过程中用好焦虑这种“精神资源”呢?
童世骏:我觉得关键是要看到,不仅“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而且“成事在天,成人在己”:父母和孩子一起作为一个家庭能做成什么事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条件,而想让自己的家庭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主要取决于家庭成员自己——哪怕身居陋巷,粗茶淡饭,也能亲慈子孝,其乐融融;在父母对孩子未来成长的期望当中,“成人”应该是比“成事”更重要的内容,而父母可爱可信的人格榜样,应该被视作孩子“学以成人”的最关键条件之一;孩子最终被培育而成的那种成熟人格,将不仅懂得应该“尽人事以听天命”,而且懂得如何“听天命而尽人事”。
作者:文汇报首席记者 杨逸淇 记者 刘力源
编辑:周辰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