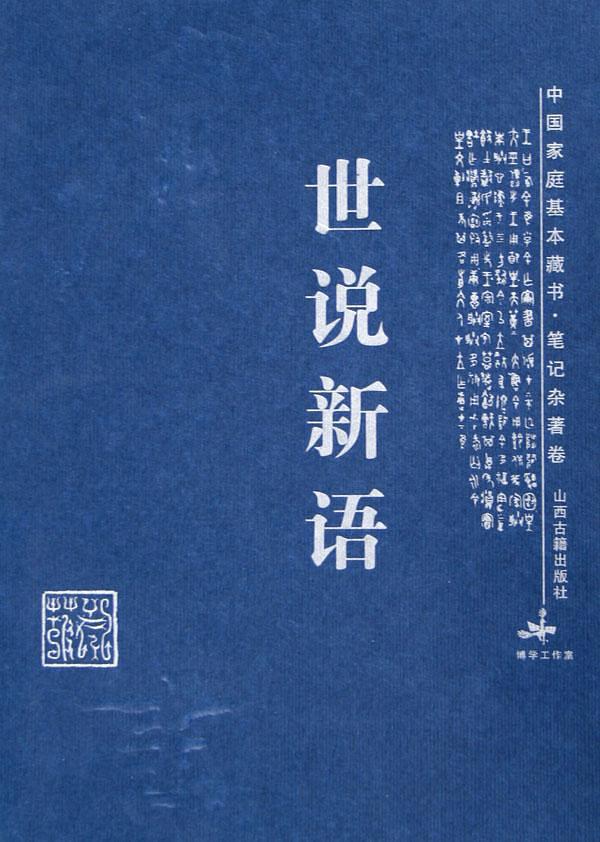
《世说新语·文学》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
孝伯是东晋名士王恭的字;睹是他弟弟王爽的小字。这对兄弟来自太原祁县王氏,是东汉司徒王允家族的成员。王家是国戚,王恭的父亲王蕴以皇后之父的身份,在孝武帝太元二年(377年)十月到四年(379年)八月,被谢安推荐委派,担任东晋徐州刺史,驻地京口。太元十五年(390年),王恭本人以皇后之兄的身份而被器重,由孝武帝任命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州晋陵诸军事、平北将军、兖青二州刺史,挂着长长的官衔,取代诸谢而接掌北府兵,直到东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驻地仍在京口。京口,也就是《世说》所谓的“京”城。
初看起来,这段故事,似乎更像发生在他随父在任的早年时光,因为当他本人出镇京口,他弟弟也已经在都城建康出仕了。然而,在东晋安帝登基之后的头两年,王爽又因为被当权的小人解职,而追随在兄长身边,直到与他一起走上人生的末路。于是,故事中的王恭,到底是出于少年人展望前途时突如其来的感叹,还是中年人回首往事时多少有些沉郁的苍凉,也就成了叠加状态。他所格外看重的两句,则出自“古诗十九首”中的《回车驾言迈》: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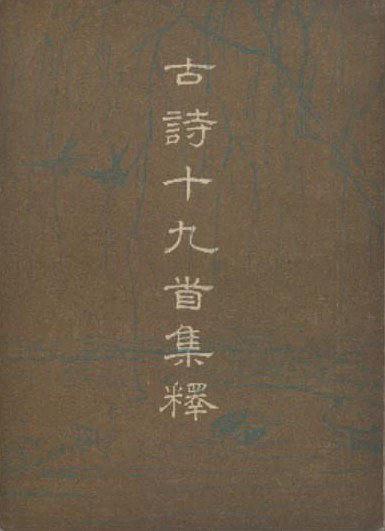
如果单分析字面,这首诗的前六句和后六句,诗人采用的并不是同一套思考模式。前半段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面对新一年开春景物突发感慨的人”;后半段则是一个“努力说服自己从草身上学到点什么的人”。两者之间存在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点断裂,就像小朋友作文最后的那一下习惯动作:试图拔高立意,但容易被读者发现。但它们又奇妙地互相穿插渗透,通过错综的情绪,把全诗联结成内洽的整体。譬如,这首诗实际分为三节,每节四句,而我们可以移动中间一节分别同上下两节结合,把它拆成这样两首诗: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前半段是伤往事,是对“故物”的寻寻觅觅,后半段是“立身”和自警,是“当下和未来”。如此,“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作为全诗承上启下的关键一节,也就更加分明。这一节上通下达,有新旧,有盛衰,高度浓缩了全诗的情绪。
当把目光分别投射到本诗的前后两段,我们会注意到,这个诗人,以及他作品里的抒情主人公,首先恋旧,恋旧到不习惯见到太“新”的东西;其次他不喜欢“老”,排斥得要把“速老”当作很不好玩的东西之典型给数落出来:有点像不想长大的年轻人,又或者是坚持拒绝承认自己年纪大了的长者,总之强烈抗拒着时光流逝对自己可能带来的影响。与之可相参照的是陆机被认为拟《回车驾言迈》的《遨游出西城》。在那首诗里,和这两句对应的是:
靡靡年时改,冉冉老已及。

年轻气盛的时节,读起来可能觉得平淡,但心灵更成熟一些,就会觉得泰然。
恋旧,无非因为旧时光或者旧物,与某些让诗人觉得值得留恋的记忆有关,否则“故物”就是陶渊明说的“觉今是而昨非”,是应当要“载欣载奔”着甩脱的。偏偏他“所遇无故物”的一路,是“回车”而行的一路,不是仗策远寻的一路。不是一般的留恋不去,他甚至还宁愿放弃继续前行的机会和未来无限的可能性,只求回溯的时候,能见到一些熟悉的东西。但他随即发现,他已经有意回头来寻找,却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以感到很怅惘。
这个诗人,或者他笔下的抒情主人公,明明已经远走,突然想起来要回头,被亲眼所见“所遇无故物”的现实打得措手不及。
类似“突然回头”的片段,前有屈原《离骚》的情节——在《离骚》中,诗人经历了“上下求索”,正待继续周游天界,忽然回头发现了自己的故乡,“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后有杜牧的《将赴吴兴乐游原》:“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这两位都是伤于国家危亡关头,自己所效忠的君主却不能有所作为,充满了欲弃不能的情绪。《回车驾言迈》的作者并不是这样的。他寻找的“故物”,似乎就只对他自己有意义。这个抒情主人公,表现得也似乎更像是一个回乡的游子,然而“到乡翻似烂柯人”。折返行为本身显然丧失了最初的意义。

所以,诗歌的后半段,抒情主人公才会选择追寻“荣名”:接下来的人生对我已然没什么分别,但我或许可以让自己对别人来说稍微有意义一点。他再一次转过身,投向对他来说已经全然陌生的世界,带着莫名苍凉的心情和不再反顾的决然。——连屈原在《离骚》的结尾,都会说出“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这样的愤激之言,一个发现自己彻底回不到过去心灵家园的游子,又如何必须留恋于那个破碎的幻境呢?
但王恭显然还是愿意继续恋旧的,所以他捕捉到了“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但令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再继续追问原因。也许他从中读出了某种轮回抑或无常;但具体是否如此,我们不得而知。《世说新语》的编写者们也是一样。他们不约而同地避开了与这两句呼应的“回车驾言迈”。或许他们都是天生直行不顾地恋着旧吧。
作者:萧牧之(南京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
编辑:柳青
责任编辑:邵岭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